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07)
著名作家周立波代表作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在《人民文学》1958年1至6月号连载推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六个月内,编辑部不断收到读者来信,给出好评,也有部分读者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疑问,希望作者解答。《人民文学》编辑部根据读者来信,综合整理了几个问题转给周立波,并在当年7月号刊出《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一文,将读者意见与作家的回答一并发表。
8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将在周立波故乡湖南益阳举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在计划启动仪式前夕,让我们一同重温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的创作心路,倾听文学名作的诞生历程。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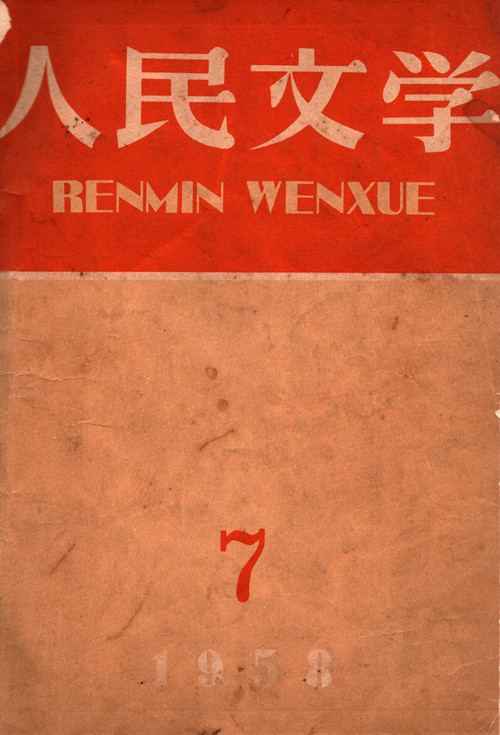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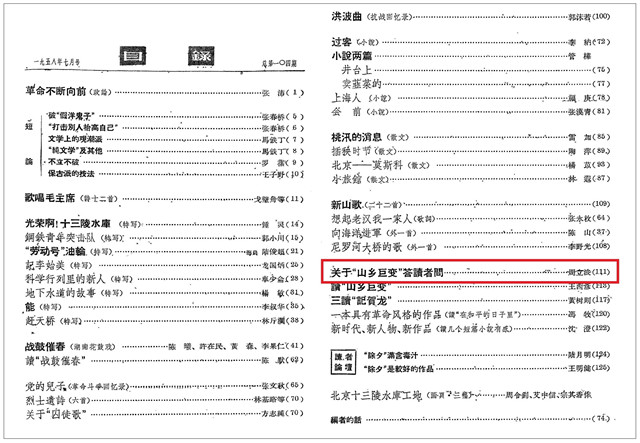
《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封面、目录
问:作品中写了好多个人物,个个生动、逼真,活灵活现,一出场就很自然地吸引了读者。特别是亭面糊、王菊生、陈先晋几个人物,更是形象鲜明,具有真实感,读后给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不知这些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儿?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有些什么体会?
答:这些人物大概都有模特儿,不过常常不止一个人。比方,王菊生的形象,有些是我的一位堂弟的缩影,有些是另外两个富裕中农的行状。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遍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的鲜明的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人。陈先晋这个人物的家里我只拜访得一次,平素,从别人的口里,主要是从他亲戚的口里,多次听到谈起他,而且,我也观察和分析了和他属于同一类型的另外几个较为守旧的贫农。
塑造人物时,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着他的生活的规律,有了这种日积月累的包括生活细节和心理动态的素材,才能进入创造加工的过程,才能在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驰骋自己的幻想,补充和发展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可能看到的部分。
没有接触和研究过的人最难描画。
问:作品中采用了群众的语言,生动、朴素,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不知作者是怎样采用了群众语言的?有的读者认为不应该用这么多方言土语使外乡人看不懂。不知作者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对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有些什么看法?
答:在农村和工厂,我常常留心倾听一切的人的说话,从他们口里,学习和记取生动活泼的语言。使用方言土语时,为了使读者能懂,我采用了三种办法:一是节约使用过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须使用估计读者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三是反复运用,使得读者一回生,二回熟,见面几次,就理解了。方言土语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如果完全摈弃它不用,会使表现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蛮大的损失。有些方言,字同音不同,写了出来,别的地方还是看得懂,如“拆壁补壁”,放在作品里,全国的人都懂,但照这地方的土音(壁音bia)讲起来,恐怕只有本地人懂了。这样的方言,我主张多用,因为它们可以丰富普通话的语汇,加强它的表现力。但也有一些土话,有音无字,或是不知道那个音是哪一个字转化而成的,写了出来,别处的人看不懂。比方,我们这里有句这样的话:“和尚错了腊肉,乱犁子犁。”意味相当地深远。吃斋吃素的和尚是不应该有腊肉的,既然有了,又失去了,急得乱跑乱找,又不好声张。拿这句话来形容暗中着急的人的心情,实在是生动。但它有两个动词:错和犁,别处地方的人看不懂,必须说明错是失,犁是奔跑和瞎撞的意思。等到解释了半天,这句话的生动性和幽默味,已经损失了。碰到这样的土话,我虽然欢喜,但也只好不用它。
有些地方特有的物事、器具,如北方的睡觉的“炕”,南方舀水的“端子”,写在书里全国的人不一定都懂。我没到北方以前,不晓得“红楼梦”里描写的“炕”是什么样子。没有到过南方的北方人一定不晓得“端子”是什么玩意。但这样的名词还是要用,估计读者不懂时,可加注释,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以为文学语言,特别是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应该尽可能地口语化,但也要提炼、润色,要多少有一些藻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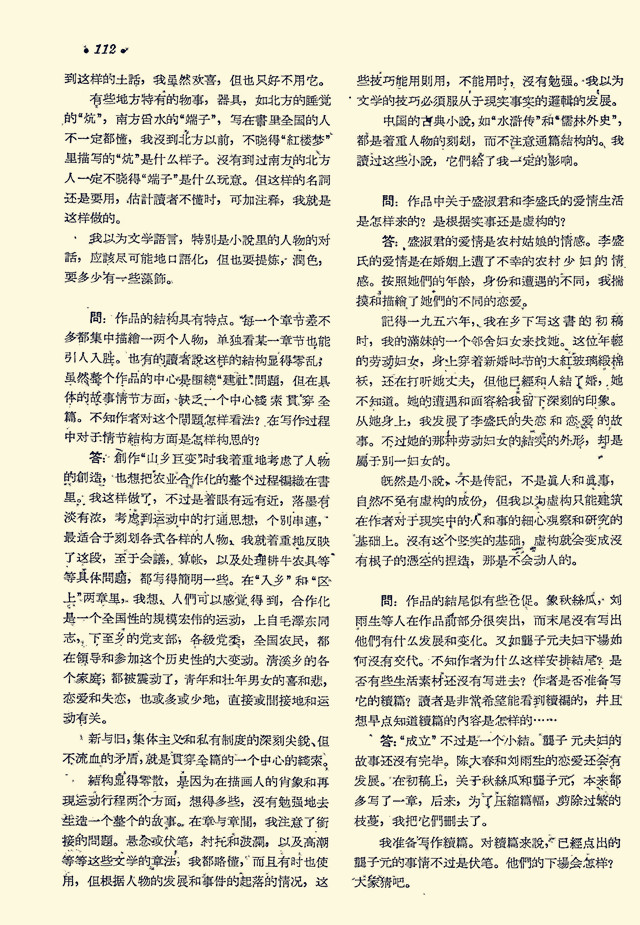
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
问:作品的结构具有特点。每一个章节差不多都集中描绘一两个人物,单独看某一章节也能引人入胜。也有的读者说这样的结构显得凌乱,虽然整个作品的中心是围绕“建社"问题,但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缺乏一个中心线索贯穿全篇。不知作者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法?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情节结构方面是怎样构思的?
答: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我这样做了,不过是着眼有远有近,落墨有淡有浓,考虑到运动中的打通思想,个别串连,最适合于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就着重地反映了这段,至于会议、算账,以及处理耕牛农具等等具体问题,都写得简明一些。在“入乡”和“区上”两章里,我想,人们可以感觉得到,合作化是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上自毛泽东同志,下至乡的党支部,各级党委,全国农民,都在领导和参加这个历史性的大变动。清溪乡的各个家庭,都被震动了,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和运动有关。
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锐但不流血的矛盾,就是贯穿全篇的一个中心的线索。
结构显得零散,是因为在描画人的肖像和再现运动行程两个方面,想得多些,没有勉强地去生造一个整个的故事。在章与章间,我注意了衔接的问题。悬念或伏笔,衬托和波澜,以及高潮等等这些文学的章法,我都略懂,而且有时也使用,但根据人物的发展和事件的起落的情况,这些技巧能用则用,不能用时,没有勉强。我以为文学的技巧必须服从于现实事实的逻辑的发展。
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和“儒林外史”,都是着重人物的刻画,而不注意通篇结构的。我读过这些小说,它们给了我一定的影响。
问:作品中关于盛淑君和李盛氏的爱情生活是怎样来的?是根据实事还是虚构的?
答:盛淑君的爱情是农村姑娘的情感。李盛氏的爱情是在婚姻上遭了不幸的农村少妇的情感。按照她们的年龄、身份和遭遇的不同,我揣摩和描绘了她们的不同的恋爱。
记得一九五六年,我在乡下写这书的初稿时,我的满妹的一个邻舍妇女来找她。这位年轻的劳动妇女,身上穿着新婚时节的大红玻璃缎棉袄,还在打听她丈夫,但他已经和人结了婚,她不知道。她的遭遇和面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她身上,我发展了李盛氏的失恋和恋爱的故事。不过她的那种劳动妇女的结实的外形,却是属于别一妇女的。
既然是小说,不是传记,不是真人和真事,自然不免有虚构的成分,但我以为虚构只能建筑在作者对于现实中的人和事的细心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坚实的基础,虚构就会变成没有根子的凭空的捏造,那是不会动人的。
问:作品的结尾似有些仓促。像秋丝瓜、刘雨生等人在作品前部分很突出,而末尾没有写出他们有什么发展和变化。又如龚子元夫妇下场如何没有交代。不知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结尾?是否有些生活素材还没有写进去?作者是否准备写它的续篇?读者是非常希望能看到续篇的,并且想早点知道续篇的内容是怎样的……
答:“成立”不过是一个小结。龚子元夫妇的故事还没有完毕。陈大春和刘雨生的恋爱还会有发展。在初稿上,关于秋丝瓜和龚子元,本来都多写了一章,后来,为了压缩篇幅,剪除过繁的枝蔓,我把它们删去了。
我准备写作续篇。对续篇来说,已经点出的龚子元的事情不过是伏笔。他们的下场会怎样?大家猜吧。
(陈泽宇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