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想象的停靠站 ——评渡澜小说集《傻子乌尼戈消失了》
主持人语:
出生于1999年的青年作家渡澜是汉语世界的后入者,她的母语是蒙语,从小接受蒙语和汉语的平行教育。蒙语中人与自然浑融不分的境界,成为其作品齐物之境的基础。小说集《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充盈着奇妙比喻,以色彩、触感、声音、气味的层层堆叠赋予文字以灵性。罗兰·巴特将写作技巧称之为“一种既固执又迂回的言语活动”,其迂回性体现于“无限多样的停靠站”。渡澜的跨语际书写就提供了这样的“停靠站”,语言、思想、作者、读者之间的对话迷离扑朔。“和光”组织了一场渡澜小说研讨,“90后”“00后”读者,试图从意象、自然、语言、修辞、叙事等视角,打开渡澜作品广袤馥郁的文学空间,牵引出游荡其间的宇宙情怀。
——戴瑶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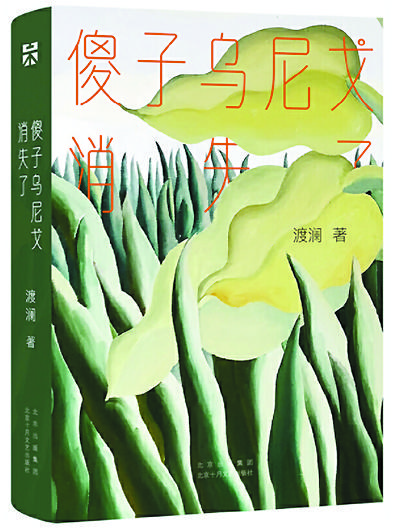
1.乌尼戈·自然力·童年
于明玉:动物入侵、世界异变的迷离景象以寻常样态踱进读者视野,将曾经此在化、生活化的物象重新推回原型。无法落地的猜疑如“嘎乐”一般涌动:在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创世神话中,母亲神额和·布尔罕分离天地之初即创造野鸭衔泥筑陆,《去看乌嘎跳舞》则以鸭子为言说单位;萨满教巫女作兽禽舞、着鸟羽服,遨游于天神/人族间沟通圣谕,又可作解喜鹊乌鸦对乌尼戈的亲昵之态。在普鲁斯特式“绵延”漫漶的时间里,动物创世神、英雄勇士以持守远古文明的超现实形象返生,也建构了民族记忆的初生场所。去仪式化的生态叙事恰与《沙乡年鉴》所述“共同体”意识偶合——生命依扶关联,万有归复于一,人与诸灵尽为穹庐怀抱的仔畜。
王奕宁:说到共同体,我不禁想起了《沙乡年鉴》中的这句话:“一个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虽然这句话看上去有些忽视事物模糊性的可能,但乌尼戈悲伤又温润的包容与平和简直是这个共同体叙述的翻版。《傻子乌尼戈消失了》表面讲述的是一个叛逆的、不溶于社会的孩童成长史,但其中更引人深思的是故事背后蕴含的自然思想。我认为,乌尼戈是被人类不断迫害的自然的缩影。他拥有“无限接近自然的美”,第一次出现时就布满了人类的“脚印”,“我”将他拴在餐桌上的举动也体现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乌尼戈包含世间万物,以及人类肉眼无法见到的物质实体(松鸡)。当他遇到能够为人类带来财富的俄日敦德日格勒的时候,命运就难以遏制地冲向低谷。他被当作取悦“致富机器”的宠儿,在“财富保安”的围追堵截之中,它自身的资源与价值也在慢慢的磨灭与销毁,直至满身创伤。即使这样,乌尼戈也没有放弃人类,他向人类展示出了近似母爱的慈悲。可这种广博的原谅却没有换来人类(小镇居民)的一丝怜悯与犹豫,他们杀死了乌尼戈,将它烧得只剩在风中蛰伏的灰尘。同时,他们——人类——也因为迫害自然的乌尼戈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切来自于乌尼戈,也复归于乌尼戈。随着风的凝聚与疏散,乌尼戈终将以另一种方式重组再现。
张晖敏:虽然小说集触及童年和自然这个常规议题,读者却难以在其中圈定传统浪漫主义书写范式的乌托邦。我觉得渡澜的书写不是回溯式的“减法”,而是时刻都在做着“加法”。族群记忆的差异首先使原型作用失效,过于冷静和细腻的讲述更让童梦的天真里带上了残酷——像是详尽地描绘灰姑娘的姐姐们如何削去脚跟。而不期而至的消失、徒劳的寻找、失效的保护和无望的抗争,总是在非现实的场景里唤起令人刺痛的现代情绪。美德、恶行、文明、野蛮、新生的芬芳纠缠着垂死的腐臭,截然对立的矛盾并置现形,又被童真逻辑弥合。“卮言”式的奇异魔力将读者拉入陌生的草原,蓬勃的生命力超越了族群乃至物种的差异汹涌而来,衔尾蛇般永恒流转的时间里。童年这个苍老的稚子被不断粉碎重组,静默地延伸向尚未展开的将来。
王奕宁:我觉得渡澜绮丽的梦背后有“天人合一”自然哲学思想为其支撑。“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善’,这种‘内在的善’所具有的非人工所能代替和改变的‘神性’,构成人类所追求的生存世界的价值本原。” 乌尼戈就是这种善的显现。像我上面提到过的,乌尼戈一直都是以一个可怜的被欺凌者形象出现的,但不管身体再怎么破碎与残裂,精神再怎么恐惧与颤抖,他还是会抱着他最珍视的宝物——喜鹊向我们横冲直撞地奔来,好像完全不在意口袋里人们对他的唾弃与伤口中流出的血渍,只是不计回报地释放“真心”的养料。这种真心和天地世界无二无别,是同一的。自然是不断循环往复的、永久的存在,它是自由无边的,而不仅仅是人类的囚徒与“供应商”。虽然自然的生命意义与内在价值需要人类的实践与改造才能完成,但这种改造也应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当人类将自己过余的妄念移除,对自然抱有同理心的关怀,才能与自然一起融通,从而达到一切皆空的“天人合一”境界。
2.跨语际·词语·修辞
张晖敏:渡澜是很典型的跨语际写作,这一写作天然带有陌生化的效果。她以囚犯“三角形”般的敏感谨慎,触摸崭新语汇,童年原初的开放性于此刻回到了作者身上。在故事里,她偏爱书写对话,将新鲜的表达欲望倾注其中,每个出现的角色都固执地展览着独属的、情绪化的主观世界。而读者也不得不加倍谨慎地对待文本。一方面,词语几乎密不透风地向读者笼罩过来。过载的信息充斥着每一帧画面,带来难以聚焦的眩晕。而这些活的、不寻常的词语又让人反复停顿下来,以免错过其中探出的细微触角。
于明玉:难以想象的是,如此一个涤荡素朴、驳杂斑斓的语言王国,却依旧锲而不舍地值守客观世界。符号如獒犬,寸步不离它畜群般的实存对象,在虚构文学创作脱壳的当下显出一份澄清与忠实。蒙语惯性使得“艾日格”“乌日木”此类不转译的称谓频频流出,直接暴露诸多词汇的源头正是向生活经验取色,而在这一点上渡澜同她的祖辈一脉相承,不过蓝(青)色神符“长生天”之宏大,已然退位于“乌珠穆沁熏皮袍色”之庸常。具体物象的扩容,逐渐将隐形关系、微妙情绪、心理图像搡出言辞洼地。
张林:聚焦词汇,小说中翻涌着大量密集而瑰丽的名词。名词作为存在物的名称,如同一扇扇门,背后站立着事物和事物的全部由来。乌尼戈从门里出来,门也是柳泽真由娜梦中的素描纸,它们是作者想象的造物,在一个个名称里活筋动骨,生长后腐朽。
她详细地命名事物,人名、地名多源自蒙语。蒙语名称常带有特殊含义,作者为少量名词给予注释,如乌尼戈意为狐狸,嘎乐意为火,这些意义在小说系统里起了直接的或象征性的作用。但大部分并未加以解释,并创造了如“吻驴的毒唇”等携带着并未言明的神话象征意味的词汇,这些无法解码的空白锻造了一种想象的停靠,作为叙事的延宕,发散出无尽可能性。
王奕宁:我看到有人评论渡澜对世界上事物总有一种天然呆的延迟感,但我更觉得她保护了青少年时期心态的敏感与丰沛。也正因为这,她的语言风格才会既有稚气孩童的柔和与谅解,又夹杂着历经磨练的成年人的犀利与深刻。小说中设计了自带含义的蒙古文名字,比如“鼬鼠之天敌”的乌尼戈,代表财富的俄日敦德日格勒,“招弟”的杜达古拉等等,这些名字组成了小说中情节推进的重要关卡。它们带有对贪婪人性、落后习俗等文化内核的讽刺,但又因为是名字的缘故变成了一种带有模糊感与距离感的独特意象,使得这些讽刺少了些刻薄的感受,多了几分跳脱灵巧的活泼,也为故事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于明玉:是的,仅有她能像摩西分红海一样直抵本义彼岸。我梳理了一下小说中的名字,状貌逾常的莫德勒图寓意“智者”,性格怯弱的阿拉坦巴图象征“如金子般坚固”,甘狄克“花岗岩”、扎那“大象”、三丹“檀香”、索布德“珍珠”……隐秘的民俗事象符码自异域文化的裂罅中向外窥探,裹挟神性与诗意。
张林:另外,在渡澜小说中,名词常常并非单独点状出现,而是通过修饰、并置或递进等关系聚合成束,他们的组合不是建立在理性逻辑之上,而是跟随作者万物浑融的独特思维,铺展成奇诡斑斓的画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本为“乱糟糟的浑然之物”,而渡澜则将“浑然”带来的独特效果极致发挥,将不同性质的名词混用。她在充满民族性与神话感的自然类名词群落里插入现代性的科学类、工业类名词,她将新几内亚桉树和甲状腺激素、分裂增殖、骺板软骨并置,将羊奶、黑艾日格与氧气、氮气、氖气互为映照,将金黄色葡萄球菌、小肠耶尔森菌与美人指、甜象草、炭火味道糅合。渡澜也在充满原始象征的词语中嵌入属于理性时代的抽象性、说明性词汇,如讲述关于傻子乌尼戈的名字时提到了应用于管理学、网页设计等领域的KISS原则;刻画生气的邻居时,形象描绘其波涛汹涌的肚子,执拗的脚,再加以总结为:结构性的生气经验。这种特殊的用词习惯或许与蒙汉双系统学习经历有关,蒙语塑造的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已然纯熟,当新名词进入其语言系统时,即被吸纳为万物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丰富而非破坏。
李婧怡:修辞在渡澜写作中占据着重中之重的位置,其中通感则占据主要位置。在文章中,五感仿佛统统混淆,声音可以充满痛感,人看起来可以像温和的气候,皮肤在恐惧时会散发出一股臭味儿……这种看似缺乏逻辑、不符合常识的搭配,赋予无形的东西以形状,击打有形之物直至其消散、弥漫在各个角落。小说中人与动物、人与自然、此物与彼物之间的界线消失了,一切都处于变形和无规律之中,世界在呼吸之间胀缩。小说中扑面而来各种感觉——vibe——仅仅是一种氛围。当你无法从她的语言中获得清晰逻辑与意义时,不需要用常识和理论去规范和解读,只需将自己浸没其中。蓬勃的氛围感推动叙事,像层层海浪交叠着涌上沙滩。读者随之变幻成一条鱼,跃迁于水面。
张晖敏:感官之间倾斜流动,物种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模糊始于命名的混杂,狐狸即是乌尼戈,乌尼戈即是那个衰老与新生间往复的男孩;婴儿即是嘎乐,嘎乐即是火,火同时是呼唤和警告,名称虚弱地提示着它们的分别。千头万绪间难以寻找到完整的逻辑链条,因此修辞也开始脱离技法的层面,“拟人”和“拟物”都无法确切概括其间深层关联,隐藏其间的、完全诗化和抽象化了的意义等待着被发掘。
张林:大片明喻隐喻换喻夸张拟人翻飞漫溢,但她赋予这些修辞以非修辞的性质。拟人以人类为中心,比喻基于事物之间的分别,夸张要首先认证某种理性的现实。而渡澜的文学世界却并不刻意分别人与物、物与物的形态,这一方面体现在人物塑造的未确定性,比如由日本黑乌鸦产下的柳泽真由娜,是“三十岁左右,头发稀少的女性”,有乳房,嘴唇,却也会掉落黑色羽毛,作者不明确其形态是人还是乌鸦,也不将其作为两种形态简单叠加,仿佛一个人身上掉落羽毛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变成羽毛的三丹姐姐,是鸟,还是人,不去区分。无须描绘本身便传递一种态度,即浑融齐物的宇宙观,这与其说是一种修辞(拟人、比喻),不如说是写作者世界观的呈现。至于看似是夸张修辞的部分,或许也是渡澜想呈现的本来面目,乌尼戈身上兼具不同的人生阶段,飞速变换,这是她塑造的独特生命形态;死也不是一种夸张,它轻易且自然,佛教称涅槃灭除烦恼,度脱生死,死是寂灭的边界,但在渡澜笔下,死后依然言语不休,烦恼不断,生死边界就这样消弭,夸张的修辞性质也在分界线的消融中自行瓦解。
于明玉:作者曾不止一次地以候鸟、四季等一切循环往复之物为生死开解:“我们的朋友乌尼戈永生不息——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这一有无相生、顺其自然的哲学思维撕破“形”与“界”。《金甲虫》里一条匪夷所思的动线——融化的雪、用胡子制作的门、马鞭、山雀的啼叫——演示了声响向色彩的更新;鼬鼠、汽车、火、舌头、老虎、牛皮、鸟标本等意象层出叠现,在其私人辞典里蜿蜒出一套挟有幻觉气质的象征群组,并最终化为一声张牙舞爪的恫吓。事物人格化、谜语式的欲望书写、形象的变化与拟构,共同推动渡澜穿越“稠密地带”,直抵“表达的真实”。
张晖敏:文集中来自不同民族的抚触切碎词语原本权威:交错的口语、书面语、“过大”和“过小”的形容词,几乎可以构成一个微小却崭新的隐喻系统。因其承载了作者完整的思维过程,尽管能指和所指的关联不断受到挑战,文字的生命力却没有被削弱,反而愈加丰盈。文集独特的修辞特征近于古典诗的“曲喻”,又因其篇幅和句式的不受限显得格外放纵。万物有灵的世界里狂欢永不停息,陌生化的语汇带着天然而野性的节奏激情,构成了鲜明的辨识度,也为读者的阅读体验增加了质感。
3.弯曲的叙事脉络
张晖敏:与其说是讲故事,我觉得渡澜更像是在写诗。非母语写作在文字中留下的中顿痕迹带来了诗行般节奏。诡谲的逻辑链条,则使得文本免于落入起因—经过—结果的线性叙事。小说中童梦色彩强烈的故事十分单纯和俭省,没有人试图追问卡夫卡的城堡是罗马式还是哥特式,那么亲吻公驴的生殖器诞下金鱼也可以具备合理性。故事的结局并不难揣测。就像王子和公主总要生活在一起——坏脾气的邻居迟早自取灭亡,珍贵的羽毛必然遭到破坏,跳舞的乌嘎一定藏着谎言。但是读者可以揣度故事的走向,承上启下的规则似乎在照常运作着,但只要稍不留神,便会从原本看似平滑无缝的情节之间重重跌落。彻底消化文本信息量不能一蹴而就,聆听者只能囫囵吞下这个草原吟游诗人的全部诡计。
于明玉:在渡澜小说里,情节是覆盖语言富矿的薄土。一方面,主人公的种种举动缺少标记明显且逻辑自洽的行动序列,让观客无从拾捡解读焦点。而叙事脉络也一再以凸字或U型的姿态出现,毫不避讳其模式化与不完整性:起点往往会预设一个抽象、笼统的答案,而后泡沫样的高潮弧线便兜转升起(中途它几近涨破),当文字呱噪得渐次拱起纸张,故事却滑向寂若死灰的乌有或温情脉脉的永恒。“始”与“终”纷然落归一线——目睹甘狄克惨死的风止息于灵魂被烧尽的松林,去而后返的乌尼戈照拂每寸生命的酣眠,阿拉坦巴图得知噪音真相的那一瞬,“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种惊人的寂静”,似乎是急于将一切飘曳在外的余语都掐灭。
李婧怡:在我看来,渡澜的叙事并非以复杂紧凑取胜。以首篇《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为例,我们或许可以对其结构作此解:相遇(出生)——误解(挫折)——崩溃(死亡)——重逢(重生)。渡澜在此为乌尼戈也为我们画出了一个完满的圆,它如一面崭新发光的镜子,反射出回环往复的时间观与万物来去自由的生死法则,同时也映照出普通人的日日夜夜。面对这样一种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叙事模式,我们可以秉承开放的解读理念对小说内容作出多种角度的解读,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甚至人的异化等等。
于明玉:恰如雷蒙·凯诺所言,“盲目屈从于冲动的所谓灵感,实际上是一种不自由。” 人物行动的屡次失常同结构形式的无限翻版,一起搅浑在渡澜诗人般的创造中,也使文本的易读性蒙尘。实际上对读者而言,从开局迈向结尾是困难的。大量信息从疯转事件中逸散,如过山车期间的风声与尖叫一般,达成了短暂的信号屏蔽效果,又在叙述完毕的那一刻迅速结网成罩。由此小说集里充斥着异质性的鬼影和漩涡,试探、狐疑与不信任竟成为了观者的常态,一个巨大的骗局悄然诞生——蓝蜻蜓日迪接回了“智慧达达”,扎那失去了“三丹姐姐”,在自由意志席卷的林野中央,渡澜平静告诉我们,她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
张晖敏:曲线叙事的方法,令民族、地域、文化的差异短暂闪现又消弭,因其生动而并不令人觉得突兀。在诗化的、狂欢的自然之境,任何封闭阈限都可以短暂性被打破。敞开的广场上,只剩下欣喜的“孩童们”——人、兽类、或是其他生灵——留下的足迹。
和光读书会简介:
大连理工大学中文学科“和光读书会”成立于2018年6月,主持人戴瑶琴,“和光”定位是本硕贯通、“90后”及“00后”、文理交叉。“和光”已发表专辑《时代记忆与空间符号认同的东北书写》《<大山里的小诗人>:翻山越岭的希望之光》《<飞鸟和池鱼>:锦鳞绣羽,水陆藏心》《<贝尔蒙特公园>/东京说:要顽强啊!》《<流俗地>:生于落俗,安于流俗》《<男孩们>:脐带与鱼线》《<流俗地>:俗地之光,岂能流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