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抵抗遗忘”是对写作者的最高要求
在散文领域,傅菲已执守多年。以对于万物的敏锐感受和诗性描绘,他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书写场域。在这其中,枫林村与饶北河是他童年的居所,也是他长久的精神源泉。近期,他以为故土乡民为书写对象的散文集《元灯长歌》推出,完成了其精神疆域的又一块重要拼图。
对傅菲而言,“元”是周而复始之始,代表初心,“灯”乃光明之源,元灯即是渊源、希望之灯、初始之灯。以村志的形式,他专注于着墨盆地人民的生存状态、内心困厄、精神风貌、时代变迁,想要为河流立传,为大地塑像,为人民刻神。
每一个有根性写作的人,都需要自己的文字根据地
记者:在你的乡村写作中,枫林村与饶北河无疑是两大精神源泉。
傅菲:枫林村是上饶市北部中心城镇郑坊镇辖下的小村,处于饶北河上游,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20年乡村写作的原点。这是一个普通、贫瘠的盆地小村,但属于我眺望世界、审视世界的视点。每一个有根性写作的人,都需要自己的文字根据地,凭此生根发芽、枝开叶散。
根性,是一个很有生长力的词,意味着只有“向下扎”,才可以“向上长”。这个并不时髦的词汇,确实很适合我。与“根”有关的是土地、水、阳光。也就是精神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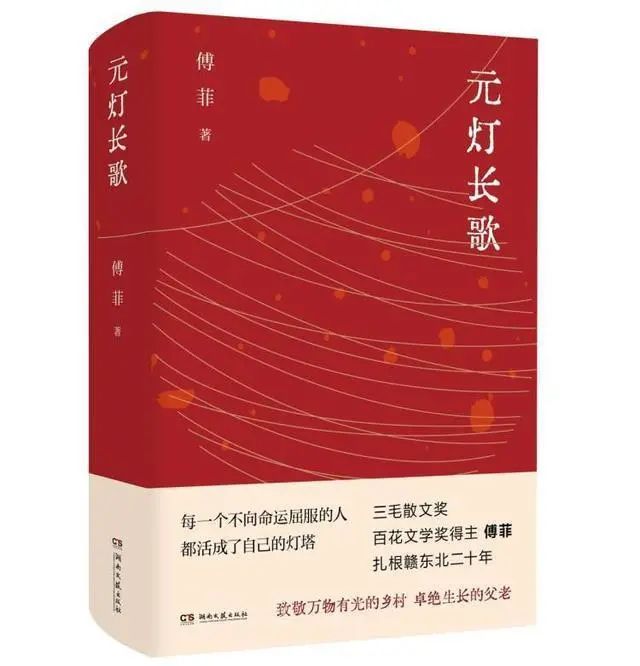
《元灯长歌》傅菲/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记者:的确如此。虽说每个人都依恋故乡,但是还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与变迁中,这片土地的独特之处在哪,以至于你多年以来有着无穷无尽的书写主题与欲望?
傅菲:“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与变迁中”,可以理解为“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的过程中”。从现实层面看,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中青年人,以外出务工为生,老年人种粮种菜。在日常生活层面,似乎与工业文明不是很贴近,但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深受城镇化和工业化影响,以至于乡人的思维、视野、精神状态、行为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他们虽处于时代的急剧变迁之下,但他们还没准备好迎接工业时代。他们努力迎接工业时代,却显得不知所措。他们有思想的斗争,有焦虑,有渴望,有尝试,有奋不顾身地融合。他们也许狭隘,也许偏执,也许误入歧途,但他们从不放弃自己。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使命,并为此付出最大的努力。正是因为他们甘愿为热爱的生活而不辞辛劳、坚忍不拔地完成自己的生命职责,我有了蓬勃书写的欲望。
一个只有2600余人口的枫林村,在他者眼中,毫不起眼,只有巴掌大,于我而言,是无穷无尽的。我以“自然生态”“地域文化”“乡村伦理”“风物之美”“生死乡村”等不同的主题去书写。《元灯长歌》以“土地的赞美诗,人民的生命史诗”为主题,以百年历史大视角、江河长卷式,书写饶北河上游的乡村变迁和乡村振兴,歌颂劳动之美、生命之美、时代之美、人民之美。
记者:在我的理解中,人从他乡经历不同的生活后又回到故乡,既然要面对自身的变化,也要面对村庄的变化,并重新找到接续过去与当下的方式。对你而言,这其中是否也存在一种“断”与“续”?
傅菲:1986年,我离开枫林村外出求学,并一直在外工作。2002年,我开始写散文。在这个时间间隔期,我很少回枫林村,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断”与“隔”。在写作初期,我写的乡村散文以生活经验、生活理解、生活见闻为主。
2014年底,我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必须从具体的现实生活汲取写作营养和力量,于是,我每年安排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到自己的村子,与村民一起生活、一起议事,参与村中公共事务讨论、建设。我不是一个乡村观察者,而是乡村生活者。我写作的很大部分素材,直接取自于现实发生的生活事件——我的写作直接来自于我的现实生活。我对村中的重病患者、退伍老兵、重要手艺人、家庭收入、就业情况、婚姻状态、违法情况、动植物分布等领域,作过多年的详细调查。
我以枫林村民自居。所以,我的“续”与众不同。我不是怀乡式的乡村写作。这是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转变:从书斋走向大地,从小我走向人民。
记者:其实对于作家而言,真正的重回而非“探亲式回归”,这无疑是困难的。我也发现在你的写作中,少有外来的价值判断、少有浮光掠影的观察和感受,这似乎是你刻意避免的一种书写倾向?
傅菲:我内心反感自己“探亲式”书写。我不写自己反感的文章。我一直恪守自己的原则:对自己笔下的文字,不可以虚情假意。
在散文中,“我”一直“在场”。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熟悉笔下人物的生活、气息、场景、出生与去向。我以丰满细腻的细节去刻画这些生动的人。在写之前,所需刻画的人已在我面前行走,如我的邻居、亲友、仇敌。我要求自己所写的每一个人物或场景,必须是生动,哪怕只有片言只语。当然,这样的要求给自己带来了写作难度。当然,我喜欢有难度的写作。挑战自己的写作难度,是写作乐趣之一。
记者:读其中的一个个故事,总有种感受:再僻远的山乡,村人的生命也很少是个体的生命,总被时代所扰,为时代所动。在不少篇目叙事中,也看到了如同期声一样的历史阐述片段,想了解的是,在这样的书写中,历史片段该如何恰切地契合于文本,而非凌空虚蹈?
傅菲:同期声一样的历史阐述片段契合个人史的文本,可以说是我写地域人物的一个特色。历史是生动的、鲜活的,通过个体的人生命细节,会表现得打动人心,也更有深度。也因此获得流淌的活力,而非刻板式的诠释。近代地域史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接”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
灵山属于怀玉山山脉,灵山北部小镇葛源是方志敏先烈当年从事革命斗争的根据地,与郑坊镇一山之隔。郑坊镇的祖辈积极加入先烈的革命事业,与当时的腐败政权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段历史,深刻地影响了祖辈、父辈、我辈的思想。方志敏先烈写的《可爱的中国》,是祖辈的梦想,也是如今的现实生活。在我的理解中,这是我辈的精神源头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思想源头之一。在《元灯》《大悲旦》《似斯兰馨》等篇什,我写了这种伟大的精神、蓬勃的生命。
记者:由此,个人史成为地域史或大历史的一部分。
傅菲:对,这是我想表达的。我专注于书写扎根在大地上的人民、始终面向未来的人、努力生活的人,传承乡村文化,赓续乡村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为河流立传,为大地塑像。他们是大地上的灯塔。
个体的人无法脱离自己的时代。个体的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支流与水系的关系。伟大的精神和蓬勃的生命,会超越自己的时代,属于任何时代,如星宿高悬,照耀我们。
记者:相较于其他的系列作品,其实这部散文集中文章篇幅普遍较长,而描写的对象基本以人为主,但既不是人物形象的素描,也不是生活的截面和片段。在书写中,你似乎执意将每个人的一生或至今为止的大半生写尽。
傅菲:收入集中的单篇以长叙事为主,或以扇形、多声部展开阐述,或以单线、长调式贯穿始终。你很细心,这个“发现”属于你。我是这样想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史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地方史或地域文化,在时代的作用力下,会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留下深痕。个体的人是时代的一个横切片。个体的人,在相对的时间长度下,方可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张力。
记者:这一组刻写中,可见村落乃至山林的斗转星移物事变迁。可以望见的是旧人物、旧习俗的远去,但却不见萎颓之气,也不见凋敝之感,是否是身为写作者进行了过滤,还是出于其他的思考?
傅菲:《元灯长歌》分四小辑,第三辑“万物生动”着墨村落与山林的物事变迁。我没有刻意过滤。我表达的主要观点之一是:人与动物之间,有高贵的情感。其实,这个系列,我写了数十万字,以写人性和自然道德。
我们的自然文明在叠加、叠高。这是时代最大的进步之一。乡人的观念在转变,摒弃了很多旧习俗、旧恶习。《敏秀的狗》直接取材于我村中的生活事件。我必须讴歌高贵的生命品质。
记者:书名中的“长歌”,也贯穿于多个篇目——这片土地上的人习惯于用歌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以歌祭奠、用歌感怀,其中像提灯师傅这样的人,用歌来迎送生与死,枯与荣。是否可以说,在这里,人类经由歌咏与万物相连,这其中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契约”?
傅菲:“歌”是一种情感表达方式,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元灯》《盆地的深度》《画师》《墨离师傅》等篇,都有“歌”的吟唱。
在赣东北的乡村,祭奠、祭祀、庆丰收、婚嫁、重体力集体劳动等日常生活,均有“歌”“登场”。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在这里,人类经由歌咏与万物相连,这其中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契约”。
“歌”既是乡人的“诗”也是乡人的“哭”,他们以“歌”赞美自己的生活和土地,以“歌”赞颂自己的时代,以“歌”哭诉自己不堪的命运,以“歌”诅咒痛恨的旧社会。这种特殊的“契约”,既与万物相连,也与生命相通。
书名中的“长歌”,还有另外两层意思,一是生命长调,二是盛世之美。
记者:讲人生,就不可避免地写死亡。从书中人物的生老病死,到旦旦师傅、墨离师傅,还有画遗像的画师等人,在他们身上可以说集中表达了村人的生死观,也表达了作者的生死观。
傅菲:生命有时很悲凉,但死亡有时并不给人悲观。死亡不是生命的消失,而是不以肉身显现。
评论家胡颖峰曾说:傅菲是最关注死亡的当代作家之一。这是胡老师的一家之言。我承认,我非常关注个体生命。死亡是个体生命的终点站台。我写死亡,其实也是写生命。一个人的临终状态,是一个人一生的浓缩体现。生死观也是生命观。人被自己的生命观指引。
记者:在对于人物的刻写中,书写上也引入了小说的笔法,从客观叙述到主观描绘都有涉及,这对散文而言是一种书写范式上的更新。其中是否有尺度所在?
傅菲:散文作为一种开放性很强的文体,探索散文的边界,一直我努力的方向之一。我对文本的探索,作过十余年的努力,从篇幅、结构、语感、句式、抒情与叙事方式、形式等方面,有过非常多的尝试。引入其他文体的写法,也是我尝试的诸多元素之一。《元灯长歌》在多篇多处引入了小说笔法,以丰富意蕴、丰满人物,为文本注入生机。在散文中,不引入小说的笔法,无法完成扇形结构的写作。散文需要丰富性。丰富性就是多样性和完整性。
我有自己严格的尺度,即:不脱离真。真是本真、真诚、真实。本真是情感、心性。真诚是态度、质地。真实是符合生活逻辑。
记者:回到作为散文书写的层面,《盆地的深度》开篇那句话很让人深思。我们总说以书写抵抗遗忘,对于多年执守散文书写的你而言,这种“抵抗遗忘”是否有更多的含义?
傅菲:“这个世界,以前发生了什么,现在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得十分有限;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更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遗忘的一部分。”这是《盆地的深度》开篇部分。非常感谢你把这句话作为我散文写作的“启示录”。我以自己的开篇语回答了我为什么写作——写作是对时间的抗衡方式之一。
“抵抗遗忘”是对写作者的最高要求——写出高度艺术化的时代文本,写出珍贵意义的特质文本,写出深刻反映时代特征的经典文本。做到“抵抗遗忘”,非常难。我还做不到,虽然我很努力。或许我终其一生,也无法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