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北京作家的书面语言和口语其实是高度接近的,用什么语言说话,就用什么语言写作。它很生动,很有画面感,但在进行思辨的时候,这种语言往往会深不下去。我现在对北京语言的想法,除了继承它的优势,更多地也会考虑补上它的短板。 石一枫:整合京味小说的优势与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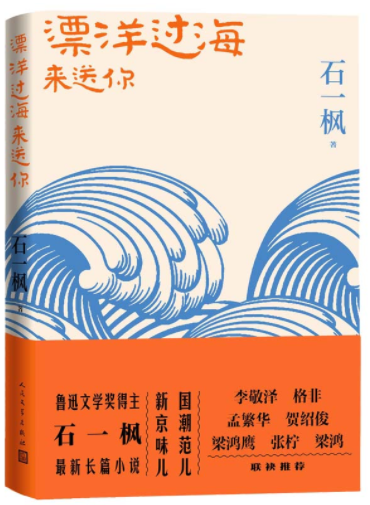
《漂洋过海来送你》,石一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68.00元
在长篇新作《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石一枫将笔触落到了北京胡同里的“原住民”——主人公那豆自小跟爷爷相依相伴,在胡同平房里生活。爷爷陡然去世,让他心中的悲痛无法释怀,偏偏此时又意外在骨灰中发现了一块似乎不属于爷爷的“异物”。
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决定一探究竟。《漂洋过海来送你》写法举重若轻,欢快好读,小说折射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从爷爷辈的保家卫国、工厂转型,到孙子辈的漂洋过海、世界互联,截然不同但又彼此支撑的生活,既有京味儿小说幽默大气的底色,又写出了新一代青年的个性。
中华读书报:这个故事如此超乎人们的想象,题目这么浪漫,内容如此荒诞,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在逻辑。能谈谈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吗?
石一枫:故事的缘起还是挺简单的,写故事的人都知道,往往一个看起来很繁复的故事,其实来自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就跟音乐一样,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就是四个音,然后敷衍出一个交响乐。像骨灰盒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有一次看电影,当时看到有一幕,一个家里孩子死了,父母把他的骨灰领出来,从窗口递出来,当时我就有点儿走神,就想怎么就知道这个骨灰就是这个人的呢? 假如说弄错了,那怎么办呢? 会不会是另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把这个动机给扩展,来看看能不能多装进去一点儿东西。也比较幸运吧,还真是能够装进一些东西,有时间的,有空间的。时间的就是从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空间有美国,有中国,有阿尔巴尼亚。东西能装进来,我就觉得这还算是一个有点儿意思的故事了。
中华读书报:爷爷去世后,那豆在骨灰中意外发现了一块似乎不属于爷爷的“异物”。漂洋过海也要换回爷爷的骨灰盒,那豆的执念中,除了对爷爷的感情,似乎还包含了更多?
石一枫:从人物自身来说就是感情。一个北京小孩儿,你说他能有多深的想法呢? 他只能跟着本能走,本能就是亲情,是他想当个好孙子那份执念。我觉得这个是极其朴素的,因此也是不容怀疑的。当然从旁观的角度,假如能够看出更多,对于我来说就是意外之喜。你可以解释成把世界放置妥当的这么一种理想主义,比如就像张爱玲在一篇文章《论写作》里引用的申曲,文官提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那是一个整饬而光明的宇宙。当然有人把它理解为一种面对纷繁世事的战斗精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对作者来说,我反而应该少考虑一点,我其实只想考虑人物本身的层次。
中华读书报:小说也写了老北京的礼数。爷爷和李固元这两个劳模,身上有很多传统的老一代人的优点,舍小家顾大局,有家国情怀,诚实守信,也写了老北京人身上朴素的生活观点。你如何看待老北京的传统?
石一枫:北京人的性格,一般人都会觉得他们比较贫,吊儿郎当的,随遇而安的一个状态,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还是表象吧。在比较传统的北京人、也是比较传统的中国人的概念里,仁义理智信的东西还是挺多的,表现得也比较朴素。比如说小说里的这个爷爷心中,其实就是俩词,一个是讲理,一个是要脸,这辈子就为这两条活着,他觉得人要没有这两条人就不是人了。说到底还是最朴素的好人的观念吧。我觉得这个层面上的优点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因为爷爷经历过共和国的年轻时期,那个特定的时代赋予了他们特定的观念,而这些特定观念在今天仍然起作用,或者我们希望它仍然起作用。
中华读书报:在探寻爷爷骨灰的过程中,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像看侦探小说一样扣人心弦。在你的小说中,“好读”和“纯文学”这两方面从不矛盾。你是否掌握了一套特别的小说技巧?
石一枫:这个评价让我非常欣慰。假如读者能够津津有味地看完小说,我就觉得我那点儿辛苦没白费。至于说好读这事儿,我觉得好的纯文学大部分都好读。像《百年孤独》《第22条军规》,那些都是可以一口气看完的。中国有很多小说,像《围城》啊,《红楼梦》啊,往往都是随便翻开一页就能接着往下读。好读跟纯文学肯定是不矛盾的,或者说得极端一点儿,假如读者觉得不好读,你还得教他读,教不会就说人家素质低,这种肯定是有点不负责任。现在大伙儿都挺忙的,人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看你的小说,你还折磨人家,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小说技巧本身的作用有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应该有热情,你对生活有热情,才能唤起别人对作品的热情。另外就是在写作的时候别那么自我,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别人看着会不会难受,别人会不会看不下去? 这些问题和能否完成自我表达同样重要。这可能也跟性格有关吧,甭管跟谁在一起,我都不希望共处的那段时间尴尬难受,大家应该愉快一点儿。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写到,按照那豆的看法,爷爷纯粹就是图个“玩儿”。“玩儿”是北京人尤其是胡同里的北京人先天都有的基因——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北京人对于“玩儿”的态度和精神。尤其是“在诸多可玩儿的物件里,唯有这嘴百玩儿不厌、随玩儿随有。玩儿鸟玩儿多了鸟还累呢,一张好嘴却永远能够花样百出。”你对于“玩儿”的态度是怎样的?
石一枫:关于玩儿嘛,可能对于北京人来说就是一个传统项目,或者是性格里带着的东西。他对什么都可以不太认真,眼里没什么太严肃的事儿。也可能是因为大事儿见多了,有苦事也有不平事,再没点儿这种精神,日子真是没法过,情绪会崩溃的。这说起来就有点儿悲凉了。另外具体说玩儿嘴,爱说话,非得把话说出花儿来,有人觉得可能是语言炫技,我理解倒也是一种无私,就像前面说的,他不希望跟谁在一块儿的时候让人家尴尬难受,他希望跟大家都愉快,所以他宁可自我牺牲多说点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怎么就那么多年还一直玩儿下来了呢? 有其内在机理。
中华读书报:酱油厂、殡仪馆对你来说都是陌生的场所吧,如何写得这么真实可信,是去实地考察过吗?
石一枫:殡仪馆肯定是去过,但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不过这就涉及到一个写小说的基本功课吧,就是资料。作家的生活圈子实际上是很小的,作家作家,都是坐在家里,但是鲁迅又说过,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你有关,所以你要写什么东西一定得把资料做齐了。一个是为了避免硬伤,另外就是增加感性认识。你对一个地方有了感性认识,写它才是活的。这个是写了这么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一点儿经验。写作的领域变得越来越宽,那么你的资料肯定是要越做越足。随着写作的时间变长,这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工作了。酱油厂肯定也是这样,你会吃酱油,但是你不一定懂得酱油厂到底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北京城里的一个酱油厂,它会经历怎样的典型命运? 这个都得研究。小说里写的胡同我自己去转一转,通过走马观花就能积累起认识,但是说像很多别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要扎扎实实地研究。您能看到这种区别,其实是看到了一个作家写作的机理内部了。
中华读书报:你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北京人,和老舍等人京味小说有哪些一脉相承之处? 或可谈谈你觉得自己的京味小说有何特点?
石一枫:京味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北京作家的书面语言和口语其实是高度接近的,用什么语言说话,就用什么语言写作。这种特点当然有它的优势,就是表形的时候非常有效,它很生动,很有画面感。但得承认缺点也有,我觉得在进行思辨的时候,这种语言往往会深不下去。这方面反而是南方作家做得好,你看鲁迅的东西就是往深里走,跟鲁迅本人有关系,跟他的语言也有关系。我经常也听南方作家说他们写作的时候,因为口语不是普通话,所以会有一个翻译的过程。但恰恰就是这么一个翻译的过程,他对一句话的意思往往比我们北京人多想了一圈儿。写东西多想一圈儿,少想一圈儿是能看出来的。我现在对北京语言的想法,除了继承它的优势,更多地也会考虑补上它的短板。
中华读书报:在《漂洋过海来看你》中,父子的关系、爷孙的关系都是暖的,爱情却是模糊的。你觉得呢?
石一枫:这个小说我觉得主要的情感还是祖孙之间的亲情,当然这种隔辈儿亲的亲情也许有着更复杂的含义,可能是历史或者社会变化的缩影。像爱情处理得比较模糊,我倒觉得是正常的,我们现在的人一天到晚在说爱情,但这种情感在你的整个情感体系里占有的位置并不是非常的大,即使它表现出来,也肯定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么纯粹。有时候它是一种被裹挟或者被掩埋的状态,就像郑老师和姚表舅那种,有的时候它干脆就是引而不发,像那豆和阴晴这种。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吧。最初倒也没有太多设想人物的情感应该是含蓄的还是鲜明的表达方式,写到那里让人物自己选择就行。相对于情感上的抒发,我更愿意在这个小说里探讨的是命运以及价值观的纠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