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历史活在永恒的当下
每年四月,许多人在社交平台引用了艾略特经典长诗《荒原》的开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2022这一年正好是《荒原》问世一百周年。
《荒原》是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代表作,其出版被誉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1922年10月,《荒原》首发于艾略特自己主编的季刊《标准》创刊号,同年底在美国出版单行本,艾略特还在单行本中加入了五十多条注释。
在四月,澎湃新闻记者特就《荒原》在中国的接受史、它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它与当下的关联等话题专访了几位中国诗人,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是批评家、作家、学者、译者、文学期刊编辑。
此文为诗人、同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桑就《荒原》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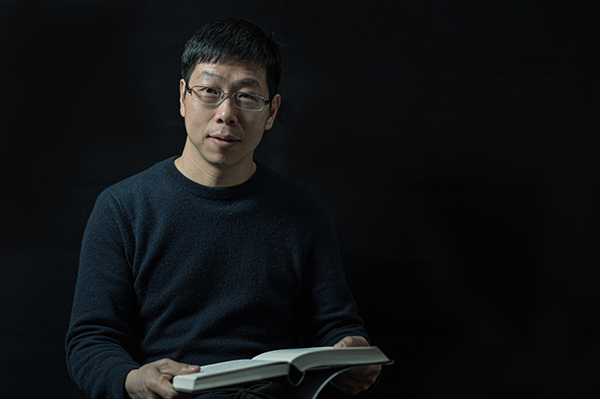
胡桑
澎湃新闻:《荒原》这部西方经典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胡桑:《荒原》发表后不久就传入了中国。1920-1930年代,很多中国诗人通过读英文版接受了影响。赵萝蕤的老师叶公超等人率先介绍了艾略特的诗学。在当时的中国,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荒原》冲击波”。“荒原意识”渗透到了很多中国诗人的写作中,比如闻一多的《荒村》、卞之琳的《春城》、何其芳的《春城》。中国诗人从“荒原”意象中看到了现代世界的困境、现代性的病症、现代人分崩离析的伦理处境。特别是赵萝蕤应戴望舒之邀,翻译《荒原》,于1937年在新诗社出版,再次推动了这首长诗的影响。赵萝蕤的译文吸收了1930年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成就,她的丈夫便是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她又继承了神学家父亲赵紫宸的家学,对圣经语言尤其是和合本语言十分熟悉。这些造就了《荒原》译本语言的蕴藉、舒朗、精准。这是一个出色的译本。这首诗对九叶诗派诗人来说举足轻重。对于他们而言,《荒原》是去个人化、智性化写作的典范。
澎湃新闻:此后《荒原》在中国经历了什么?
胡桑:1949年以后,艾略特像很多西方诗人一样,被打入了冷宫。袁可嘉在1960年甚至撰文称艾略特为“英美帝国主义御用文阀”。
后来穆旦在1970年代进行重译,不过直到1985年才出版,收入《英国现代诗选》。裘小龙(1983)、叶维廉(1983)、赵毅衡(1985)、杜若洲(1985)、汤永宽(1994)等译过多个版本。《荒原》里的“荒原意识”慢慢褪去,新古典主义倾向得以显露。对经典文本、典故的现代激活方式刺激了很多中国诗人去中国传统里寻找现代性,比较典型的是杨炼的《诺日朗》。其实,海子的长诗里也能看到《荒原》的痕迹。
到了1990年代,中国诗歌不再满足于无论是语言的还是精神的宏大叙事。日常性和叙事性变成了变革的方向。此时,《荒原》里日常生活的象征式书写、对生活片段的叙事性处理启发了王家新、萧开愚等众多诗人。我们可以在萧开愚长诗《向杜甫致敬》(1996)里看到《荒原》里对当代日常生活片段的提炼。
澎湃新闻: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到了《荒原》,当时有着怎样的感受?
胡桑:我在1997年读到一本王家新、沈睿编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诗集《最明亮的与最黑暗的》。里面收了艾略特几首诗。只是可能因为《荒原》名声太盛,反而没收入。我第一次读到全本《荒原》是在2000年,我来到西安读大学。在书店里,淘到了赵萝蕤译文自选集《荒原》。让人惊讶的是,在序言里,我发现,赵萝蕤是我同一个镇的老乡。她1912年5月9日出生于浙江德清县新市古镇四平路1号,当时是一家米行,米行在她祖父手里已经逐渐败落。她家就在我从小去吃馄饨的平桥旁边。不过,后来我知道,1992年,赵家三进院落由赵萝蕤的堂妹拆除重建成了很当代的砖瓦房。
当时读完《荒原》,由于知识储备的不足,对它充满了疑惑。不过,里面的幽暗、荒凉、欲望和凌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来源于《金枝》里的圣杯、鱼王传说。后来,为了研读《荒原》等诗歌,我专门从外网收集了很多艾略特的英文诗,打印成了一本艾略特诗集。当时的打印费特别贵,是一元一页,那是22年前的价格。通过长时间研读英文版,慢慢地我更能理解这首长诗了。它对时代的命名能力以及对当代世界认知的丰富性是惊人的。不过,由于我个人的写作喜好,对其过于强烈的智性化、典故的繁冗略有不满。也就没有倾心于它,没有学到太多技艺。
澎湃新闻:后来呢,对《荒原》的读后感发生了变化吗?
胡桑:确实,当我从西安回到江南后。对艾略特所写的一些片段却更有感触了,尤其是那句“大半个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到南方。”我必须重新体验、理解这个我度过了漫长童年少年时光的“南方”。我特别喜欢赵萝蕤的译文,很多句式、语调也会无意间会渗透进自己的诗句。比如被他激活的瓦格纳的句子“荒凉而空虚的是那大海”,但丁的句子“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那么多人”,我都深有感触,也偷偷模仿过。
这些年我在大学教书,从没有想过要给学生讲解这首诗。但随着对圣经、但丁、莎士比亚等人的不断研读,其实更能体会到诗中对典故的化用的鬼斧神工,也更能明白了它从西方传统里滋养出来的生命力量。于是越发觉得他具有强大的创造性,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深刻体认。这些是我们的诗歌难以企及的。这些年,我也越发感觉到了艾略特的伟大,和一再重读的必要性。
澎湃新闻:为什么没有想过要给学生讲解这首诗?
胡桑:我可能觉得它太难了。除了在知识层面的讲述,我不太能把握讲述这首诗的路径。这就像我在课堂上没有专门讲解过《尤利西斯》,虽然我一直认为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平时我也一直研读着。但总觉得没有准备好去给学生讲解。
在课堂上讲授《荒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这样丰富的一首诗,细读会显得极为繁琐。而我最喜欢以细读的方式讲课。我觉得本科生最需要一种细读能力,在字里行间锻炼理解作品的能力——感受力、认知力和想象力。
还有,艾略特本身是极好的批评家。但在我阅读视野里,比较经典的,除了海伦·加德纳的《艾略特的艺术》之外,西方学界对于艾略特的批评、阐释并不丰富。大学课堂的讲授是需要知识基础的。在没有西方一流学者、批评家的阐释基础,我不敢擅自解读。我之所以敢和学生讲《神曲》、莎士比亚悲剧,是因为我可以借助西方大量的经典的但丁、莎士比亚阐述。毕竟我们和西方文学有着语境之隔。我更相信他们语境内部的学者、批评家阐述的准确性。
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艾略特给这首诗做了太多注释,反而限制了读者的阅读方式。解读它,就没有解读但丁、莎士比亚时那种可以不断做出新的发现的愉悦。
澎湃新闻:你和诗友们讨论过这首诗吗?
胡桑:不太多。对于我和朋友们而言,《荒原》就像一个庞然高峰,它默默矗立在那里。我们可能会一个人默默攀登,不适合组团一起登览。其实我们这二十年,谈论的诗人里,艾略特的诗是往往缺席的。我们可能经常谈论他的文论,尤其是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或者他对但丁、莎士比亚、玄学派诗人的阐述。由于艾略特的保守主义倾向,他的诗的“现代性”尽管很有特点,却不是特别明显。他诗歌中的语言的和情感的激情也并不强烈。所以,在外国诗歌方面,我们谈论最多的大概是布罗茨基、希尼、沃尔科特、毕肖普、策兰、米沃什这些诗人。
澎湃新闻:你认为《荒原》对你,以及你这一代中国诗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胡桑:刚开始,我对《荒原》中的宏大的命名能力,对经验的提炼能力,对当代生活的复杂的洞察,是不太能理解的。理解它需要太多的智慧,或者说是成熟的心智。
艾略特对于我这一代诗人的具体写作,我的感觉是影响不大的,因为我们最初进入诗坛的是反叛宏大叙事,要去建立和具体生活的直接性和肉身性,对个人体验的真实性是有强烈的渴望的。而艾略特恰恰提倡传统和历史的重要性,要求诗人“去个人化”。在这个方面,其实他的文论对我影响更大。当时我本科时在陈越老师的课上,听他讲解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深受启发。此后,不断会不断重读这篇文章。我在自己从事批评写作时也会经常引用艾略特这篇文章。在诗人与传统重建联系这一点上,艾略特对我影响太深。我的诗歌里也开始重新处理对中国古典诗歌某些因素的挪用和激活。比如我写古代诗人那个系列《孟郊:仄步》《赵孟頫:寓形》《姜夔:自倚》《吴文英:须断》《叶小鸾》等,一直想到艾略特的教诲。
来到上海后,我慢慢不再关心如何去构建一代人的写作方式,而是更关心个人声音的建构和汉语诗歌的未来。这个时候,艾略特对时代经验的命名能力,对历史记忆和文本经验的引用能力和更新能力极大地启发了我。我从组诗《惶然书》开始,诗歌中的“荒原意识”其实是加强了。每当我写到上海时,我总是想到艾略特诗中作为“无实体的城”的伦敦。但如何认识上海的当代性,依然难度巨大。我这几年一边关心数字媒介对当代人的影响,又不断试图去命名这座城市的经验,尝试着写下了《内卷时代》三部曲、《空城》等诗。算是对《荒原》的致敬。
当然,这几年我们这一代中国诗人其实都在变化,已经脱去了个人化写作痕迹,对《荒原》式的巨大的命名能力都有一定的理解吧,甚至对超越个人的写作方式、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提炼、命名,对于走向开阔的诗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澎湃新闻:四月,不少人喜欢引用“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你怎么看待《荒原》与当下的关系?我们如今纪念《荒原》,需要纪念什么?
胡桑:“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是裘小龙的译文。我记忆中的译文还是赵萝蕤的:“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一个月”这种具体性对我来说是触目惊心的。诗歌开头的残忍性就在于它是以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具体的事物“四月”为载体的。这个“四月”有那么大的承受力吗?
在大流行、国际战争、难民浪潮、核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的巨大语境中,我们如何看待一个月、一星期、一天和身边一个个具体的人?我觉得,《荒原》里那种虚无感和危机感一直左右着这个世纪。曾经,在我少年的新自由主义语境里,我以为,《荒原》只是一首象征感强烈的诗。但这两年我才明白,这首诗就是我们的现实,它一直在我们的空气里飘荡着。它通过引用经典观看当代生活的碎片,激发对当下生活的想象力。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观看”,或者,用本雅明的说法,引用文本,就是引用历史。引用历史,是为了烛照我们当下的生活。在我们置身于荒原的时候,我们需要历史的镜像装置来帮助我们重建“观看”的能力。《荒原》一直在提示我们,如何引用过去,如何看到历史活在永恒的当下,看到我们对时代的记录会成为未来的记忆。同时,我们害怕词语变得轻浮,对记忆的去向听之任之,被人窃取、涂抹、屏蔽,借用艾略特在《荒原》的词句来说,我们害怕自己的言辞成为“野蛮的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