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命的共鸣,让我们先倾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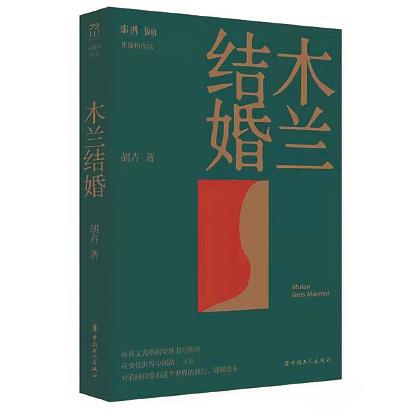
《木兰结婚》胡卉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上海朵云书院位于上海中心大厦52层。从这幢巨型高层地标式摩天大楼望下去,整个上海市区尽收眼底。
2021年岁末,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为《木兰结婚》举办的新书分享会。十五篇非虚构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作者胡卉也是一名女性,1990年生于湖南宁乡,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硕士毕业。上海向来有出女作家的土壤。作为女性,在这座一直有“最适合女性居住”美誉的城市里学习和生活,着手写一些女性的故事,似乎是一种特别自然的事。
但年轻的胡卉,聚焦的却不是传统意义上都会摩登女郎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她书写的女性,多来自三四线城市,有的是小镇少女,有的来自偏僻农村。即便最终身处城市中心,很少有鲜衣怒马的都会爱情,也没有职场进击的“大女主”爽剧,她们的外貌和穿着是被隐去的,她们内心的困惑和幽微处的隐痛被推到聚光灯下。她们有的上进要强,但在命运的某个转折下坠,最后遭遇不幸婚姻;有的为爱情奔赴大城市打拼,分手后黯然离去;有的在面对自己婚姻时,不得不重返童年经历的阴影。
面对城市化的进程,面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化,面对来自父母辈的历史,面对两性关系的角力,这些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艰难也顽强地用自己的经历写出答卷,其中并不包含任何英雄主义的成分,而只是一种诚实,胡卉用文字的形式尽量诚实记录了下来。在写作的几年里,胡卉也经历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变化。书写别人的过程,也成为她面对自己人生的观察维度。结集为书后,这些故事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木兰结婚》。
胡卉说,其一是因为有一篇文章中的女主人公名叫木兰,其二也是因为木兰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关于女性形象的特例。
木兰从军,她既遵循忠孝节义,也反叛传统。她离开家庭走向战场,和男性并肩作战,直面困境,也依旧保有对镜贴花黄的温存。在看到许多个人挣扎却不能超越自我的故事后,在体会了许多女性无人分担无处出口的情绪后,木兰依旧代表一种积极向上的方向。在当下一个变革的时代,当找不到一个新的典范去模仿的时候,不妨看看木兰,因为木兰是一个依靠自己的独立勇敢的理想形象。
成为木兰,是一种祝愿。
成为一条声带
读书周刊:什么时候开始写第一个故事?
胡卉:我记得是2018年六七月份。当时一位媒体的编辑问我手里有没有稿子,我手里正好有两篇完成的。其中就有《亲爱的红豆》,对方觉得挺好的就开始约我写,我也就一直写下来了。
读书周刊:《亲爱的红豆》讲述的是一起虐童事件,让本来在稳定工作轨道上运行的母亲生活巨变。这是你在复旦读书时的习作,还是毕业以后遇到的故事?
胡卉:是毕业以后遇到的事情。我在湖南长大,在山东念本科,到上海念研究生,毕业后在深圳工作过一段时间。几乎每年都会自己进行一两次旅行,也曾经在新疆和西藏住过半个月,会把自己遇到的人写下来。开始正式接受媒体的约稿后,我就会自己寻找选题,然后出差,去年去了浙江、广东佛山还有安徽采访。
最近我在写一个发生在监狱里的故事。采访时间拖得挺长,从去年9月份开始做,主角也是一个女性,她作为导演到监狱里指导服刑人员,排一出戏。参加这样的艺术演出也是对服刑人员进行矫正教育的一部分。之前我对监狱完全不熟悉。因为这个机会采访了一些已经出狱的服刑人员。
读书周刊:是为了写非虚构而第一次接触有服刑经历的人吗?
胡卉:倒是不算。因为原先在我们老家那边遇到过有这样经历的人。我知道有一个家庭,男人是服过刑的,出来后去相亲,没想到一看女方也有过服刑经历。女方的爸爸不放心,就让自己的儿子去看看情况,没想到相亲男就和这未来的小舅子打起来了。可以想象他性格的冲动。但我并不是要说个体,我这次是想写服刑人员这样一组群像。
读书周刊:你现在从事非虚构写作已经三年了,你觉得和你一开始时有什么区别吗?比如在采访的时候,在挑选选题和选定人物时?
胡卉:嗯,我觉得,我会更耐心一点。
读书周刊:耐心。
胡卉:对,就是对很多的拒绝、沟通的失败还有不能完成的选题会更习以为常。
读书周刊:你会有意识去警惕自己,落入某种猎奇或者窥私的这种角度?
胡卉: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我不觉得这些是猎奇,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都是普通人的事情。我可能是反而要警惕好奇心不足。我感觉是,每天有那么多的选题可以写。我反而担心自己会在这么多可以写的选题前面,变得无感跟冷漠。
读书周刊:我们看《祝福》里面,那些老妇人会特地去找祥林嫂,听她把自己的悲惨生活再讲一遍,陪她掉一下眼泪,你会害怕自己会落入这种状态吗?
胡卉: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通过看别人的悲惨的事情来获得自己精神的愉悦。
读书周刊:那么当你去写边缘人物,尤其是女性的生命困境时,你觉得你的角度在哪里?
胡卉:我觉得应该是把他们当作我自己的事。
读书周刊:全部当作你自己经历的事?
胡卉:对,因为我也来自农村,小镇是一个熟人社会。我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生活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完全也能发生在我身上。
读书周刊:新书分享会上,似乎也有一个读者问,为什么你要挑选写这些悲伤的故事,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呢?
胡卉:我当时一下子不太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不在一个处境里谈论事情,可能会发生误读。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角度。我在网上看到读者对《木兰结婚》的一个短评,说:
“胡卉既没有采用一种对比或自省的姿态在写作,也没有站在幸存者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假意关怀,没有介入式地冒犯,更没有用文字轻佻地将那些幽暗隐秘的真实包装成廉价煽情的地摊故事。”“胡卉完全进入了她笔下的女性生命中,成为她们温柔又坚定的声带,让那些原本可能会被历史车轮声所淹没的微弱呢喃,那些时代洪流中沉默群体的艰难喘息,被我们听见,被世界听见。”
读书周刊:你觉得他说出了你的想法。
胡卉: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贴近我本意的。我没有试图从我采访的对象身上找一点经验教训。我也不能提供一个女性生活的范本。
面对生命的共鸣
读书周刊:你最初比较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写作的冲动是什么时候?
胡卉:我想应该是从《春晓》那篇。春晓是我刚到上海时,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工作时认识的朋友。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上海打拼,面对的处境差不多。春晓是为了追随男友到上海来,但被男友分手,最后只身前往孤岛,又遇到了一些情感的波折。我写完后也给春晓看,但春晓反而说,那些我很在意并觉得很重要的事,对她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和伤害。
后来春晓回到老家后,结婚生子,过得安稳。那时我想,文章的体量有限,其实不能完全展现一个被书写的人之后人生的走向。也不能展示一个人全部的精神力量。
在复旦大学学习创意写作时,我们上过非虚构写作课,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老师、青年作家张怡微说过,有时人们会放大女性之间的竞争和敌意,但其实女性之间的义气和友谊值得书写,女性之间有产生凝聚的渴望。我后来意识到,其实我写作的一个动力之源就是,我想去写女性之间的友谊,女性面对生命困惑的共鸣,以及这份凝聚力所产生的力量。
读书周刊:你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吗?
胡卉:我还有个弟弟。我爸爸是个手艺人,我妈妈是家庭主妇,主要照顾我们和照顾家里的庄稼。我爸爸在农忙的时候也回家帮忙料理农活,平时外出帮人盖房子。在当地,我们家收入还算不错。我也没有在经济上吃过什么苦。
读书周刊:作为姐姐,要帮忙分担家务吗?
胡卉:应该是要的,但因为我读书挺好,所以父母也都很保护我,不让我干活。我记得大概在初中的时候,我和父母一起下田,当时赤脚,很害怕蚂蟥,就拿着一束秧苗站在地里哭,我父母也没有责怪我。那就算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田了。
读书周刊:挺被呵护的。
胡卉:是啊,我没有被打或者被责骂的经历,也没有重男轻女的这种创伤,现在回想起来,家里对我的都是宠爱,尤其是家里的老祖父对我特别宠爱,想起来童年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老家,那里背靠山和树林,有很多果园,前面就是田野,有河流,有稻田。早上传来卖鱼小贩的叫卖,我就写到作文本上。到了新世纪后,几乎每家都盖起了楼房,周边的环境也很好。我爸爸是木工,给我们自己家做设计,然后盖楼。然后我妈在家,喂鸡、养鸭、种菜,非常单纯。
读书周刊:听起来挺桃源的。
胡卉:是挺桃源的。但是我后来找了个对象,是我们同乡的,他说他记忆里,小时候家乡还会发生械斗,感觉生存非常艰难。
读书周刊:是不是还会挺惊讶的,和你如此亲近的人,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感受与你截然不同?
胡卉: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冲击。尤其是当你自以为很熟悉的事,在看到反转的一面后,这样的冲击会更大。
就好像我写《消失的女友》这篇,主人公是我熟悉的发小,她非常开朗,常常笑。但是我外出读大学几年后,回来看见她,她已经是在精神病院了。我去看她,她隔着桌子坐着,完全不认识我了。我去了解她经历了什么,如何被疾病和欺骗摧毁,我感到难以置信又痛彻心扉。
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她还住在我家,每天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她的命运也完全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很想问问,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但没有人能回答我。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梦见她,却看不清她的脸。写她的故事,我写得有粗糙的地方,但我写很快,也很心痛。
读书周刊:去年电影《我的姐姐》上映时,引起许多人共鸣,我看许多影评里会有人留言,讲自己亲历的或者目睹的对女性的剥夺,以及对这种剥夺的默许。
胡卉:这的确是现在大家在关注的话题。女性在清洁、育儿、烹饪、购物等每一项家庭劳动指标中承担的比例都比男性高。《木兰结婚》里也说到女性的牺牲和付出。这是一个一直都存在的现象,现在受教育的女性也多一些了,大家开始更多关照这种生存状态。但谈论这些话题的,还是以一线城市受教育的人为主。
而且,虽然我写的人物都是女性,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只和女性有关的问题。生活本身是艰难的,人如何借助自身力量和外部力量突破自己的局限,是男女都遇到的主题。事实上,即便是在一个最小的社会单元,比如说家庭里面一个女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丰富,对男性也是一种滋养和鼓舞。新书发布会上,我的导师梁永安老师来做我的嘉宾,他说的一句话特别好:
“女性不缺力量,但是特别缺对自己人生权利的一种清晰的认识,以及去维护它、坚持它的意识。”
一个寻亲的人
读书周刊:我看到你在采访时,会飞去主人公生活或者事发的现场,还会把遇到的河流、田野都用手绘地图画下来。你说过,当你采访当地的饭店老板、酒厂保安、卖爆米花的大爷时,他们没把你当成一个采访者,而是把你当成了来“寻亲”的人。寻亲这个词,很特别。
胡卉:非虚构写作的基础是不能虚构。所以我想尽量还原现场。但即便是到现场,从不同人不同角度来看,还是会得出不同的感受。在面对采访得来的素材时,选用哪些不用哪些,也还是要做一个取舍。
我想,我不论是学科的专业基础、采访所得,还是包括个人的阅历都很有限,我不想去选边站队发出议论,我只是想把各方的意见倾听、记录、呈现,让读者从中得出自己的判断。包括写《木兰结婚》这本书,我的编辑和老师也说我,写的上一个人,和下一个人,好像完全不同,甚至有时还是相悖的。我觉得说得很对。但也许我以后会有一个更为统一的观点贯彻一个作品,但目前来说,我还是倾向于让人物自己开口说话。
读书周刊:想问问你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是否对你有很大影响?
胡卉:我挺喜欢这本书,我在大学里看的时候,在书上划满了线条。看《冷血》,他会让你哭,他会让你有想法,他的文字也特别好,但是读这本书时的沉浸度,肯定不如看他的小说。我想,这是非虚构的本质决定的。
读书周刊:你写小说吗?
胡卉:以前在学校念创意写作时,也会写诗歌、小说。但我感觉目前还是写非虚构更适合自己。
读书周刊:发微博和短视频吗?
胡卉:我现在每天还是看视频的时候要少一些,看书的时候特别多。我觉得书里的世界已经非常有趣了。不论外部世界时兴什么表现形式,我想人还是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如果说我落伍,那就让我落伍吧,我是这么想的。
读书周刊:这个世界上有像豹子跑得这么快的动物对吧?但它也容得下很慢的蜗牛。
胡卉:是这个意思,对,这个比方非常好。这个世界太丰富了,可选择的东西也太多了,我还是想从自身出发。
读书周刊:最近在看什么书?
胡卉:我最近手头在看的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康复的家庭》。作家有好几个健康的孩子,但他的长子是有智力障碍的。大江健三郎对这个残疾多病的孩子描写最多。我不觉得聚焦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是一种标新立异。
读书周刊:你觉得是什么。
胡卉:是最深的惦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