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另一种新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跟东南大学是南北的两个重镇,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是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挑战它们的是吴宓、梅光迪,他们其实原来也在北方执教,不满意北方激进的气氛而南下,跑到南京的东南大学,以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人为中坚,创办了《学衡》杂志,所以就变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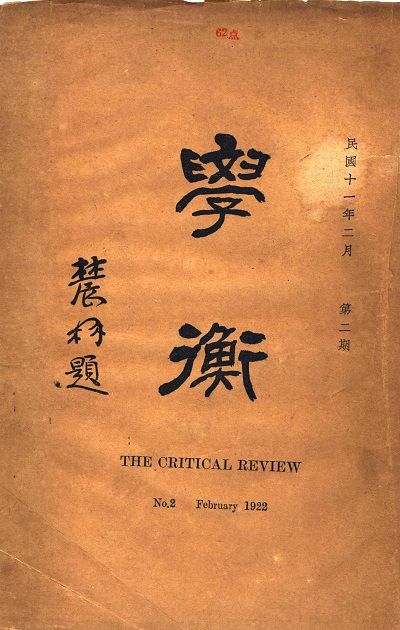
《学衡》
我们必须知道,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这些人文学者并不是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反对北方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但是他们因为反对北方的新文化运动,被视为维护旧文化、拒绝外来文化、反对新文化的顽固派、守旧派。其实,他们明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也就是说他们要保持国粹,也要接受新知,不是像胡适他们那一派就是要放弃旧的来迎接新的。而且这些人的态度是不要“拿来”,而要“融化”。全盘西化论等于是拿来主义,凡是西方的都好,都拿来,而把旧的放弃。所以学衡派实际上代表着另外一种新文化。我一直强调,他们不是守旧派,他们不同意北方以北大为中心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因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是两种新文化运动的交锋。
百年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长时间可以检验真理。在当时所谓“南北战争”的时候,都认为北方是进步的、现代的,而南方是保守的。其实在这场所谓的新旧之争中,真正的守旧派根本没有参与这场论争。事实上,南北两派都是留学生,学衡派像梅光迪、吴宓等人都是从哈佛留学回来的。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南北战争”是两种不同新文化的论争。百余年后回头来看,当时学衡派虽然在论辩上是失败的,可是从实践来检验,它讲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我们可以说,假如他们那些意见在当时能够被接受的话,今天有很多不好的后果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说回头来看,更能理解学衡当时那些主张的价值。

江苏南京,东南大学校园
第一个议题,当然是文言与白话。北方要用白话来取代文言。胡适说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这个就是他要取代文言的原因。文言是死的你还要它干嘛,白话才是活的,所以要用白话来取代文言。南方当然要维护文言,梅光迪认为新旧文体应该承前启后,可以并存。换言之,学衡派并不是反对白话。当然我们觉得白话是很有用的,我们大家到现在看到白话是很成功的,所以不成问题,问题就是说该不该用白话来取代文言。因为白话跟文言不是两种语言,是一种语言,所以学衡派说是可以并存的,“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对学衡派来讲,问题就是“独尊”。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文言跟白话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在形象上,胡适成为识时务者的英雄,而梅光迪则成为反对白话文的不识时务者。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反对白话文,而且梅光迪他自己也经常用白话文,比如他给儿子写信就用白话。梅光迪跟胡适原来是好朋友,亦是同乡,都在美国留学。梅光迪只比胡适大一岁,他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先是到西北大学,后来到哈佛大学,专攻西洋文学,他并不反对白话文。他反对的是“废文言而用白话”,他不认为文学的演变是新文学取代旧文学,而认为是“若古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什么叫革命?就是白话革掉文言的命——等一下我会讲到后果——等于把文言文废掉。废掉的谬误在哪里?刚刚我也讲到,胡适说文言是死的,为什么?他用的词是“dead language”。我觉得胡适英文还不错,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误解呢,还是确实有一定的误解。因为在英文里头,“dead language”是指“已废文字”(language no longer in use),就是说这个语言已经不用了,已经废了。像很多古文字,已经没有人在用了,才叫“dead language”,可是当时用文言的人很多啊,而且到现在还是有人在用——当然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了。最著名的就是钱钟书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用典雅的古文写成。所以文言根本不是“dead language”。
今天看来,用白话取代文言是相当成功的。1920年教育部就通令全国用白话教学,一直持续到今天。大家知道在从前,在前清时代,所谓的启蒙教育就是学方块字,学完方块字就学对联,学完对联就学作诗,慢慢进入文言的世界。1920年以后进入学校体制者与古文渐行渐远,当然愈来愈少有人能写古文、读古文。这样一来,也许真的有一天文言会变成“dead language”。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大家知道,自先秦至晚清,古文乃中国文化之宝筏;无此宝筏,安能登彼岸,以窥中华文化之堂奥?
要废除文言的另外一个原因,胡适讲得很清楚,他说白话容易,文言难。可是我们怎么能用难易繁简来决定文本的存废?文言与白话都是汉文,白话主要是spoken language,文言是written language。我们知道,在英文里头spoken language跟written language也是有距离的,当然中国的古文跟白话的距离比较大一点。你写英文,如果你把讲出来的白话直接写出来,没有人会接受的。所以假如文言不被取代的话,对白话和文言双向都有好处,白话可以使古文除去陈腔滥调而更具弹性,白话可以使文学作品得到普及——这当然是最大的功用,但是没有必要废除所谓的贵族的、美学的、精英的古文。原来照学衡派的看法,可以双轨并行,而且相互都有好的影响。所以用白话取代文言,是不幸的。
第三点,我们到今天也可以知道,白话文被证明是可以成为精致的白话文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写得非常好的白话文。但是我觉得,白话文写得好不好,跟有没有古文的根底很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白话写得好的,都有古文的根底,能够把白话写得简洁明畅。今天我在书店看到很多翻译自西方的作品,打开来看,很多都看不懂。英文原本能看得懂,反而翻译的看不懂,为什么?因为这些译本就是完全用白话,然后根据西方的语法进行拼凑,缺少语言的功底,其实很多可以用大家都知道的well-established language表达出来。所以把古文废掉,不仅枯竭了白话文的泉源,而且涉及到汉文化的宝筏,正如学衡大将吴宓所言,文言乃“民族特性与生命之所寄”。(Mi Wu, “Old and New in China”, in Chinese Students’ Monthy, vol. 16, no. 3, June 1921.)
白话有别的功能,没有人会反对,学衡派也没有反对,但是学衡派特别反对独尊白话文。因为他们反对独尊白话文,被认为是反对白话文,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一点我们是必须要澄清的。刚刚我也讲到,真正的保守派、顽固派根本没有参与,他们的心态很值得研究,到底他们是不屑讨论呢,还是觉得很无聊等等。真正的所谓新旧之争就是《新青年》跟《学衡》两派的争论。幸亏当时没有把汉字给废掉,因为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钱玄同就主张要拼音化,就认为拼音文字是现代的、进步的,世界上大部分用拼音文字,中国的方块字太古老,不适合现代。后来证明,电脑完全可以解决汉字的输入问题,跟是不是现代没有关系。汉字的功用在哪里?有的象形文字被消灭,可是中国这个方块字绵延那么久,而且它的功用我觉得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假如真的把汉字除掉,变成拼音文字,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就像欧洲一样。欧洲怎么样,原来罗马帝国是统一的,罗马帝国的文字是拉丁,拉丁是拼音文字。蛮族入侵以后,德国人用他们的母语来拼,法国人用他们的母语来拼,英国人用他们的母语来拼,就变成法文、德文、英文,所以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一千年演变成为西方的帝国。我在美国教书的同事他们觉得很奇怪,中国汉帝国跟罗马帝国差不多时候,汉帝国崩溃以后,中间大概经过五百年之后,隋唐又统一了,而且比以前更统一,他们说这是一个奇迹。可是我说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功用。我个人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汉字非常好。现在在应用上毫无问题,电脑打字没有问题,像我个人打中文跟打英文根本没有区别,而且这是把中国人凝聚在一起的潜在的力量。大家知道,假如是拼音的话,不但是蒙古人、满人,请问福建人用福建话来拼,广东人用广东话来拼,你看得懂吗?所以每个省都可能像欧洲一样变成一个国。除此之外,汉字还有艺术性。你能用ABC来讲书法吗?书法是艺术品,其他国家一般没有这种艺术。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些,希望大家珍视我们中国的汉字,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汉字的优势,刚刚我也讲过了,现在谈谈学衡派维护文言失败的后果。1920年教育部正式宣布白话取代文言教学,文言日渐凋零。我觉得这个后果已经看得到了。我记得1981年见钱钟书先生,他说现在60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办法写古文。这也许言过其实,但如今确实不免衰退。所以白话没有了文言的根底之后,很容易受到外文的污染,等于是破坏了中文的语言结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白话文写得啰里啰唆,有时候不知所云。此种后果下,不得不令人感念当年东南大学人文学者反对废弃古文、独尊白话的远见。

《新青年》
第二个议题是尊孔与反孔。北方的《新青年》猛烈地攻击儒家,儒家被视为专制集权的渊薮,经书被视为无用的渣滓。学衡派拒绝反孔,主张中西文化会通,反对各种激烈主张。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有个响亮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但是我觉得“孔家店”既然称为“店”,店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好的也有坏的,你要把孔家店打倒,就是好坏通通打倒,所以算是比较极端的。学衡派对此非常反对。当然反孔有它的时代背景,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的核心,而且从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侮蔑、挫败,归罪于中国的旧文化,而旧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儒家。大家攻击孔子,戴上封建愚昧的大帽子,儒家被视为专制集权的渊薮,经书被视为无用的渣滓,所以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在当时,反孔好像变成一种潮流。其实我觉得孔子是替罪羔羊。老实讲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主要不是儒家,而主要基于讲求严刑峻法的法家,而儒家思想多少起了“软化”冷酷专制政体的作用。朱熹曾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答陈同甫书》)所以,说孔子是专制的罪魁祸首,其实并不很公平的。另一方面,儒家道德规范与伦常关系也多少起了稳定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南方文史学者深感难以坐实孔子赞同独裁之罪,更忧虑维持社会的礼法因反孔而毁灭,因此“深膑太息,以为此非孔孟之厄,实中国文化之厄也”。(王焕镳:《梅迪生先生文录序》,《梅光迪文录》,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8年)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儒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灾难。
在这个气氛之下,学衡派力言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儒家的经典经过千年的涵化,就好像基督教之于欧美,成为中国人所尊奉的行为准则。人有行为准则才能异于禽兽,排脱丛林法则,使礼法制度与民生日用随时日进。南雍学衡诸公认为,反孔不只是破坏伦理,而且摧毁社会秩序,因而导致动乱不断,尊孔或反孔更关系到人心之邪正与国家的治乱。现在我们看当时他们这个见解还是很正确的。学衡派认为,儒家经典要在致用。所谓“儒教”,乃儒者的教化,并不是西方所谓的宗教。当然现在有些西方人认为Confucianism也有宗教的色彩,比如孔庙、祭祀等等,可是我们主要讲它的本质应该是teaching而不是religion,所以它提倡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等等,在当时都被认为是一种封建。这是第二个大议题。
第三个议题是全盘西化。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改成“充分世界化”、“充分西化”。名词之异并未改变他一贯主张西化的实质内容。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现代文化和文明都是普及的,并无国界与种界,这是一种“文化一元论”的观点。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保守派排斥西方文化,独尊中国文化,其实与西方派一样是“文化一元论”者,因为他们都具排斥性。康有为追寻放诸四海皆准的大同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一元论”。他说文化是人类的公共的道路,中国为什么现在落后呢,因为在这共同的道路上落后了。中国文化是旧文化,西方文化是新文化,新旧不能并存,这是他们的思维。即使是中西文化折中论也是变相地保持这种观点。胡适去世之前在菲律宾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都不能发展出科学。当时这个观点受到了批评,这是他过世前不久的事情。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终身的信念。我觉得他是把自然科学跟人文学科混为一体了。其实早在17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对此就有详论。维柯将自然科学视为“天界”(world of nature)或“外知识”(outer knowledge),而将人文社会科学视为“心界”(world of mind)或“内知识”(inner knowledge)。他认为“心界”跟“天界”是两回事情,心界或内知识就是他的“新科学”。换言之,文化有意识、有经验、有价值判断,所以不可复制。科技可以照搬,人文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自然界有“客体”可以认知,比如日出东山、夕阳西下,是相当自然的、客观的,不至于有不同的解释,因自然科学的“客体”不涉及个人思考,主体性可以排除在外。不过有人也说,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百分百没有主体性,不过一般讲起来,自然科学是可以排除掉主体的。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如声、光、电,是可以“普遍的”(universal),不因为地区或文化差别而有不同。而文史哲在维柯看来,是心智之学,属于“列国的世界”(world of nations),亦称之为“人间世界”。他显然想要平衡自十七世纪以来专注自然科学与自然法则的趋势,所以所谓“新科学”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性质不同,所以不能够混为一谈。人文社会科学虽然也有它的“客体”,像历史事实,但对此“客体”的认知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观、文化背景,就有了“主体性”(subjectivity)。
Subjectivity这个概念最早从康德开始,后来被所有西方学者承认。有个很有名的史学学者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他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这本书里说,主体性是所有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对此我想大家也都同意的。西方人都承认这个主体性,可能是因为他们文化发达、学术进步,所以他们从主体性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我们要接受,他当然不反对。而且我发现美国的主流历史学家——我所谓的主流历史学家,是指搞欧美历史、西方史学的这些人,在美国研究中国、日本、第三世界的不是主流,也因为他们对第三世界的认知不足,他们非常地藐视除了西方以外的史学,他们当然知道中国历史悠久、材料很多,但是他们说你们没有史学,没有historical conscious。有个很有名的学者,他说写印度、写日本、写中国的历史写得最好的是西洋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站在我们的主体性来立论,其结果是丧失了话语权。我现在有点担心,我看到美国写的关于中国的历史,大家就拼命地翻译,不管好坏都翻译,我怕有一天中国历史的话语权会落到欧美人的手上,当然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人文学科对外界的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均不必见之自然科学。英国很有名的哲学家怀特(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近代科学虽然在欧洲发现,但可以传播到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国家或者理性世界,可是人文学科就不行。我们只要稍微想想,拿史学来讲,我们能够超越过西方吗?绝对不可能。可是我们自然科学可以,我们看到我们造飞弹、造航空母舰,都追上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看看人文社会科学讲到史学理论、文学理论,还是远远跟不上西方,我觉得是无法超越的。这是主体性和话语权的关系。
第四个议题是浪漫与古典。这一点以前人没有讲过的,是我特别注意到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北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但它其实是一场浪漫主义风潮。大家都以为是启蒙,可是启蒙是理性的、古典的。革命要革文学的命,讲国族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浪漫的思潮,不是古典的。这种强烈的文化批判并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激情,诸如“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都是非理性的、激情的革命口号。
大家知道,18世纪是启蒙时代,到了19世纪就进入到浪漫期。假如最简单地讲,启蒙就是讲理性(reason),浪漫就是讲意志(will)。新文化运动,甚至于科学和民主都不是理性的。科学当然很理性,可是他们当时所谈的科学是科学主义。夏威夷大学有个教授叫郭颖颐(D. W. Kwok),她写的博士论文就专门讨论scientism,科学(science)是理性的,可是科学主义(scientism)就不是理性的,崇拜科学、科学万能,这个不是理性思维,而是一种浪漫主义。民主也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可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所谓的民主基本上还是浪漫风潮下的东西,而不是启蒙的。在思想上则是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反动,拒斥学院派而倾向公众,趋向于意志、情绪、民主、权力,回归原始的浪漫风潮。法国哲学家卢梭追求感性,他认为文明污染人性,成为浪漫运动的先知。浪漫风潮开启了以感性为主的文化,与理性文化针锋相对。所以我们看到,南北的针锋相对从某一个层面来看就是浪漫与理性、浪漫与古典的针锋相对。讲到浪漫主义,诚如西班牙艺术家戈雅(Francisco de Goyay Lucientes)所说,浪漫乃“理性沉睡后生出来一个怪兽”。(Tim Blanning, The Romanic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11, pp.73-77.)戈雅所谓的“怪兽”即艺术上的幻想与想像,但亦可泛指整个反理性的文化氛围。所以毫无疑问,新青年在北方是激昂的、浪漫的风潮,文学革命,主张批评主义,要用俗话代替雅文,许许多多新青年的口号反映的全是浪漫主义风潮,所以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它所反映的是当时世界上所流行的浪漫主义。但是在南方,学衡派他们是古典的,他们所提倡的是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就是古典的人文主义,这个也是有来源的。因为学衡派的主要人物梅光迪、吴宓,他们先后到哈佛大学留学,他们的老师就是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白璧德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当时是哈佛教授,但不是当时的主流,所以他的名气远远没有其他人大。为什么?因为当时整个的氛围就是浪漫主义风潮。白璧德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就叫《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他对浪漫主义批判得非常厉害。所以吴宓、梅光迪他们到哈佛,跟了白璧德,思想上沟通得非常好,而且过从非常密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他们来往的书信。而且白璧德也对中国很感兴趣,他认为儒家(Confucianism)是人文主义的,所以他后来跟他的学生创造了一个儒家人文主义(Confucian humanism)。可是这个人文主义没有被发扬出来。白璧德极力反对浪漫主义,他的人文主义就通过梅光迪、吴宓他们这些人的讲述传入中国。学衡派毫无疑问是非常欣赏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的,刚刚我们讲到的这本书《卢梭与浪漫主义》,它谴责浪漫主义为西方文明颓废之源,因其抛弃准则、逾越界线、嘲讽习俗。面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兴起、中下层社会的质鲁无文,白璧德要以教育为手段、文学为工具,挽浪漫主义的颓风,以提升行为规范与社会融洽。白璧德这一思想背景很容易使他欣赏儒家的君子之风、道德规范与重视教育,自然引孔子为知己,笑与抃会。而白氏的中国门生亦因此人文主义,与儒教最为相契而醉心,益增对儒学的信心,深信中华古典与西方古典有可以相通之处,视打倒孔家店者为“鲁莽灭裂”,欲融儒家于新人文主义之中而成为“儒家人文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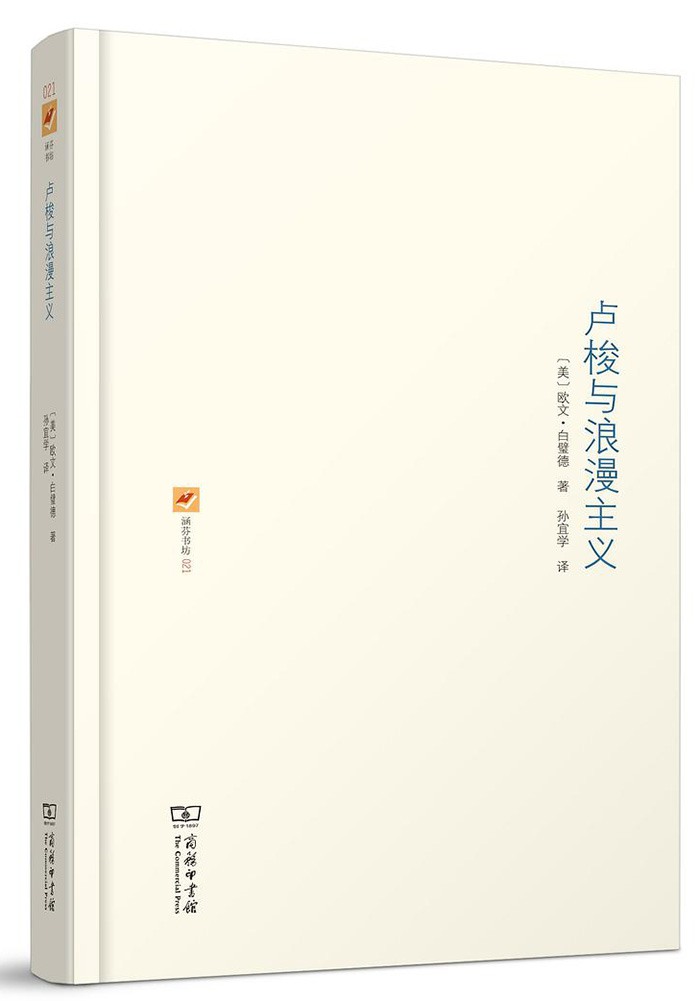
《卢梭与浪漫主义》
毫无疑问,儒家的东西非常理性,所以梅光迪希望在中国形成以白璧德和摩尔(Paul Elmer More)为主导的人文主义运动,成为一个正面而有建设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也提了新文化运动,可是他们的版本不被接受,被接受的是北方的浪漫主义的版本。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南北主张的差异在哪。第一点,北方倡言文学革命,南方主张文化改良;北方提倡“平民文学”,南方则认为不应将精英文学降格为平民文学,而应经过教育来提升平民文学。第二点,北方要摒弃传统,而南方要继承而后改造传统;北方喜新好奇,而南方强调温故知新;北方以普及为能事,而南方则认为学术思想非凡民所能,文化不能依赖群众维持。第三点,北方以“顺应世界潮流”自命,而南方斥之以盲从趋时;北方亟言学以致用,而南方坚持学术乃万世之业,积久而弥彰。很明显,南北间的差异非常大,结果是学衡派无力回天。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南北之争在抗战前已决胜负,北全胜而南惨败。
俞颂华说,“孔子教义,自有其不可诬者”(《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一百多年后来看,这句话是没错的。我们注意到现在大陆国学兴起了,孔子学院林立,证明当年轰轰烈烈的反孔言论与行动至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废弃,要从头来是相当困难的。当年在南京东南大学的人文学者逆势而为,貌似顽固保守,实则择善固执,预知文言之不可废、儒教之不可弃、浪漫之不可久。
百余年后回看,新文化运动以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杂志作者群为主角,影响深远。然而以《学衡》为论坛的南雍诸公,却被认定为反新文化的守旧派,几被遗忘。所谓“新文化”主要来自西方,然西方文化内容丰富,种类不一,固不能以某一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而以另一西方文化批评或反对此一新文化为反对新文化。
白璧德从1912年开始就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与文评家摩尔共同创立“新人文主义运动”(neo-humanistic movement),以“古典主义”(classicism)来针砭奇特的、强烈的、夸张的浪漫主义。白璧德将浪漫主义的始作俑者卢梭视为狂徒,抨击尤厉。梅光迪、刘伯明、吴宓等就学于哈佛文学系,接触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获得另类新文化的认知,他们不是简单的守旧,而是立足于西方古典主义的高度,批判充满浪漫精神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并不是盲目的,就如他们尊奉的老师所知道的那样,中国的传统当然有它的缺点,但是,“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主张“中国旧学中根本之正义,则务宜保存而勿失也”。(白璧德撰、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3期)白璧德认可孔子的人文主义,而且直言较西方更优,更规劝中国新文化运动不可忽略道德、不应信从西方功利主义过深,应合中西智慧使新人文主义的内容更加丰富。南雍诸公尊奉白璧德,坚信新人文主义才是中国应有的新文化。
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重估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应该仔细辨析、严肃批判,认知到北方新文化运动遗产的负面后果:旧学的脐带不绝如缕;古文对一般读书人而言几乎犹如天书;一味追慕西风而乏自主性;重功利而轻人文。当年新文化运动曾在南方花开别枝,却无端被视为反新文化、泥古守旧而弃之,岂无遗憾?今日回顾学衡的主张,或许有助于重构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之图谱。
(本文系节选,原载《新学衡》第4卷《新文化运动的异途》,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