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只“栖息着的鹰”开始 ——特德·休斯文集《冬日花粉》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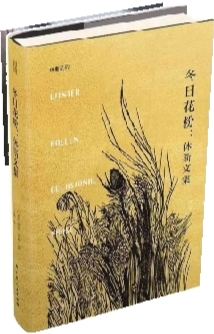
一
第一次接触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的作品还是1994年秋天。那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印数寥寥的《英美桂冠诗人诗选》。英国部分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剧作家本·琼森为起点,以当时尚在世的休斯为压轴。我没去考证,该书选收的11首休斯诗歌是不是第一批休斯汉译,我只记得当时扑面而来的阅读震动,尤其那首《栖息着的鹰》,令人看到休斯与众不同的叙述角度。而且不难看出,休斯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以勃朗宁为代表的独白体诗歌传统。但继承传统,不等于被传统遮蔽,从整部世界诗歌史来看,强有力的诗人往往在继承中破茧成蝶。在休斯那里,将独白转换到动物身上,形成别具一格的“动物诗”,就已显示了诗人对新领域的开拓能量。
独白往往直白,休斯在极为坚决的语调中体现了直白的力度。读过这首诗的读者不可能忘记它既充满寓意,又充满自信和打击力的结尾:“太阳就在我背后。/我开始以来,什么也不曾改变。/我的眼睛不允许改变。/我打算让世界就这样子下去。”这是鹰的独白,也是极其冷酷和有力的本质独白——生活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同时是诗歌和诗人的本质。没有非凡的力量,不可能要求“让世界就这样子下去”。所以,这首诗能成为休斯的名篇,也成为现代主义的诗歌名篇。
这11首短诗为我打开了休斯的诗歌大门,乃至后来在坊间每见一部翻译诗选,我都会首先浏览目录,看书内是否有休斯的诗歌,一旦发现,就立刻翻到他的作品细读。当然,这种情况只偶然发生。英国桂冠诗人的头衔终究不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更引人注目。必须强调一句,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一个诗人的作品衡量不假,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更不是至高无上的标准。在里尔克面前、奥登面前、博尔赫斯面前、弗罗斯特面前、曼德尔施塔姆面前,不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水准就很难说比肩甚至超过了他们。
令我感到惊喜的一次购书经历发生在2001年年初,逛书店时陡然看到一部署名特德·休斯的诗集《生日信札》。我当即买下,尽管诗集名已经告诉我,它不是休斯名震诗坛的“动物诗”集结,但它毕竟是休斯的诗集,自然不能错过。果然,这部诗集不是“动物诗”,而是纪念他妻子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部诗集。从封面上原版“畅销数十万册”的推荐语和译者张子清先生的序言来看,英文诗集“畅销”的最大理由是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和猎奇心理。毕竟,生前默默无闻的普拉斯已成自白派诗人代表,被公认为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她的自杀与休斯的情变有直接关系,饱受长达35年指责的休斯以这部诗集的出版进行了回应。他与亡妻的点点滴滴都浓缩为他笔下的一首首诗歌。这些诗歌与独白无关,而是一首首或长或短的叙事诗歌。从独白到叙事,是诗人的变化,也是表现题材的变化,关键是,从自己驾轻就熟的手法进入另外一种叙述,考验的不只是诗人的才力,还有诗人对文体的深入理解。
理解诗歌文体也就是理解诗歌本身。读完那部《生日信札》,我在暂且撇开诗集主题后想到,对休斯这样的诗人来说,如果缺失对诗歌的深度理解,就不可能游刃有余地展开多种写作技艺,更不可能开辟属于自己的诗歌道路。进入现代以来,越是出类拔萃的诗人,对诗歌的建设就越不仅仅只停留在单纯的诗歌写作上面。对一个诗人来说,写出了什么诗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就西方诗歌来看,从数千年前的荷马到揭开文艺复兴序幕的但丁,再到俯瞰全球的莎士比亚,有条清晰的发展线路呈现在读者和诗歌史面前。在那些源头性诗人那里,作品意味着一切。当诗歌来到20世纪,诗歌对诗人的要求已不仅仅是写出作品。伴随人类的思想和社会发展,诗歌变得日益多元,最明显的特征是,诗歌已从垂直的线性抒情中完成了摆脱。不是说诗歌不再是抒情的载体,而是作为载体本身,诗歌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现代主义的多元手法中有了醒目的凸显。这时诗人该走什么路,该展开何种探索,该如何界定时代对诗歌提出的新的要求,无不使诗歌的发展变得错综复杂——浪漫与现代、现代与象征、象征与后现代等等,都成为诗人能驱赶诗歌进行横冲直撞的领域。
二
这部《冬日花粉》是休斯毕生的思想结晶,它汇集了休斯各个时期的著名文论。这部没有分辑的书其实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书的后半部,它显示了休斯对传统的关注——不论诗人如何现代,没有谁可以摆脱传统。艾略特的文论精华不就包含了他对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核心解读?休斯同样如此,眼光从来没有从莎士比亚身上离开过。在休斯笔下,他对莎士比亚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于艾略特的理解。最起码,当艾略特将目光集中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斯多葛派哲学的纠缠中时,休斯已将关注点位移到莎士比亚所代表的文学世界与意大利新柏拉图主义所代表的社交世界的编织中。构建理论的前提是视野。休斯在这里展现了自己的视野。没有这一视野,休斯就不会在另一篇《伟大的主题》中体会到莎士比亚“一词一句都具备如此微妙的准确性”。庞德不也异常决绝地说过“准确的陈述是写作的第一要素”?当然,休斯说的莎士比亚“准确”与庞德的“准确”没什么必然关系。作为诗人,休斯紧扣的是自己对莎士比亚的语言理解,“当我们的目光透过这些文字,注入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时,种种新的事物、新的可能便层出不穷,尽显于词句之中。”
视野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经典能成为经典的理由再多,语言始终是不可绕过的核心环节。休斯对语言“准确”的理解导致他对“内心深处的黑暗”触及。不是说“黑暗”是诗歌的核心,对一个不断挖掘生活的诗人来说,深处的事物无不具有“黑暗”的质地,在莎士比亚身上,休斯发现了其“恶魔”与“神圣”的统一,才让后世读者最终面对“一位完整的诗人”。并且,通过对莎士比亚的作品选编,休斯还体会到“莎士比亚的语言依然比之后存世的任何文字都更贴近英语本身的生命内核”。这就是阅读带来的认知。我既感意外又觉正常的是,休斯不像一般编选者那样,将笔墨集中在对作者的生平介绍和对入选作品的阐释之上,而是极为深入地展开个人与经典的相互纠缠,乃至提炼出自己对诗歌的理解,所以他才能坚定地以为“一首长诗的片段并不构成一首短诗”,甚至不含糊地指出,“即便是莎士比亚,也终究无法摆脱自我。”这是令人意外和惊讶的判断,研究者公认的,恰恰是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过于缺失自我,才导致后人对其生平的研究十分欠缺。在休斯那里,结论完全不同,这决非休斯的标新立异,它反而证明了,一个真正理解创作的诗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视角,不论通过该视角形成的结论是否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被承认和接受,它毕竟体现了休斯充满个性的理解。
三
而我所理解的第二部分集中在“更趋尖锐,更显严肃”的表述。休斯离开人物,将全部身心集中在对诗歌本身的理论探索当中。这部分的篇章包括《奇闻异事和血淋淋的冒险》《火狐》《诗的锻造》《略谈中小学写作》《隐匿的能量》《人性之歌》《国家的幽灵》等等。这是休斯面对诗歌的直接言说,哪怕《奇闻异事和血淋淋的冒险》和《火狐》不无诗人的自传元素。早在11岁时,休斯就对韵律发生兴趣而大量阅读诗歌。这是成为诗人的最初和必要准备,但休斯又决非要写一篇或数篇自传,通过自述,休斯剖析了韵律和节奏的重要,也回顾了自己对惠特曼从失望到崇敬的接近。初时的失望是自己在后者诗歌中没找到韵律,后来的崇敬是因为自己终究理解了什么是诗歌。
在这部书里,休斯至少用两种方式定义了他以为的现代诗歌。在《诗的锻造》中,休斯现身说法,叙述了自己如何写下第一首“动物诗”《思想之狐》的过程。令人意外的是,休斯明确告诉读者,诗名虽有“思想”二字,但“从这首诗里,很难找得出堪称‘意义’的成分”。这是休斯包括“动物诗”在内的全部诗歌的核心标志,也是现代诗的核心标志——诗歌从来不是对“意义”的寻找,而是如何准确呈现出客观风貌。这首被诗歌史重视的诗歌也被休斯自己重视。他的重视方式不是浅薄的自鸣得意,而是为读者打开专属于诗歌的隐秘通道,“每当我读起它来,那只狐狸都会从黑暗中现身,然后钻进我的脑袋。我想,在未来,即便我离世已久,只要有人读它一回,那只狐狸就会再次现身——从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现身,然后一步一步向他走来。”这种表述是作者对自己诗歌的回望,也让读者在这些话中体会到一首现代诗的本质——它与思想无关,只是不折不扣的存在。休斯在另外的篇章中说得更加明白,“我所谓‘思考’——说是花招也好技巧也罢——能使我们有能力抓住那些难以捉摸或者幽暗不明的想法,将它们聚敛一处,放平摆稳,供我们真真切切地看上一看。”
用自己的写作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诗歌定义,没几个人这样做到过,而且,在读者跟随休斯的创作过程中,不仅能体会诗歌的含义,还能体会一首现代诗的魅力形成。休斯的诗歌的确充满魅力,很少有读者能抵挡从他诗歌中散发出的魅力。休斯一方面承认“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模仿或者替换的维度”,一方面又异常坚定地对诗歌下出了和庞德等先行者有所区别的直接定义,“当文字足以在短暂的一瞬间里掌控‘某某’,从中辨识并透视出所有最具生命也最为关键的信号——不是原子,也不是几何图形,更不是一堆晶体,而是人的信号时,我们便称之为诗。”
在这句话里,他特意在“人”字下划了一杠,提醒读者重视,因为“人类存活的证据无声地合唱,汇成一曲普遍的吟咏,倘若作者置身事外,对这歌声充耳不闻,便会立即被拒之门外”。休斯自己的实践也无不如此,在他至今拥有全球读者的“动物诗”里,没有哪首诗不是看似在写动物,实则在写人,仍以那首堪为代表作的《栖息着的鹰》为例,不论评论家们的解读如何有异,共同的一点是,那只“鹰”不仅仅是“鹰”,而是“人”的化身,这就像休斯自己说过的那样,其写作目的,是“企图通过我与世界真实关系的建立来证明世界的真实性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性”。所以无论他写下什么、暗示什么、隐喻什么,表面上看,与他宣称“可教”和“可训练与强化”的想象力有关,往深处看,则与他在《退世》一文中展现的思想核心有关,“让人类的灵魂完整,幸福地回归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