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旅:不忘初心的文学摆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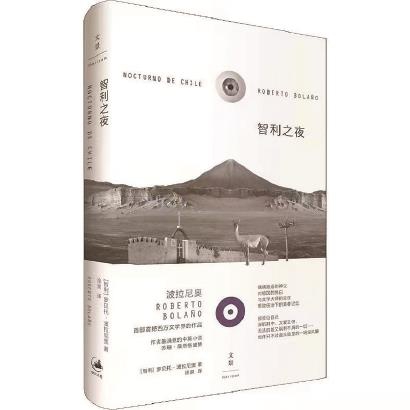
多年以后,当我与师大的同事开始合译阿根廷作家比奥伊·卡萨雷斯的鸿篇巨著《日记中的博尔赫斯》并一度被数以千计的注释索引折磨到生无可恋的时候,不禁回想起初二那年去图书馆借阅《百年孤独》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彼时那个在不经意间闯入到奇妙瑰丽的拉美文学世界的小小少女,显然不可能预见到,自己最终会在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从事西班牙语教学并致力于西语文学翻译。
作为一名年轻的译者,我有幸与罗贝托·波拉尼奥结缘。在文学爆炸之后,可能再也没有哪位拉美文人能像这位智利作家这般引发大众的关注。随着世界各地陆续掀起阅读波拉尼奥的热潮,他已然成为一代文艺青年的新偶像。而《智利之夜》作为其首部被引入英语世界并引发轰动的作品,更是被苏珊·桑塔格誉为“一部注定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当代小说”。波拉尼奥曾借费尔韦尔,那位他在《智利之夜》中杜撰出来的智利文学界教父之口说出:“文学之路并不轻松……这条道路并非是开满了玫瑰花的。”然而相较文学之路,翻译之路的艰辛更是难以言说。作为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再创作,字斟句酌的文学翻译就仿佛是闯进了一片暗黑森林,须得历经千辛万苦,才可能通过并最终抵达彼岸。
具体到波拉尼奥,这位“当代西班牙语文学中最胆大的作家”,因其黑暗晦涩的遣词造句、暴风骤雨般的语言节奏,及其穿梭时空凝聚历史的信息流量,他笔下的这片暗黑森林显得更为广袤,环绕其间的迷雾也更为浓密。而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投入差不多9年时间反复打磨这部近十万字的中篇小说的译稿,除了推动西语文学传播的那份小小执着,更是源于丽娃河畔翻译家群的那份情怀传承。
这种“隐身于作品之后”的“文学摆渡”,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放空”,“剥离”译者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属性——像是袁筱一教授所说的那样:“遏制自我表达的欲望,专注地去做一个译者,感受来自不同语言间的新鲜撞击,刺激我们寻找语言的更多可能性。”而在语言的维度以外,译者势必会借助原著作者的触角去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源源不断地接受新的讯息和思想的输入。每一个主动或是被动获得的知识点将暗夜中的“灯塔”一盏盏点亮,串联在一起照亮这段文学之旅。而一想到这些精神上的电波,将会借助自己的译本被传达给更多的读者,像是在水面上激起阵阵涟漪并不断扩展,完成“文学摆渡人”的使命,心中则更添一份动力——是的,译者们虽然大多低调、朴实,但却从未失其初心。
诚然,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查证作者语焉不详地提及的一个姓氏或是一则逸闻,往往得要花费很长时间,并可能需要向拉丁文或是德、法、意、葡等其他语种的同行们求教,然而每完成一处难点或是疑点,每补全一条有助于理顺行文内在逻辑的译者注所能获得的满足感,与年少时破解奥数难题时的畅快体验颇为相似。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有着显著的不同:数学之美在于它有唯一的正解,而翻译之旅,却始终只能是一个努力追寻最优解的过程——可能越来越接近,却永远不可能趋于完美,即便是经过不断地修订和校正,反复地推敲与打磨,多少还是会有力所不能及之处;此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每一代译者的不同文字风格,也给“翻译之美”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
由于西语文学的译介在国内起步较晚,一直到近10年来才迎来一个小高潮,绝大多数被引进的作品皆为中文首译本。没有前辈们的珠玉在前,翻译自然更具挑战性。在《智利之夜》出版后的几年间,我还会时不时地翻阅一下原著,若是偶得新的灵感,便汇总下来发给编辑,以备在重印时加以完善。犹记得书中第171页的那句“一个圭多都没有”,初时因为不确定“Guido”这个单词属于哪一语种,是人名抑或是姓氏,一番搜索之后只能大概确认它应该是源自日耳曼语的男用姓名,译为“圭多”或“吉多”,如今一般用来代指意大利后裔。某一日,在聆听了一场文学讲座后,我突然顿悟此处应该是指但丁的挚友卡瓦尔康蒂,一位十三世纪的佛罗伦萨诗人。根据《十日谈》第六天故事九的相关记载,此君常常在一座教堂附近的墓地绿林里一边漫步一边思考哲学问题。某日,一群骑着马招摇过市的纨绔子弟将其围堵在墓碑前发起挑衅,然而他却机智地纵身一跳摆脱了他们。那一跳是如此轻盈灵动,以至于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第一讲“轻逸”中写道:“如果让我为新世纪选择一个吉利的形象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就是: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伴随着以上的背景注释,那句“一个圭多都没有”与后续行文“没有绿色的树木。没有骑着马的小跑。没有争论,也没有研究”就有了内在逻辑,变得更为生动且含义深远——这也正是恰当地补充译者注能够大大丰富文本的可读性并增强文本的互文性的一项有力例证。
在挑战完波拉尼奥之后,我又陆续收到了几家出版社的翻译邀约,并在看到“塞萨尔·艾拉”这个在西语文学界绝对不容忽视的名字之后,第一时间读起了《文学会议》的原著。作为20世纪末阿根廷文学的领军人物,艾拉深受欧美先锋派文学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他在这部作品中彻底贯彻了反传统的精神:主题多变,语言跳脱,情节碎片化,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和奇妙荒诞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波拉尼奥曾表示:“一旦读了艾拉的小说,你就停不下来,还想读更多。”恰是这种“一路飞奔向前”的独特阅读体验,吸引我再次静下心来翻译。
而随着翻译过程的深入,博尔赫斯、波拉尼奥与艾拉,这几位西语文坛巨匠的一大共性也逐渐显现:他们都热衷于不动声色地旁征博引,就像是一种出于本能的炫技。那必然是因为,在“作家”的身份标签之前(博尔赫斯和艾拉同时也是“翻译家”),他们本都是博览群书的“读者”——虽然人生经历不尽相同,却都积极践行“以阅读充实和丰富生命的维度”的处世原则,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广泛涉略,同时笔耕不怠。对于译者,乃至广大读者而言,阅读这类作家的作品,就如同闯入了一座小型图书馆:除了那些含义隽永、引人深思的关于文学的哲理性讨论,他们旁征博引,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文学、艺术、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为读者铺设了穿梭往来的通道。同时,这类作家往往还钟爱在作品中虚虚实实地设计富有深意的隐藏细节,吸引着包括译者在内的读者去一一探究和解答。
正如《出版人周刊》所评述的那样:“在艾拉的妙笔之下,含混积蓄为秩序,谜团得以澄清,每个看似离题的叙述最终都自有其目的。”看似天马行空、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戏剧性效果的创作,实则深入探究人类的生存困境,并试图以文字抵御现代社会中那种身处边缘的孤独感,以及面对不可知、不可控的未来的焦虑感。而波拉尼奥也已在《智利之夜》中告诉我们:“那些文字正含糊地诉说着人类的历史和渴求,事实上它们真正讲述的是我们的溃败。”面对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既然唯有文学才是治愈人心的救赎,那么,就让我们这群勇敢的“摆渡人”,伴随着那些即将绽放在师大校园里的新种“翻译家”玫瑰,继续痛并快乐地翻译下去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