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时间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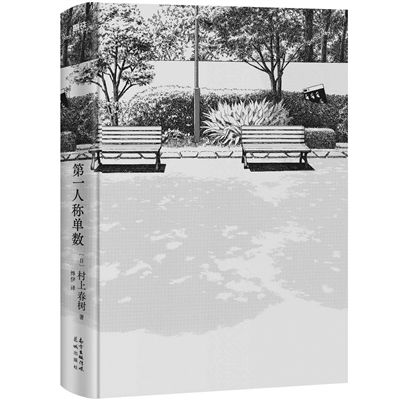

村上春树已经年过七十了,虽然早就知道他生于1949年,却无法把他跟“衰老”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他的小说世界里自然有时间的刻度,可是又像是不存在时间似的,无论他写于哪个时代的作品,无论他的读者更新换代过多少,阅读的感觉始终是恒定的,写作的内容也是恒定的,就像是身处一个调控得刚刚好的房间,待在里面凉爽、舒适,时间丝滑得让人感受不到重量。
那么他的这一本最新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与他过去的作品相比会怎样呢?
1
先说相同之处,一如既往恒定的阅读愉悦感(只要是在旅途中一定会想带上一本看看),一如既往地反复写着他那些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一如既往地把人物安排在“人生的中间地带”……总之,哪怕不看作者名,我们都能一眼看出这还是村上熟悉的配方。再说变化之处,文章一开始我提到村上已经七十岁了,这其实是不容忽视的,无论他如何要保持自己的状态,时间的重量感还是在作品中体现了出来。
全书一共八个短篇小说,前面七篇都发表在日本文学杂志《文学界》,时间集中于2018年和2019年,最后一篇同名小说《第一人称单数》是新写的,基本上都是村上七十岁左右写的。人走到了这个年龄段,该经历的事情基本上都经历过了,该探索的路也基本上走过了,就会忍不住回望过去,“时间怎么说都是同样的时间,一分钟就是一分钟,一小时就是一小时。无论如何,都是我们必须珍视的。与时间好好和解,尽可能留下宝贵的记忆——这比什么都重要。”(《养乐多燕子队诗集》)可以说,“记忆”是这本小说集一个关键词,“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圆满地得到这份悸动的时候,我便让过往对它的记忆从自己的身体内部悄悄复苏。就这样,记忆有时成了我最珍贵的情感资产之一,也成了我活下去的寄托,就像躲在外套大口袋里熟睡的、暖乎乎的小猫。”(《和披头士一起》)
小说中的“我”自然不等同于现实中的村上春树。不过写作的暧昧之处也在这里,我们会忍不住把小说中的“我”代入到作者身上。这里要提一笔的是书名“第一人称单数”,它不仅仅是此书的同名小说,也是全书的写作特点:每一篇都是以“我”的第一人称来讲述的。“我本来以第一人称‘我’开始写小说,这种写法持续了二十年左右。”村上春树曾经在《身为职业小说家》里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每一本不同的小说,‘我’的人物就会改变,虽然如此,但在继续以第一人称写作时,有时现实上的我和小说中的主角‘我’的界限,对写的人或读的人而言——某种程度也难免会变得混淆不清。”当然我们作为读者也知道这些故事不是发生在作者身上的,但那种叙事的心态却是属于村上这个人的。
2
那是怎样一种叙事心态呢?书中有一篇小说《奶油》,其中的一段可以很好地回答,“我们的人生中,有时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无法解释,也不合逻辑,却唯独深深地搅乱了我们的心。这样的时候,大概只有什么也不想、什么都不考虑,只有闭上眼睛,让一切过去,就像从巨大的浪涛之下钻出去一样。”《在石枕上》里那个做爱时喜欢叫前男友名字的女人,《和披头士一起》里那个会丧失片段记忆的女友哥哥,《品川猴的告白》那个偷了七个心爱女人名字的猴子……哪一个是可以解释而且合乎逻辑的呢?哪一个不是“搅乱了我们的心”的呢?站在现在回望过去,常常就是这样的事情回旋在记忆中。
不过颇有意思的是,既然是记忆,有记得的,也有记不得的,“想不起来”“记不太清”在全书里频繁出现:“我对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就连她的名字和长相也想不起来。”(《在石枕上》)“一个我已经想不起来的、极为普通的陌生男人的名字。”(《在石枕上》)“为什么会和他讲这个,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奶油》)“可还是连一个小节都想不起来。”(《和查理·帕克演奏波萨诺瓦》)“除此之外,我对她一无所知。”(《和披头士一起》)……
如果熟悉村上过去作品的读者,会发现这是他常用的叙事策略。他笔下的人物经常是面目模糊的,哪怕他会给出一些交代背景的笔墨,也不能增加人物的厚度。通读完小说,基本上没有人物会在我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除开那只品川猴,但它不是人),他们又轻又薄。如果说在很多作家那里需要浓墨重要刻画的人物是油画,那在村上这里的人物就是用铅笔几笔勾勒的素描,只有线条,没有色彩,没有背景,只有空白。但在村上的文学世界,这不是缺点。毕竟写活一个人物,不是村上要达成的目标,他志不在此。
3
再回到“记得”这部分上来说。同名小说《第一人称单数》里写道:“这可能和我早先就感受到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违和感有关。我能意识到一种微妙的偏差,好像此刻我的灵魂和它的载体不相契合,或是它们原有的契合在某个时间点被打破了一样。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我认为村上的短篇小说非常迷人的部分就是这种“微妙的偏差”。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戴着面罩,都在正常地扮演着各自社会赋予的角色,有各种道德法律纪律约束着你在正常的按照规定生活。你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上课学习,上班工作,都是平淡乏味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对一个陌生人知根知底的了解。因为大家太正常了。但在这日常生活中总觉得有隐隐的不安。这不安像是一条细细的裂缝,在生活光滑的质地上分外触目。好比是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米饭放在你面前,你却总觉得吃得不踏实,要么是这米饭散发出来的不是米香,却是肉香,或者是端饭的人那一抹轻俏的微笑,让你惴惴不安。总要发生点什么吧?在看小说的时候,我们不常怀有这种期待吗?这种细软如丝般的不安就是村上经常写到的“微妙的偏差”。
举一个例子,同名小说《第一人称单数》里的“我”,平日都不会穿西装,因为他觉得一旦穿了西装,就会有异样的感觉,有一天他穿上西装后,“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站在镜子前,我的情绪却有些异样,其中似乎暗含着一丝负疚。负疚?该怎么形容好呢……也许和那些惯于给自己的履历添油加醋的人的罪恶感差不多。即使不和法律相悖,也是伦理道德上的欺诈。明知不该做这样的事,也清楚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却还是忍不住做了——那种不好受的滋味正是如此而来的。容我擅自想象,瞒着大伙男扮女装的男人们,心里的感受也大抵如此。”结果,穿着西装的“我”到一家咖啡馆看书,却惹怒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莫名地给自己“正常的人生”惹来了无来由的麻烦。
村上的小说里,常见这种的情节设置,人在“正常”的人生轨道上滑行,忽然莫名地略微出轨(注意,不是完全出轨),产生了摩擦,由此激发了异样的心理体验,然后又一次回到了正轨。《奶油》里“我”忽然无法正常呼吸时,遇到一个老人跟他谈起不同寻常的圆,之后这个老人消失不见了;《品川猴的告白》“我”在萧索的旅馆碰到跟其聊天的猴子,说起了种种奇妙的事情,然而第二天却发现无人知道这只猴子;《狂欢节》里“我”碰到一位同样喜欢一样音乐的丑女,而这个女人之后就消失了,再见她是在电视中……种种“偏差”出现,而后都一一消失,唯有在心头留存“微妙”的涟漪。
4
最后必须要提到的是在这本书里能鲜明地感觉到村上的确“老”了,因为每一篇小说的中间和结尾“感叹”的部分比之前过去多了很多。村上的短篇小说向来轻盈、散淡、微妙,这在此书中也有部分体现,但很多大段落的“感叹”,让全书有了人生累积下来的重要感(我统计了一下,全书出现了22次“人生”)。
当然,我特别喜欢这些感叹,其中有我认为是全书最动人的段落,“迄今为止,我的人生有几个重要的分水岭——恐怕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如此。向左或向右,往哪边都可以走。面对这样的时刻,我有时选左,有时选右……然后才有了如今的我。就这样,第一人称单数的我实实在在地出现在这里。要是我在其中任何一处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了。”遥想当年,村上春树在29岁时走上了写作这条路,一晃就是四十余载了,他可能也没想到这样一个选择把他导向了现在。我知道,他依旧会继续走下去的。
作为读者,我继续等待他的下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