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与“回归”之间的文学与人生 ——读《昆德拉传:一种作家人生》
198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过两次“昆德拉热”,关于作家的作品、写作关键词甚至作品改编的电影都成了讨论焦点,但是对于作家本人却知之甚少。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昆德拉传:一种作家人生》首次将昆德拉的人生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是,细读之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部“非典型”传记,以“作家人生”为昆德拉的传记命名,颇有一种维特根斯坦哲学之妙:“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都必须保持沉默”。作者布里埃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对昆德拉关于私人生活的原则恪守不渝,同时又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对昆德拉作为作家的人生进行了清醒的解读和冷静的哲思。
布里埃将昆德拉的人生置于近百年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在详实的文学资料、历史资料与访谈资料中探寻昆德拉的精神世界及其作为“作家”的人生旅程。传记的前两章“在奥匈帝国的废墟里”“布拉格政变”,将昆德拉的出生与青少年期间的成长和人生选择与历史和政治勾连起来。昆德拉十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十五岁时战争结束。战争与随后的政治热潮中的种种必然与偶然,将出生于音乐之家的昆德拉抛向了诗歌的激情之中。在被昆德拉称为“抒情年代”的青年时期创作,他是以诗人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但是他却在1970年代否定了自己当时的诗歌,并且在七星文库版作品集中将诗歌全部抹去,认为自己当时的“诗歌与政治介入”都和“最糟糕的年代混在一起”,“如果一生都是抒情诗人,那我便会不寒而栗。”1960年代开始,随着政治热情的消退,昆德拉摆脱了革命幻想,放弃了诗歌这种抒情性的表达。
昆德拉三十岁左右放弃诗歌,他把这种放弃称之为一种“背叛”。对于昆德拉来说,抒情诗与小说都不仅仅是文学体裁,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一种世界观。放弃抒情性而转向反讽,从诗人变成小说家,意味着昆德拉对世界的态度的转变,同时也是他思想和文学创作上日益走向成熟的表现。曾被命名为《抒情年代》的小说《生活在别处》,正是标志着这种转变与成熟的“反抒情性”宣言书。主人公雅罗米尔在“革命热情”表象之下的自我陶醉的抒情性被作家深刻地揭露。昆德拉把这种可能出现在所有时代、所有体制之下的年轻人身上的恐怖的抒情性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行为进行探索,并试图用小说的反讽来摧毁抒情幻想。“玩笑”是昆德拉式反讽的利器,《玩笑》中主人公经历了历史的玩笑,《生活在别处》中主人公经历了青春的玩笑,在此后的作品中,爱情、逃亡、回归、不朽等等文学中的重要主题都被昆德拉以玩笑的方式瓦解,甚至存在本身也成为了玩笑。“布拉格之春”后,昆德拉被宣布为“右派作家”,失去了电影学院的教职。由于长时间无法找到工作,他不得不在几年里匿名为某刊物撰写占星专栏。他的专栏深受读者喜爱,他甚至还曾戴着面具为一些官僚政客做占卜,这几乎成为了他人生中最滑稽的时刻。昆德拉在小说中探讨的“玩笑”,以一种现实的方式切入了他的人生之中,又或者正是人生中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玩笑,才使昆德拉更加深入地将其展现在自己的小说之中。小说中的玩笑越真实就越证明,在那个时代,最小的玩笑话就能摧毁一个人的生活。昆德拉成为小说家的过程,是一次又一次与玩笑、与误解对抗的过程。
1975年夏天,昆德拉离开捷克前往法国雷恩第二大学任教。抵达法国不到一年的时候,昆德拉向一位德国记者申明:“我有权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永久的移民生活使我沮丧”。昆德拉在法国写作的第一部小说《笑忘录》中首次展现了“流亡者”的形象。分离把人与物都变得更远,这种遥远以空间开始,继而蔓延到了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去的人或地方的形象变得模糊,进而会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昆德拉小说中的“流亡者”却不断地徒劳地与这种遗忘抗争。昆德拉小说中的遗忘主题在《笑忘录》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现。昆德拉把人生中的遗忘当作一种死亡,并且认为一切通过记忆和想象重构过去的尝试都只能是徒劳。这种对捷克当时的政治进行“遗忘”式的反讽,使昆德拉的捷克公民身份在1979年被剥夺,1981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昆德拉法国国籍。这一转变被昆德拉认为是作家在追寻着作品的道路,1980年代,昆德拉开始了他的法语写作。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从一个国家转换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入另一种意识形态,昆德拉的身份激起了人们的好奇。他不得不应对人们接连不断的有关身份选择的问题,昆德拉总是以一种绝对而没有任何异议的方式做答:“我是小说家”。“小说家”自此成为了昆德拉所需要的唯一身份。
如果说“作家昆德拉”是在不断的“离开”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其成熟的一面,那么“摩拉维亚人昆德拉”则是在不断的“回归书写”中呈现出其“不可能”的悖论。自大学时代离开布尔诺到布拉格求学开始,昆德拉便体会到一种“温和却很真实的流亡”。在布拉格,波西米亚文化对布尔诺的摩拉维亚文化的重压,使昆德拉感受到了自己和故乡所受到的轻视。布拉格是全国关注的中心,而布尔诺可以作为永恒的不幸者被人们提起。自五十年代的诗歌一直到1967年的第一部小说,昆德拉都在不断地歌颂着故乡,如流亡在布拉格的尤利西斯,昆德拉“沿着破旧的铁路,回到故乡”。他渴望书写故乡,摩拉维亚的音乐与音乐史上的众多音乐形式都如同他童年与青年的记忆一样,由音符幻化成词语被写入昆德拉的小说之中。失去捷克国籍后,昆德拉一直拒绝各种回归的可能,认为自己“再也没有力量从巴黎流亡到布拉格”,并且极力反对自己被媚俗地贴上“不幸的流亡者”的标签。但是昆德拉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了一个对所有作家都适用的明显道理:“人在前半生积累了重要的生活经历、社会经历以及情色和性经历。所以作家总是根植于前半生”。虽然在现实中拒绝回归,昆德拉却在小说中不断地重复着“回归”这一主题。在回归与遗忘中徘徊的主人公,一方面难以摆脱对失去的故乡的怀念,另一方面又惧怕无法真正地回归到彼时彼地的故乡。西方语言中的“怀念”一词,最早是用来定义17世纪晚期瑞士雇佣兵所患的“思乡病”。从这一词源意义上来讲,“怀念”是一种根植于现代性之中的“病症”,昆德拉一直以一种“反现代”的姿态书写着“现代人”的种种痛苦。在现代之中,他所否定的是一种“真正的回归”。当故乡已经不是我们离开时的故乡,我们已不再是离开时的我们,地理意义上的回归只能带来一种美梦成真后的破碎。昆德拉在“遗忘三部曲”中,特别是在《无知》中,对这种“不可能的回归”做出了最明确的阐释。
2019年,昆德拉重获捷克国籍。昆德拉接受了捷克政府恢复其公民身份的文件,在多次“不得不如此”的离开后,抵达了一种形而上意义的回归。由此作家昆德拉与其作品所根植的故乡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昆德拉通过“背叛”确立了其作家身份,又通过“回归”而实现了其人生的“永劫轮回”。或许布里埃以“作家人生”为名为昆德拉做传,并不是出于对昆德拉私人生活原则的顾忌,也不是因为作家生活琐事与人生传奇难以追寻,而是因为昆德拉本身并不需要任何矫饰,只需回顾他的作家之路,便已经足以了解他在“背叛”与“回归”之间的文学与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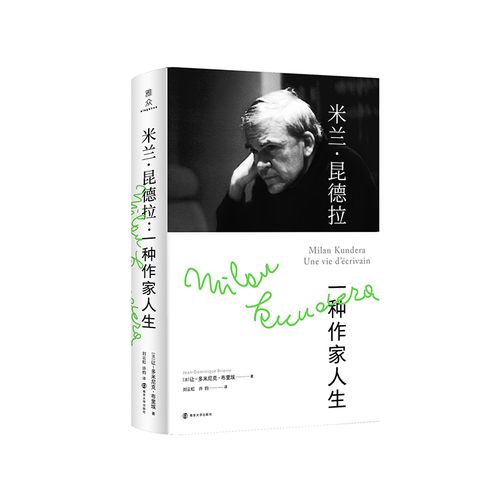
(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刘云虹、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