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追寻——论拉什迪的新作《吉诃德》
内容提要 萨尔曼·拉什迪的新作《吉诃德》揭示了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众生如何以爱联结彼此,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文学如何成为唤醒爱的有效方式。本文从该小说中爱的追寻入手,从异化危机、爱的追寻以及文学之用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试图说明拉什迪对面临生存危机的现代人命运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 萨尔曼·拉什迪 《吉诃德》 爱 异化 文学

萨尔曼·拉什迪,图片源自Yandex
自2000年移居纽约以来,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 )的创作主题从反思印度历史文化、书写东西方文化冲突转移到思考美国社会问题折射出的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他关于美国社会的审视见诸《狂怒》《两年八个月二十八夜》《戈尔登一家》以及新作《吉诃德》(Quichotte,2019)。与前三部聚焦纽约市曼哈顿区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同,《吉诃德》讲述了同名主人公吉诃德横穿美国,从怀俄明州的魔鬼塔到纽约市的旅行故事。这部改写自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的作品出版不久便与加拿大小说家阿特伍德等其他五位作家的作品一同入围2019年“布克奖短名单”,尽管最终未能获奖,但评委仍然对该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
与拉什迪此前的小说相比,《吉诃德》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小说中的空间位移,其中一个更深刻、更有价值的变化是,这部小说为他之前的小说中悬而未决的故事结尾提出了一个解决策略:爱能够化解人类的冲突。评论家也发现,吉诃德“坚信爱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定愿望”一直是这部小说的核心,这预示着作家“在一个不断走向仇恨、排斥和不宽容的世界里,对普遍存在的爱和宽容怀有的理想”。可以说,这是步入古稀之年的拉什迪为世人走出冲突频仍的困境指出的对策。
一、异化危机:现代人的精神孤独与分裂世界
《吉诃德》包含三条故事线:第一条故事线是一位名为布拉泽(Brother)的印度裔美国作家正在创作一部改写自《堂吉诃德》的小说《吉诃德》。布拉泽年逾七旬,生活并不如意,婚姻破裂,儿子因此离家而杳无音讯,此外,他和妹妹赛斯特也因口角之争结怨许久。布拉泽虽然追悔莫及,但缺乏认错的勇气,因此,他在《吉诃德》中假借吉诃德的寻爱之旅,寄托了希望重获亲人之爱的心愿。第二条故事线围绕布拉泽的小说《吉诃德》展开。吉诃德原名伊斯梅尔·斯米莱(Ismail Smile),是一位居住在纽约市的记者,后因意外中风性情大变。与妹妹塔姆潘琳争吵之后,他离开纽约市,只身来到表兄斯米莱医生的医药公司担任旅行推销员。常年在外奔波让吉诃德养成了沉迷电视节目的习惯,他误把对脱口秀巨星萨尔玛的迷恋当作爱情,并由此开启了一段寻爱之旅。第三条故事线是关于小说《吉诃德》如何改善布拉泽的现实生活。吉诃德向塔姆潘琳求取谅解,他与桑丘的父子之爱鼓励布拉泽在现实生活中与妹妹和解、与儿子团聚。
这部小说蕴含着拉什迪对现代人面临的异化危机的思考。2005年,时任美国笔会主席的拉什迪在“世界之声”国际文学节上发表题为《笔与剑》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扩大对话的时候,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事情正在被停止,障碍正在被竖起,对话正在被扼杀。冷战结束了,但一场更怪异的战争已经开始了。异化或许从未如此普遍;那我们就更有理由聚在一起,看看能建一些什么样的桥梁。”拉什迪所说的“异化”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疏离与彼此分裂,这与埃里希·弗洛姆的异化观相暗合。弗洛姆认为,异化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他对异化一词进行考究之后发现,“‘异化’一词过去是指精神不健全的人;法语中的aliene及西班牙语中的alienado都是较古老的称呼患有精神病的、完全异化了的人的词汇”。在他看来,“异化了的人同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联系一样。他感受自己及其他人的方式就像感受物一样,他有感觉,也有常识,可是他同自己以及同外界之间并不存在创造性的关系”。弗洛姆所说的异化其实就是人的安全感以及身份感的丧失,其根源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要求人把自己的技能、知识甚至生命转化成商品来创造利润,这导致人与自己以及同胞相互疏离。正因如此,人只能依附于身外之物来获取暂时的安全感或身份感,如弗洛姆所说,“每个人都把他的安全建立在附和群体的基础上,而在思想、感情或行为上没有什么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尽可能靠近其他人,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独,充满深重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和内疚感,这些感觉源于不可克服的分离”。可见,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疏离所引发的孤独感是人的异化危机的主要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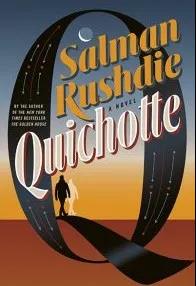
《吉诃德》,图片源自拉什迪官网
在《吉诃德》中,拉什迪以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为切入点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在小说中,印裔美国制药业亿万富翁斯米莱医生的医药公司非法售卖一款名为“InSmileTM”的芬太尼舌下喷剂,这款镇痛剂原本用于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却因能够让人产生兴奋快感而成为一种新型毒品。萨尔玛滥用芬太尼成瘾,还险些因此丧命,她服药的原因看似是为了缓解躁郁症引发的痛苦,实则是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这款产品并非拉什迪虚构,斯米莱医生的原型是美国知名止痛药制造商INSY的前董事长约翰·卡普尔(John Kapoor),他通过贿赂医师大量向患者开处方,推广一款名为“Subsys”的可以让人上瘾的芬太尼舌下喷剂,导致服用者滥用药物致死。拉什迪的一个妹妹和几位亲友正是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受害者。
吉诃德踽踽独行,沉迷电视节目让他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与身份感,却无法根除他的孤独。毋庸讳言,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缩小了的世界中,麦克卢汉所谓的“全新的、电子的相互依存关系将整个世界重新构建成一个‘地球村’”的预言逐步得到了印证,然而,电子媒介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让我们因为缺少深度的情感交流而比以往更加孤独。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孤独,影射了拥有便利的通讯设施但中断了与他人情感交流的现代人的孤独。正因如此,弗洛姆才说,“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避免孤独。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会导致精神崩溃,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
拉什迪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了人性的异化。他将以斯米莱医生为代表的利益至上且丧失人性的这类人魔幻化为一群史前时代的“乳齿象”(mastodon)。小说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吉诃德和桑丘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上发现,镇上的居民会莫名其妙地变成一种巨大的早已灭绝的乳齿象。关于魔幻现实主义,拉什迪在2014年悼念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章《为真理服务的魔幻》中写道: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的问题在于,当人们说到或听到它时,他们实际上只听到或说到它的一半,即“魔幻”,而没有注意到另一半,即“现实主义”。如果魔幻现实主义仅仅是魔幻,就没那么重要了。那只不过是异想天开,因为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所以没有什么效果。魔幻现实主义中的魔幻深深扎根于现实,它从现实中产生,以一种美丽而意想不到的方式照亮现实,所以它才有效。
可以说,魔幻现实主义通过独特新奇的方式刺激人的感官与情感,使程式化的现实陌生化,以此来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感知。拉什迪将一群为牟取私利不惜牺牲人性的人魔幻化为一种粗野蛮横的庞然大物,通过这种陌生化的艺术表达效果警示我们这股野蛮力量给当下文明造成的破坏。正如故事中的小说家布拉泽所解释的,这些乳齿象象征着“我们日益失去人性”,即“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或者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正在失去我们的道德指南针,同时变异成一种野蛮的、史前的、长牙的、过去的生物,这也是正折磨着世人的一种怪物”。
同时,拉什迪还用科幻表现手法呈现了破碎的世界。在吉诃德的故事中,人们的视野中不断出现黑影,这起初被认为是眼睛中的黄斑病变所致,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物质自身出现了黑洞。这一现象导致的物质分裂引发了众多交通事故,并最终衍变成一场“黑洞危机”(Quichotte:314),布拉泽认为这场“黑洞危机”反映了“他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环境、政治、社会以及道德方面的衰败”(Quichotte:356)。
从拉什迪揭示的现代人面临的异化危机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悲观的情绪,但拉什迪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说:
我天生是乐观主义者,但我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作家。我认为生活在世界历史的这一刻是如此艰难,以至于很难不对生活产生悲剧感。作为一名作家,我观察这个世界,我发现我的悲剧意识与之相呼应。但我也知道,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件事。双面性总是同时存在的。对我来说,作为一名作家,我总是有一种本能,那就是不按事情发展的规律来写作,把可怕的事情当作喜剧来谈论,从有趣的事情中寻找悲哀。
可以说,身为作家的本能促使拉什迪捕捉生活的复杂性:生活并不是一部纯粹的悲剧或喜剧,而是一场混杂了世间百态的悲喜剧。正因如此,拉什迪在揭示当下人们面临的诸多苦难时总会留出一丝“爱”的希望,这在《撒旦诗篇》以及《戈尔登一家》等小说的结尾处可见一斑。在《撒旦诗篇》结尾,是爱让吉百列抛下和查姆恰之间的恩怨,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将查姆恰从火海中救出来,也是爱让查姆恰放下对父亲多年的怨愤,在父亲处于弥留之际重新爱上了他。在《戈尔登一家》的结尾,是爱让尼禄谅解了辜负了自己信任的勒内,也是爱让苏希特拉原谅了背叛了她的勒内。小说叙述者勒内说,“拯救地球的力量是爱”,这正呼应了吉诃德关于爱的信念,即“人类的生活大多是不快乐的”,“人类痛苦的唯一解药便是爱”(Quichotte:150)。不过,之前的小说只是偶尔出现对爱的思考,在《吉诃德》中,爱是核心主题——爱能够让个体与自己以及同胞相互联结,消除精神孤独,创造完整生活。
二、爱的追寻:时代之殇与罕见之爱
正如骑士文学让《堂吉诃德》中的阿隆索·吉哈诺混淆虚实,他自封为“堂吉诃德”,领着侍从桑丘·潘沙,骑着瘦马“驽骍难得”踏上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之旅,电视节目也使伊斯梅尔·斯米莱难辨真假,他自封“吉诃德”,领着许愿求得的儿子桑丘,驾驶着一辆雪佛兰科鲁兹开启了自己的寻爱之旅。吉诃德对桑丘坦言,自己向来都是一个分裂的人,是爱让他与众生联结,如他所说,是爱让“我重新与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建立联结,接触生活的多样性,超越它的许多不和谐,触及它更深层的和谐”(Quichotte:195)。
吉诃德认为爱能够联结众生的看法,与弗洛姆所说的只有爱才能满足人与世界有效结合的观点颇为相近。弗洛姆说,“人身上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人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还能使人保持完整性和个性,这种感情就是爱。爱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自身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合在一起”。弗洛姆说的是一种成熟的爱,即爱的双方在彼此结合的同时依旧保存各自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没有精神独立的彼此依赖只是一种“共生性关系”。弗洛姆认为爱是一种积极的活动,一种根植于人的本性中的能力和性格倾向,“爱主要不是一种对某个特殊人的关系;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定一个人对整个世界而不是对某个爱的‘对象’的关系的性格倾向”,也就是说,“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我就会爱所有人,爱这个世界,爱生活”。爱是弗洛姆为现代人开出的医治精神孤独的良方,爱也是拉什迪在《吉诃德》中为异化了的现代人指出的希望。
吉诃德用爱联结人类同胞的希冀呼应了《堂吉诃德》中以爱为基调的人文主义关怀,在《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与桑丘在旅途中同甘共苦,他们在争吵与拌嘴中学会聆听彼此的心声、采纳对方的建议,二人的主仆关系也逐渐升华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关系,布鲁姆认为他们之间的“友谊胜过任何其他文学著作中的友谊”。拉什迪在《吉诃德》中续写了这种诚挚之爱。想与同胞联结的迫切希冀让吉诃德通过向流星雨许愿求得儿子桑丘,他对桑丘关怀备至、呵护有加,这份父爱让他懂得了爱护、尊重和责任的重要性,也帮助他获得了爱的能力。爱的能力把他对萨尔玛的迷恋升华为一种精神之爱。他向萨尔玛坦言,“我对你的追寻并不仅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善良和美德。我现在明白了。通过追寻你——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我想我也许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当我配得上你,我可能就会觉得配得上做我自己”(Quichotte:318)。吉诃德的寻爱之旅实质上是一次自我完善的修炼,而堂吉诃德对意中人杜尔西内亚的爱亦是如此。堂吉诃德与杜尔西内亚素未谋面,当公爵夫人质疑杜尔西内亚的真实性时,他这样解释道,“上帝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杜尔西内亚,她到底是不是虚构的人物,这种事没有必要去追根寻底。并非我无中生有,我确实把她当作一位具有各种美德、足以扬名于世的贵夫人,非常崇拜”。因此,杜尔西内亚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堂吉诃德心中真善美的化身,是激励他崇善弃恶的动力源泉。
吉诃德在寻爱之旅中获得了自爱,一个关键佐证是,吉诃德抵达纽约之后不是立即去找萨尔玛,而是去向同父异母的妹妹塔姆潘琳低头认错,这其实是他与自我和解的自爱举动。吉诃德早年与妹妹争吵之后,二人一别十余载,步入垂暮之年的他对妹妹心怀愧疚,内心重燃的爱让他敢于直面曾经不负责的自我,并鼓足勇气向妹妹认错,得到谅解的吉诃德感到一种新的“和谐”(Quichotte:276)。
然而,吉诃德和桑丘在旅途中遭遇的一系列种族歧视事件让他的寻爱之旅受到重创。长着一副印度裔面孔的吉诃德和桑丘遭到一位白人女性的无端指责;他们的印度同胞被称作“该死的伊朗人”“恐怖分子”(Quichotte:144);桑丘因盯着三位白人中年男子看了几眼而遭到殴打。吉诃德和桑丘遭遇的歧视要归因于“9·11事件”之后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的对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恐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印度裔群体的仇视,这与《堂吉诃德》中人与人之间浓厚的“人情味”形成鲜明对照。堂吉诃德虽然时常处于半疯癫状态,但他的身边有忠诚的侍从桑丘、有悉心关怀他的家仆和外甥女,更有为了治好他的疯癫病不辞辛劳通过“坑蒙拐骗”接他回家的同村好友以及旅途中的好心人。生活在21世纪的吉诃德却没有堂吉诃德那样幸运。尽管吉诃德尝试用爱联结同胞、化解冲突,但是这个缺爱的时代对他的寻爱之旅极为漠然。正如弗洛姆所言,“在当代的西方社会,爱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许多职业不容博爱的态度,而是因为以生产为中心的贪婪的商品社会的精神就是如此,以至于只有个别人能够抵抗”。拉什迪借吉诃德的寻爱之旅重申了爱的重要性,虽然爱已成为一种罕见现象,但它仍旧是化解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一剂良方。更重要的是,拉什迪还指出文学是激发当下人们心中之爱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之用:文学的“逾规越矩”与动力“引擎”
在小说中,布拉泽对妹妹和儿子心怀愧疚,但一直缺乏认错的勇气,所以他借吉诃德寻爱这个故事表达了他未在现实生活中吐露的爱,与此同时,吉诃德寻爱的故事又改善了布拉泽的现实生活。拉什迪通过这一情节表明,文学是化解当前我们面临的诸多冲突、唤醒人们心中之爱的有效策略。
在“9·11事件”之后,拉什迪曾经表达过对文学能够消除弥漫在美国人心中的恐惧的信念。如前所述,美国社会对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恐惧使以往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转变为对印度人、阿拉伯人以及巴基斯坦人的歧视。美国应对恐惧的措施包括颁布针对伊朗、朝鲜等所谓敌对国的书籍禁令等等,这非但不能缓解民众的恐惧,反而因保守排外而加剧种族仇恨。拉什迪认为,美国应该克服国内“故意保持的那种恐惧气氛”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对话,美国“需要知道、倾听和理解世界上其他人在说什么”。文学在这方面很有帮助,因为“它可以消除基于无知的恐惧”。
拉什迪强调,当人们局限于狭隘的文化边界论时,文学家作为时代的“逆行者”应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拓宽人们认知和理解的边界:
文学试图打开世界,增加人类感知、理解以及存在的所有可能性,即使只是一点点。伟大的文学跨越已知的边界,挑战语言、形式和可能性的边界,让世界感觉比以前更大、更宽。……文学的人性观鼓励人们理解、同情和认同不像自己的人,但这个世界却正在将每个人推向狭隘、偏执、部落主义、激进主义和战争。有很多人不希望世界开放一些,他们其实更希望世界封闭一点,所以当艺术家们走向边界并推动边界的时候,他们通常发现有强大的力量正在把自己往回推。然而,他们还是做了自己必须要做的事,即使牺牲自己的安逸,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可见,在一个不断缩小了的世界中,文学家应该努力跨越诸多人为界限,扩大人们认知和理解的可能性,帮助人们消除因无知而形成的偏见。在小说中,吉诃德的寻爱故事实质上是布拉泽的自我反思过程。故事中吉诃德和桑丘的内心独白为布拉泽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视角,这让他反观自己以往仅凭一己之见对妹妹产生的误解以及对儿子的疏忽,从而帮助他理解妹妹反叛的个中缘由以及感知儿子逆反的心路历程。因此,布拉泽鼓起勇气化解了与妹妹的恩怨,并与儿子重归于好。父子俩团聚之后也开启了一段公路旅行,旅途中相似的见闻让布拉泽意识到“想象优先于现实……他真的觉得好像进入了他的小说世界”(Quichotte:363)。这似乎也印证了拉什迪的文学信念:“具有创造力的人的想象可以超越作品本身的界限,它们拥有进入和改变、甚至改善现实世界的能力。”(Quichotte:3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帮助我们察看人性、洞悉事理。
故事的优势在于它自身的连续性与包容性能够囊括繁杂的生活与复杂的人性,从而有助于消除人们因为视野局限而形成的暂时性的认知偏见。正因如此,亨利·詹姆斯说,那些写得活龙活现的故事能够给人们“以丰富的、然而得自别人的经验的知识”;同时,“作为一个醉心于思考并且喜欢思想的社会群体,人类会试着用‘故事’作为试验”。然而,当今的作家似乎不屑于讲故事,而只顾着观念和技巧。谈到故事在当今文学中受到轻视这一现象时,拉什迪说道:
在文学中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广为流传的故事。我认为文学中的这一元素在当下可能有点被低估了,人们不再把故事作为推动艺术作品的动力。但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引擎,特别是如果你想尝试并写出一些大部头、有野心的东西,如果你想造一辆大汽车,你最好装一个大引擎。如果你有一辆动力不足的大车,驾驶起来会很不愉快,而且在我看来,故事是一部巨著运转的大引擎。作为人类,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叙事程序,我们喜欢通过讲故事来理解自己。所以一本书如果把故事和叙述放在书的核心,我们就更容易记住它,因为我们记得一个人物,以及发生在他或她身上的事情,我们会在意它。
布拉泽通过讲故事重新获得爱的能力,又让爱通过文学接连延续,他在与儿子的公路之旅结束之后创作了《吉诃德》的结尾,在那场黑洞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吉诃德牵着萨尔玛穿过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谁知道门的那一边是什么呢?但在门的那一边,还有希望。毕竟,死后可能会有生命”(Quichotte:389)。这段以爱为基调的新旅程暗示着拉什迪对爱能够化解人类苦难怀有的信心,也是他对文学能够传递爱所寄予的希冀。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新作评论”专题,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