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背后:被普鲁斯特怠慢的友谊和生命

所谓“摄于丽兹酒店”的照片,其实是在摄影师奥托的工作室拍摄

《方舟与白鸽:普鲁斯特 影像集》 [法]帕特里西亚·芒特-普鲁斯特 米蕾叶·纳杜蕾尔著 张新木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版
这本关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影像集取名《方舟与白鸽》,当这两个在西方传统文学语境里喻示着光明和希望的词语出现在普鲁斯特的世界里,却被覆上一层挥之不去的哀愁。正如他在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作品《欢乐与时日》前言中所说,他从小为诺亚的命运悲哀。诺亚被困在方舟中的意象让普鲁斯特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因为体弱多病,他总是被禁锢在家中。而他的母亲则像白鸽,带来外界的消息。
“我摆了一堆可笑的姿势”
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打开这本集子。
第一种,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对以《追忆似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为首的普鲁斯特所有作品的现实补充。那些在书中提到的场所和人物有了原型:我们在第115页看到夏尔·哈斯,他是斯万的原型;盖尔芒特夫人的原型、一头黑发的施特劳斯夫人在这本集子里不止出现了一次……这些照片和绘画让我们的想象在顺着他的时光之河流淌时,有了实际的载体。
第二种,你也可以将这本影像集纯粹看成对一个人一生的回顾,其人生的各个阶段几乎都以影像方式得以呈现,虽然难免给人以浮光掠影之感。除了普鲁斯特本人,还有一些和他人生发生过千丝万缕纠葛的重要人物也出现在书里。我们或许可以讲讲这些影像背后的人和事,就从第119页普鲁斯特坐在被认为是丽兹大酒店的长椅上那张不朽的照片开始吧。
该页所选取的是一组至少四个姿势的照片系列中的两张,由奥托拍摄,其中一张原图在苏富比举行的一次拍卖中以21250欧元被拍下。长期以来,它被广泛认为摄于丽兹大酒店,在普鲁斯特的曾侄女帕特里西亚·芒特这本原著里也如此标识,但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照片摄于1896年(另一说为1895年),而丽兹大酒店直到1898年才开张。
因此一个更现实的假设是,这张照片其实是在位于玛德莱纳广场的奥托工作室中拍摄的。而这似乎可以从他在1896年写给好友吕西安·都德——著名小说家阿尔方斯·都德之子的信中得到佐证。“您要我寄一张在奥托那里拍的照片给您吗。”普鲁斯特写道,“不,您最好还是自己来选,我摆了一堆可笑的姿势”。
“我一点都不理解他的作品”
人们一厢情愿地将照片拍摄地点当成丽兹大酒店,这不是一个荒唐的错误,因为普鲁斯特和它太密不可分了。没有丽兹,就不会存在《追忆》。
1898年开张的丽兹大酒店是典型的“美丽年代”的产物。后来的人通常将法国在色当战役中战败的1871年视为其开端,而1918年一战胜利后的那几年则是收梢。这段歌舞升平的时期,沙龙文化在巴黎再度兴盛。而相比巴尔扎克时代,“美丽年代”的沙龙虽然仍是上流人物的阵地,但这一人群的定义不再局限于贵族。暴发户们终于不必再像纽沁根那样削尖脑袋为自己挣得一个贵族头衔,而政客、高级公务员等在这里也受到欢迎。
虽然“美丽年代”的沙龙已打破了阶层的局限,但这仍是一个需要被引荐才能进入的圈子。普鲁斯特对于上流社会很早就流露出一种近乎偏执的迷恋,“附庸风雅”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标签。在孔多塞中学求学期间,他就通过同学比才(作曲家比才的儿子)和拜尼埃尔进入了由施特劳斯夫人(比才的母亲)和拜尼埃尔夫人举办的沙龙。
在各个沙龙的辗转中,普鲁斯特在1889年来到了加亚维夫人的沙龙,并在那里认识了他生命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男人——文豪阿纳托尔·法朗士,后者当时的身份是夫人的情人。本书第108页有对于两人交情的简介。1896年,当普鲁斯特出版第一本作品《欢乐与时日》时,法朗士为其作序。
但这篇序言对于提携普鲁斯特的创作生涯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法朗士,这本书的价值变得微乎其微。而从序本身的内容看,法朗士对于自己年轻朋友作品的文学性并不欣赏,他更多把普鲁斯特当成一个交好的朋友,而非一名真正的作家。事实上,法朗士直到去世也没真正喜欢过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他80岁高龄,而普鲁斯特也已去世后,法朗士这样谈及他,“我一点都不理解他的作品……我努力尝试去理解,但我做不到。但这不是他的错,而是我的错。我们只能理解自己的同辈人……”
出版《欢乐与时日》后的整整17年间普鲁斯特没有再发表过著作,直到1913年《追忆》的第一卷问世。法国文学界很多声音认为,17年正是普鲁斯特用来彻底摆脱法朗士对自己影响的时间长度。但这不是法朗士的错,在《欢乐与时日》出版2年后,两人的友谊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甚至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巅峰。
“《追忆》的出版困扰着我”
发生在19世纪末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由于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介入而震动世界。回到1898年6月1日的晚上,这既是丽兹大酒店开张之夜,也是德雷福斯事件进入如火如荼阶段的晚上。就在丽兹开张前一周,左拉因为写了那篇惊世骇俗的“我控诉”而被以诽谤罪上诉,在法庭接受审讯,当时的普鲁斯特带着三明治和咖啡前去旁听。
1898年6月1日这个细雨濛濛的晚上,当一身时髦打扮的普鲁斯特前往旺多姆广场15号参加丽兹大酒店开张典礼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撕裂的。早在几个月前,他已经加入3000人联名上书请求赦免德雷福斯的行动。这既是出于他的知识分子良心,也是因为他自身的一半犹太血统。然而普鲁斯特对于德雷福斯的支持,让他不得不和自己多年来煞费苦心跻入的上流社交圈价值观背道而驰。他的恩主孟德斯鸠伯爵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这个晚上两人都在丽兹的开业沙龙,但伯爵故意回避了他。孟德斯鸠后来也被写进了《追忆》,成为夏吕斯的原型。他因此被气得卧床不起,并在一封信中承认,“三卷小说(《追忆》)的出版困扰着我。”他的身体再没有复原。
当自觉被上流社会排挤的普鲁斯特怅然若失之时,法朗士和他坚定地站在同一战壕,这对于他不仅是安慰,更是其战斗力量的来源。可惜的是和普鲁斯特一生中的很多友情一样,这段师徒关系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人们普遍相信,《追忆》里贝格特的原型就是法朗士,这也被视为普鲁斯特对老文豪的一次间接清算。本书第158页到160页用了些篇幅介绍普鲁斯特描写贝格特之死时的构思,事实上,他几乎是最后修改完贝格特之死就去世了。在一些评论家看来,这是法国文学史上一次经典的“弑父”行动。
“他被迷得神魂颠倒”
普鲁斯特在人际交往中展现的形象常常是薄情的,但他有自己的长情,这体现在他数十年如一日对于丽兹大酒店的忠诚上。
距离1898年的丽兹开张之夜过去近20年后,此地仍然是普鲁斯特出入最频繁的场所。但此时,陪伴他身边的人成了让·科克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上空频繁遭受轰炸威胁,而丽兹依然灯红酒绿。在《旺多姆的丽兹》里,作者提拉·马奇奥告诉我们,“他(普鲁斯特)当时正被在这里拥有豪华套房的罗马尼亚公主苏卓迷得神魂颠倒,积极参加公主举办的每一次沙龙。而科克托则扮演着这一切的清醒的旁观者角色”。
普鲁斯特和科克托相识于1910年,当时前者40岁左右,后者差不多20岁。尽管岁数相差悬殊,但他们之间巨大的相似让普鲁斯特感叹两人的灵魂如同镜中人般孪生。他们几乎立刻成为密友,普鲁斯特完成《追忆》第一卷后,科克托一直费心费力为他寻找出版商。这本著作屡屡遭拒,最后是由格拉塞出版社勉强同意由普鲁斯特自费、删节出版。
在当时拒绝《追忆》的出版社中,就包括后来鼎鼎有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的冷淡和以纪德为代表的《新法兰西评论》核心成员们对此书发表的负面评论有关。但纪德本人于1914年向普鲁斯特致歉,致歉内容可参见本书第173页。据说,科克托在这种态度的转变中起到了极大影响,而普鲁斯特对此也十分感激。
但随着一战进入尾声,两人终于还是渐行渐远。据阿尔诺在《普鲁斯特对阵科克托》一书中透露,经历一战归来的科克托在文学风格上发生了巨变,他创作的《好望角》明显呈现出一种黩武倾向,对此普鲁斯特并不欣赏。而在科克托看来,他曾经不遗余力地帮助普鲁斯特对抗文学界,但当他需要这名前辈的帮助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他们从未正式决裂,但两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凶残的虫子蛰死了自己”
1907年,普鲁斯特搬到奥斯曼大道102号。此后,他在这度过了12年时光。
从这里去丽兹大酒店,步行只需10分钟。写作之余,他的一大爱好就是在丽兹大宴宾客。据茨威格在一篇文章中的描述,“他以他的好客和数目巨大的小费而闻名,他给的小费比美国百万富翁给的十倍还要多……”茨威格由此感叹,普鲁斯特“用自己的殷勤和大方赢得了整个巴黎。”
但我们无从得知友谊在普鲁斯特心目中究竟有多重要,他的朋友们似乎都受过他严重的伤害。吕西安·都德有一次写信给科克托哀怨地提及普鲁斯特,“马塞尔很棒,但这也是一只凶残的虫子,您有一天会理解的。”而科克托后来也承认,“听到普鲁斯特谈论友谊,让人很不舒服,友谊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普鲁斯特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奋笔疾书中度过,到了日夜颠倒的程度。1922年9月,几次哮喘的发作彻底损坏了他的身体。普鲁斯特很偶尔才离开自己的房间,那通常是在结束了一天工作后的凌晨4点。这时,他会去丽兹大酒店里进食当天的晚餐。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疏于出门。据记载,他最后一次出门是1922年10月。这次出门让他着了凉,患上感冒,但他拒绝接受治疗,也不让弟弟罗贝尔照料自己。管家塞莱斯特·阿尔巴莱——她和丈夫奥迪龙·阿尔巴莱也出现在这本集子里——晚年在她的回忆录《普鲁斯特先生》中写道,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几乎只喝饮料:一点牛奶咖啡,但主要是丽兹大酒店里的新鲜啤酒,每天由忠诚的奥迪龙去买了来。
1922年11月18日,油尽灯枯的普鲁斯特永远闭上了自己热衷于观察的双眼。他死后的遗照为著名摄影家曼·雷所摄,在本书第92页、93页可以看到。而曼·雷当时正是在科克托的要求下拍下了这张照片。在逝者的床边,科克托似乎理解了吕西安昔日所作“凶残的虫子”的比喻。他说,“他蛰死了自己。”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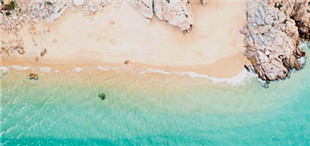
李洁非:通过写作勾勒当代文学史的基本轮廓
“我自己希望通过这一写作,整理出一个当代文学史的‘精神脉络’,可能达不到一览无余的程度,但把基本轮廓勾勒出来。”
 更多
更多

沈从文与颐和园霁清轩
霁清轩长年闭门不开,知名度非常低。“就全个霁清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丘壑一所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