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嵩:鲁迅与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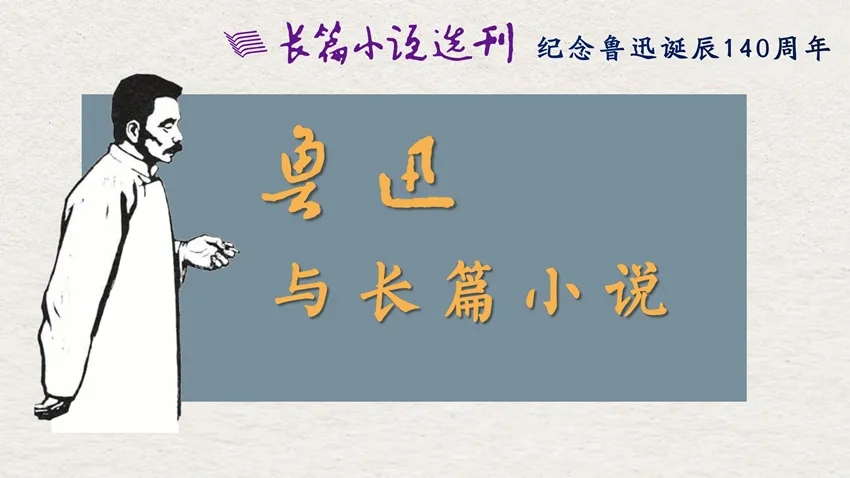
前言
2000年初,王朔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我看鲁迅》,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章一共有五节,其中第二节专门指出了“鲁迅没有长篇”这个早就被人念叨了几十年的问题:
……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有一种为没写过什么东西混了一辈子的老作家遮丑的鬼话,说写短篇比写长篇难,因为结构如何如何之难,语言要如何如何精练,这也就是蒙蒙没写过东西的人。短就是短,长就是长,写长的要比写短的多倾注心血这还用说么?长篇就不用结构了?就该啰嗦?长篇需要用力劳神的地方那是只会写短篇的人想也想不到的。是,小说只有好坏之分,不在长短,同是好小说,我也没见谁真拿《祝福》《交叉小径的花园》去和《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相提并论。
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中间有一个悖论: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乱世,周围有那么多叫他生气的人和事,他再不是那么个脾气,他也就有时间写长篇了;但若不是那样一个时代,周围不是那么个环境,他再跟他弟一样客气,我们就只有在翻阅北洋政府人事档案时才能找到周树人的名字,知道是那个周作人的哥。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宿命,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像样的作品。
“鲁迅没有长篇”,是明摆着的事实;然而,究其一生,鲁迅曾经有过好多次写长篇小说的念头和构想,却始终未能完成,也是事实。
一、《杨贵妃》
鲁迅一生中构思时间最长的长篇小说,是以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为原型的《杨贵妃》。从1921年6月翻译完日本作家菊池宽的短篇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之后起意,一直到1934年1月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最后一次表明自己有写《杨贵妃》的意愿,前后近十五年,可以说贯穿了鲁迅人生的最后阶段。而这一构思,又经历了多次波折。
1921年6月30日,鲁迅在《〈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中写道:“杨太真(按:即杨贵妃)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虽然没有明确说要根据杨贵妃的故事写小说,但是从“我也愿意发掘真实”一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鲁迅的用意。
此事从鲁迅一生的好友郁达夫的一篇文章里也能看出端倪。1926年,郁达夫在《创造月刊》上发表《历史小说论》一文,文中提到一个细节:
说到了杨贵妃,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了。朋友的L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会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了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L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惜他近来事忙,终于到现在,还没有写成功。
熟悉郁达夫和鲁迅之间关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朋友的L先生”就是鲁迅。既然“从前老和我谈及”,说明至少在写作此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按:从鲁迅日记看,鲁、郁二人第一次见面是1923年初),鲁迅就早有“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的想法,但是并不能确定鲁迅要写的是不是“长篇小说”(从“一篇小说”的提法来看,似乎更可能是短篇小说)。
1924年7-8月,鲁迅应邀到西安,为西北大学的“暑期学校”讲学,同行的人中有好友孙伏园。孙伏园日后将回忆鲁迅的文章结集为《鲁迅先生二三事》,其中一篇即题为《〈杨贵妃〉》。文章开头就说:
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经有人提到,手边没有书籍,不能确切征引。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
关于这个剧本的内容和构思过程,则是: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按:即1921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在这里。
恰巧西安讲学的机会来了。鲁迅先生那时几已十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
可是,鲁迅此次西行看到的西安,“的确残破得可以”,再加上“人事有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最终使他打消了创作这个剧本的念头: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所以严格的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只是一个腹稿。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因到西安而被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的了。
孙伏园说“《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事实上,杨贵妃的故事一直萦绕在鲁迅心头,对梅兰芳风靡一时的《贵妃醉酒》也多有微词。例如,著名画家李毅士(祖鸿)在1932年出版了代表作《长恨歌画意》,鲁迅对这个作品意见很大。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鲁迅“能够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间出版的《长恨歌画意》的内容的错误”;而在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鲁迅也批评《长恨歌画意》“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按:即梅兰芳)之流耳”。至于他就京剧《贵妃醉酒》引发的“杨贵妃热”而写《略论梅兰芳及其他》等文章,早已为读者熟知,此处不表。
明确说《杨贵妃》是“长篇小说”的,是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冯雪峰的《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亡友鲁迅印象记》的第十五节“杂谈著作”中提到,“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杨贵妃》。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而冯雪峰则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指出:
……鲁迅先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不很有意思写长篇小说……因为在先生,有自己的一定的工作计划和方针。朋友之间常有人主张他写它几部长篇的,对于这样的劝告,鲁迅先生常没有听进耳里。……
但是,鲁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计划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制作,是欲描写唐朝的文明的。这个他后来似乎不想实现的计划,大概很多人知道,因为鲁迅先生似乎对很多人说过,别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详细。我只听他在闲谈中说过好几次,有几点我还记得清楚的是,第一,他说唐朝的文化很发达,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第二,他以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了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里闪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记得先生自己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但他又说他曾为了要写这小说,特别到长安去跑了一趟(按即一九二四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讲),去看遗迹,可是现存的遗迹全不是古籍上所见的那么一回事,——黄土,枯蓬……他想写它的兴趣反而因此索然了。写这历史小说的计划,应该在一九二四年以前,而终未实现,他似乎不想实现。
前文提及鲁迅1934年1月11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其中关于小说《杨贵妃》是这样说的:
……五、六年前(按:此处应为误记,实际上是十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这个延续了十几年(或许更长?)的“摹想”,就这样一直牵挂在鲁迅心头,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二、《红军西征记》(?)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由于涉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最艰难那段时期的历史,证据不多,基本上只能依靠冯雪峰的回忆:
那是一九三二年,大约夏秋之间,陈赓同志(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陈赓将军)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方面来到上海,谈到红军在反对国民党围剿中的战斗的剧烈、艰苦和英勇的情形,听到的人都认为要超过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中所写到的。大家认为如果有一个作家把它写成作品,那多好呢。于是就想到鲁迅先生了。那时候朱镜我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他把油印的材料交给我送去请鲁迅先生看,并由我和他谈;我所持的理由有二点:第一,当时外国的记者或作家,例如史沫特莱,根据从我们这方面得去的材料写成文艺性的报告,也都成为很宝贵的东西,而以鲁迅先生的文笔来写,当然很能高出一等的,况且他是中国人,社会经验又丰富,无论怎样,可以写得不同一些的。第二,写不成小说,只写成像报告文学一类东西,也就很好了,因为在政治上的作用是一定很大的,尤其由他来写。我记得,鲁迅先生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任务,虽然没有立刻接受,也并没有拒绝,说道:“看罢。”几天之后,鲁迅先生还请许广平先生预备了许多菜,由我约了陈赓和朱镜我同志到北四川路的他的家里去,请陈赓同志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吃了晚饭才走的。鲁迅先生大概在心里也酝酿过一个时候,因为那以后不久曾经几次谈起,他都好像准备要写似的。别的话记不得,象下面这几句,我还记得清楚的:“写是可以写的。”“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象《铁流》似地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但后来时过境迁,他既没有动笔,我们也没有再去催他了。不过那些油印的材料,他就保存了很久时候;我记得一直以后他还问过我:“那些东西要不要还给你?”我说:“不要,你藏着如不方便,就烧毁了罢。”在他逝世以后,许广平先生有一次还谈起过,说鲁迅先生曾经把那些材料郑重其事地藏来藏去的。(冯雪峰:《回忆鲁迅》)
1956年,作家张佳邻采访了陈赓将军,写成《陈赓将军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一文,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文章的开头说:
我们听说过,鲁迅先生曾经想写一本关于红军的书,这是由于和陈赓将军的一次会面引起的。在那次会面时,陈赓将军为鲁迅先生讲了许多红军的战斗故事,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了鲁迅先生。后来,不幸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没有写成。但是,这些材料鲁迅先生一直珍惜的收藏了很久。在白色恐怖下,保存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这些材料经常要移动地方,但是鲁迅先生一直未舍得焚毁。听说甚至当年陈赓将军在介绍战斗情况时,随手所画的地图,鲁迅先生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幸运能读到鲁迅先生描写红军的书,但是从这件事所体现的,先生对红军的关怀、期待、爱,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我们曾为此事去访问过陈赓将军。
文章以陈赓口述实录的方式回忆了同鲁迅的这次会面,内容与冯雪峰的回忆基本相同。此文曾被收录进中学语文课本,因此广为流传。
另一个证据,知道的人较少,但是来自鲁迅夫人许广平亲自写的文章,故可信度较高:
大家知道,鲁迅生前曾经非常希望能够写出一些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小说,他听到许多有关红军的英勇事迹以后,曾经打算写一部像《铁流》那样的作品,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亲自约请红军中的著名将领谈话,从事资料的搜集工作,但是就因为感到自己遭到敌人的包围,没有机会和红军直接生活在一起,没有直接处于这个“斗争的旋涡”之中,唯恐自己的创作不能更好的表现红军的英雄形象,因此只好忍痛放手。(许广平:《文艺——革命斗争的武器(谈谈鲁迅的写作态度)》,1961年9月24日《工人日报》)
这部小说始终没有写出来,因此自然没有题目。但是在陈梦熊的《瞿秋白对鲁迅创作长篇小说的关注和期待——杨之华两封遗札所示的一段史实》(《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一文中,却径直称之为《红军西征记》,不知有何根据。因此笔者在本节小标题后加了“(?)”,以示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同意写的是一个“中篇”,陈梦熊的文章也称《红军西征记》为“中篇”。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篇小说”与“中篇小说”的区分并不严格,当时的许多长篇小说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篇幅比较长的中篇小说,且当时中篇小说出版单行本是很常见的事,因此笔者仍然将这部只存在于鲁迅构思中的小说为“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冯雪峰、许广平都说鲁迅打算将这部小说写成“《铁流》那样的作品”。鲁迅自觉地将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这部著名长篇作为学习对象,或许也意味着有将这部小说写成《铁流》那样的“长篇”的可能。
三、关于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小说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于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很快便同鲁迅相识。有趣的是,据她回忆,鲁迅“常常对我谈起,他打算写一本以他自己的经过为基础的长篇历史小说的计划,可是在他的国家翻滚着的那种社会反动势力,使得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戈宝权辑译:《史沫特莱回忆鲁迅》,见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辑:《鲁迅研究年刊1980》,第47页)欲写“长篇历史小说”而“以他自己的经过为基础”,似乎很难同《杨贵妃》联系到一起。这或许说明,鲁迅还曾有写另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打算。
就在逝世前一年(1935年),鲁迅曾经对画家王钧初说自己“正在预备写一部大的东西,从‘辛亥革命’写起”,而“这件东西如果我不写它,恐怕再没有别人去写了”。将这条史料同史沫特莱的回忆相对照,我们大概可以明白所谓的“以他自己的经过为基础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个什么样子。
关于这部小说,仍然是以冯雪峰的回忆最为权威: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大病前后,鲁迅先生曾屡次谈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有时也谈起高尔基的巨篇《萨姆金的一生》,也谈到长篇小说的严格形式的解放。有一天,我们谈着,我说鲁迅先生深知四代的知识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他当时说,“倘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接下去,我们又谈到长篇小说……而有一天,这是在他大病后精神较好的时候,就极自然地归结到他写长篇小说的问题。那时他说:“这倒可以想想看,如果还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是可以的。或者,想写的文学史再搁一搁也可以,——即同时写也可以。”大约过了一星期,一晚再去访问的时候,鲁迅先生说道:“那天谈起的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曾想了一下,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又加说,“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分量可不小。——不过一些事情总得结束一下,也要迁移一个地方才好。”可知这已经是鲁迅先生有意的存心的计划了。然而这将反映中国近六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国知识阶级的真实的历史,并将创造了新形式的巨制的计划,终于因为鲁迅先生的死从我们的文学史上被夺了去了,这才是永久无法补偿的损失。(《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
请注意文中提到的时间:1936年6月。此时距离鲁迅逝世不过三、四个月。可以说,这部关于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小说,是鲁迅在1935年底写完《采薇》《起死》等短篇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酝酿的一部小说作品。“如果还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语成谶。
结语
许寿裳曾说,鲁迅的许多腹稿和未成稿“终于没有写出,赍志以殁了”,是因为他“没有余暇”且“没有助手”(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笔者的老乡、山东东营利津县出身的批评家李长之则认为,鲁迅“内倾”的性格是他写不了长篇小说的根本原因:他“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倾’的。……宴会就加以拒绝,群集里就坐不久,这尤其不是小说家的风度”;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鲁迅“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李长之:《鲁迅批判》)。冯雪峰则对鲁迅寄予了“理解之同情”:“我觉得他不很有意去计划写长篇者,主要的是他埋头在现实社会的短兵相接的斗争里,从他的岗位来说,对于现在中国社会,他以为社会批评的工作比长篇巨制的作品更急需。记得他曾说:‘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重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这些原因,或主观或客观,纠缠在一起,使“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在《鲁迅全集》里成为空白。
1935年1月17日晚上,鲁迅又给山本初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给自己的一生下了一个精确的定论:“我是散文式的人”。“散文”,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许,不写长篇小说的鲁迅,才是完美的鲁迅。
2021年9月25日,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