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创作《红日》的故事

吴 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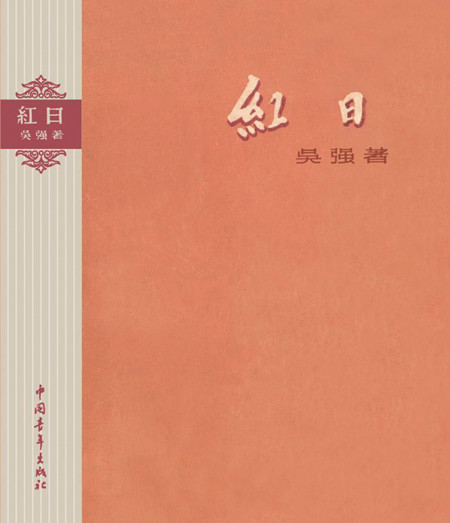
《红日》
父亲吴强去世已经30余年了,我们对他的思念非但未减,反而与日俱增。我们对父亲和他的作品小说《红日》,对那场一战定乾坤从而转变国共内战局势的规模巨大的大军团作战的孟良崮战役,对这场战役中我军的战略战术、大规模的部队协调以及大战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父亲能有机会参加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性的大战,以他的笔墨,忠实于历史,生动地描绘刻画我军的胜不骄、败不馁和从弱到强,再现这场伟大战役的规模,文情并茂地记录这段历史,真是一件幸事。能够完成这样一部脍炙人口的巨作,他和他的书历经多方磨难而不倒,也绝非偶然,是与他的成长环境、经历和品格分不开的。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他为创作所经受的压力、磨难和写作的不易。无论历史以后如何演变,这段历史已经被忠实地记录下来了,这本书也会作为中国军事文学经典被永远地传承下去。
要写好这样一部军事题材小说,必要条件就是熟悉部队生活、各级领头和战士。1938年8月,父亲参加新四军,起先是参加战地服务团,做些慰问演出。他写了话剧《激变》《诡计多端》《皖南一家》,与战友们合作写了《繁昌之战》 等在部队演出,先后结识了粟裕将军、陈毅司令员。1943年,经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同意,爸爸被分配到华中四分区敌工部工作。他改扮成商贾,走南闯北,深入虎穴,依靠群众做侦察、分化和争取敌军的工作,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这本书中的人物都是生活里实际存在的。比如,军长沈振新是以王必成司令为原型综合了其他将领的特点,副军长梁波是以皮定均司令员为原型。王必成司令员告诉别人:“有他个吴强的,书中的梁波,活脱脱地画出了个皮定均,气派,举动都八九不离十。”刘胜团长的牺牲也是一例。在实际生活里,刘胜团长在大战前中了敌人的埋伏不幸牺牲,当时,王必成司令悲痛欲绝,闭门三天不出,请求一定要让他去打张灵甫,为刘胜团长报仇。陈毅也非常理解他,他的愿望也确实如愿以偿。战友之间的友谊跃然纸上。许多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活灵活现地再现了残酷战争中的人性和人之间的真情实感。而这也是最扣人心弦的。戎马倥偬之下很难坐下写作,写的笔记、积累的资料也很容易丢失。爸爸就不断地在脑海里重复回忆经历的那些故事和人物,使他们铭刻在心中,活在心里,以后写书时,那些人物和故事便跃然而出、栩栩如生。在他心里,他已经和红日里的主人翁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了,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书动笔于1956年,经历240天写成,于1957年出版。可是他的构思和腹稿,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至于对军队的将领们的熟悉和了解,则时间更长。
一个人最珍惜的莫过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感情最深的莫过于乡情和亲情。写作需要激情,父亲的写作激情就来自于他对战斗果实的感情,对并肩战斗的战友的了解和友谊,还有对家乡的热爱。第二次涟水战役的失利,他亲眼看到部队后撤,家乡受到敌人的蹂躏,那份刻骨的心痛和战友们报仇的强烈愿望,促使他要把这个历史写下来。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之时,父亲在华野六纵队任宣教部部长。战斗非常激烈,双方死伤不少。战斗结束后,他看到一副门板上躺着一个人,战士说此人拒不投降,被击毙了。掀开毯子一看,叫来认证的敌军团长战俘哭了起来,证实就是张灵甫。爸爸激动极了,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历史写下来。1949年7月,他随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的第十兵团南征福建、进驻厦门。未来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开始搅得他寝食不安了,迫使他尽快进入写作状态,常常一下笔就通宵达旦。有时写到感人处,竟会情不自禁地失声恸哭,他完全进入了他和他的那些主人公的世界,只跟书中的人物交谈,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
1952年,父亲转业地方。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他终于带着8万字的《红日》故事框架和部分初稿,还有一大皮箱资料,征得上级批准,躲进无锡大箕山,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抽两三包烟,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自己定下指标,当天不完成6000字的数量,就不上床睡觉。超强度的劳作,使他两鬓顿生白发,面容憔悴,连走路也步履蹒跚。有一次上街,竟一头撞在人行道边的树上,还向树连声说对不起,惹得行人哄笑。初稿完成的当天,他几近虚脱,招待所的同志们只得把他送进医院输液抢救。半个月后,他又提起皮箱到了杭州的一个部队招待所,接着写第二稿。整整持续4个月,这部40万字的巨作才算画上了句号,此时他已整整瘦了30多斤。父亲在写作中投入了全部精力,在创作中获得极大的快乐,但也在这极为艰苦的劳动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我们家住在上海复兴西路的12层楼高的卫乐公寓的8楼A室。四间屋子,两间朝南,两间朝北。爸爸的书房是一间北屋,一张大写字台临窗放置,深绿色的呢子台布上铺着玻璃台面。他定下规矩,写作时不要叫他吃饭,来客人也不要叫他,不要到他的书房去打扰他。有一次,老二样样仗着受爸爸宠爱犯规了,到书房去叫他吃饭,一打开门,只见满屋子的烟雾缭绕,爸爸正在屋里踱步,神情激动,眼睛红红的,似乎哭过了,爸爸看着她,一反往常的和蔼可亲,严厉地要她出去,她立即意识到写作是个神圣的感情活动,是不可以打扰的,连忙退了出去。后来,为了避免干扰,爸爸有时到上海作家协会租下来给作家写作的12楼去,有时也到外地去写作。
我上初中时,每天走5里地去上学,很早就要起床。有一次,错把3点半看成6点一刻,起床看到爸爸的书房里还亮着灯,发现他还在写作,我惊讶地问他为什么还不睡。爸爸看到我也大吃一惊,问我怎么这么早就起来,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回房间睡觉,他自己继续写作。爸爸随身带着一只拇指粗的带灯的圆珠笔,睡觉时放在床头。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晚上如果灵感一来,想到什么,就可以马上写下来。那时的写作又称“爬格子”,都是一笔笔地写,一遍遍地改,有时要挪换段落或者章节的位置,爸爸就用剪贴的办法,常看到他把手稿剪得一条条的。最后还要誊写后才能交稿。爸爸通常都是请人誊写,但有时也会要我替他誊写稿件,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刻了,觉得受到爸爸的赏识,可以为他做点事。
“文革”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还记得在1966年11月的一个晚上,爸爸妈妈跟我说,你带着老二样样一起出去走走吧。爸爸完全凭他的记忆,拿了一张纸铺在饭桌上开始画路线图。他是那么熟悉地画了从上海到山东的路线图,连城镇之间的距离都记得,不走大城市,全部走小城镇,穿过沂蒙山区,经过孟良崮,走到北京。我们发现,爸爸的记忆如此准确,城镇间的距离都对。这是他的家乡,是他生长和战斗的地方。他对这个地方的感情如此深厚在书中处处可见。我们带了一本小小的地图册和爸爸画的路线图,走了1700公里,用了57天。我们去到孟良崮,爬到崮顶,看到《红日》电影中张灵甫指挥部所在的小山洞, 离洞口不远的山壁上刻着“张灵甫被击毙于此”。沿途还有许许多多牺牲战士的坟头。在山东境内,碰到北京七院14所的一小队人,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人很和善地说:“你们就两个人走啊!要不,就和我们一起走吧!”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走完了后半段旅程。我们没有坐一步车,硬是从上海步行到北京,到北京是1967年的1月17日。我们有时一天走上百里地,就是想走爸爸当年走过的路,看看他们战斗过的地方。其实爸爸妈妈要我们小小年纪便离家远行,是想保护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心理受折磨。与其在家里让幼小的心灵备受打击和伤害,不如离开家到自由空间去飞翔。那年我20岁,妹妹才16岁。到了北京我和妹妹就都病倒了,我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我在病床上才闻讯上海的一月风暴,随着这场风暴的愈演愈烈,我们经历了后面的更残酷的冲击。记得那是个寒冷的晚上,1968年4月的一天,我依偎着妈妈坐在床上,灯光暗淡,爸爸坐在床尾的椅子上,人几乎是陷在黑暗里,对我们说“我明天很可能回不来了,你们要有准备”,我只觉得浑身发冷,紧紧地靠着妈妈,恨不得钻到妈妈怀里。1968年4月24日,爸爸没有回来。这一次分开,直到7年后才见到他。我们全家都一直生活在这本小说诞生后产生的巨大的漩涡和影响之中,尝尽生活的酸甜苦辣。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的一生就像是一部惊心动魄、百转千回的小说,一部婉转曲折、回肠荡气的电影。从儿时和小伙伴讲《西游记》的故事开始,到百折不挠的求学过程,从开始用笔墨写作,到写剧本参与抗日、携笔从戎,莫不如是。行军战斗之余,他收集积累资料,不忘写作。笔记本和装有74师《士兵报》的一包资料在孟良崮战役后两个月行军渡驹河时不幸丢失,他不灰心,再从头开始。解放后,不得已离开部队回到地方,反而得到机会专心创作,终于写成巨作《红日》。一开始到处投稿,可是音讯全无,最后还是文友沈默君联系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主任江晓天。中青社一向以“我们只看作品,不管作者是否有名”为宗旨,江晓天欣然收下稿件,看了之后深受作品的魅力感染,觉得这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的作品,交给编辑部副主任陶国鉴,陶国鉴看了以后,觉得确实写得很好,文字技巧也无须修改,立即发排。《红日》因而喷薄而出,爸爸也从此一举成名。正喜见小说改编成电影之时,不想再一落千丈,成为革命对象,直到1978年才得以昭雪平反,10年间都不得写作。手稿《堡垒》在动乱中被抄走丢失,他又一次重写。父亲吴强的写作生涯是如此一波三折,像过山车似的起伏动荡。他被人爱,被人骂,更被人怀念。我们后来在自己的奋斗生涯中,更深深体会到父亲的不容易。笔记本、资料、手稿都是心血的积累和结晶,是劳动的成果,一旦丢失,心痛是刻骨的,打击是巨大的。爸爸经历了这么多次打击,却从未气馁,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最为爸爸感到骄傲的是他的真诚,实事求是。他写了我军的胜利,也写了我军的失利,刻画了我方的英雄,也写出了英雄的“缺点”,这些更显得书中人物的真实可爱。他写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有高度的军事素养、精明能干的敌人,这才能凸显胜利的不易。他写出了一场真实的历史性的宏伟大战,写出来我们为什么能打赢,敌人为什么会失败,而不是格式化地、抽象地把一切归功于思想的伟大和敌人的愚蠢。人们从他的书中学到了历史,学到了奋斗的精神。世事可以变迁和演变,但是历史事实则坚如磐石,时间磨灭不了《红日》的光辉,书也会因其忠于史实及高度的艺术价值而得以永生。文章的最后,希望能以我们姐弟为父亲写的诗歌来作为结尾:
战乱动荡满沉疴,
携笔从戎挥金戈。
人生最难为求是,
《红日》不落颂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