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笔记本》:一种“新文化”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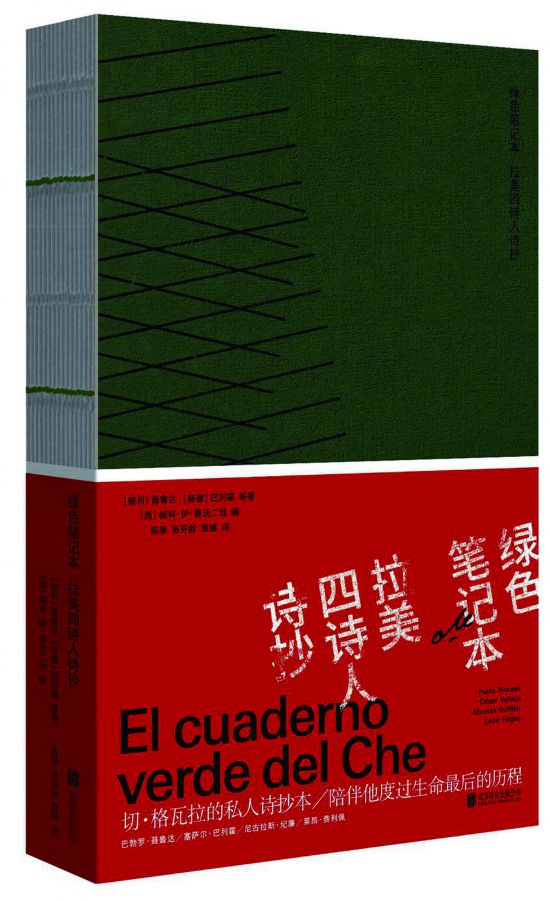
《绿色笔记本:拉美四诗人诗抄》书影
《绿色笔记本》是一本罕见的诗集,凸显了切·格瓦拉这个20世纪最著名的革命者作为诗人、诗歌读者的身份,这除了使他离我们更近,更了解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外,也使他离我们更远了,似乎还有很多我们无法想象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天赋,都在切的身上被证实了。《绿色笔记本》表明,他除了高尚的情操、英勇的精神、敏锐的头脑之外,还有可观的文学修养。这本由他亲自抄录的诗集,伴随着他最后的日子,里面有情诗,有借鉴了黑人民歌的富有节奏感的作品,也有富有战斗性的篇什。也许正是这些诗篇,帮助他度过了在玻利维亚山中受困的日子。
其中第一首《黑色使者》,我第一次接触是在胡旭东老师的世界诗歌课上。那门课程的时间是在周二下午,十几个人用整整两个小时翻译和细读一两首诗,每个同学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准备,以弄懂每一个词在原文中的意思。印象中,塞萨尔·巴列霍是与法国诗人雅克·普雷维尔放在一起讨论的,构成沉重与轻盈的奇妙组合。此外,我们还选译了尼卡诺尔·帕拉等拉美诗人。我也是在那门课上第一次见到《绿色笔记本》的译者陈黎老师,而袁婧则是那门课全程参与的同学。
在切·格瓦拉选取的四个诗人中,塞萨尔·巴列霍、巴勃罗·聂鲁达、尼古拉斯·纪廉都已为人所知,只有莱昂·费利佩在中文世界欠缺相应的名声。聂鲁达在这几个人中流传最广,他的诗有一气呵成的气质和尽量接近大众的语言,奇幻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腾挪跌宕的感官愉悦,创造了一种把拉丁美洲的土地和海洋母性化、神圣化的修辞范式。切对聂鲁达作品的选择方式,则是颇为让人意外的,就像编选者指出的,他没有选择《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却选择了《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中的多首作品,包括《女体,白色小山》《我们甚至失去了》《今夜我可以写出》《绝望的歌》,这是聂鲁达20岁时写作的情诗的一部分。此外,像《我双腿的仪式》以对男性身体的古希腊式的赞颂,肯定了人自身的美感和价值。这些诗表明,切并不是从纯政治性的角度选取作品的。
与聂鲁达原始的、带有雄性荷尔蒙的爆发力相比,巴列霍则具有一种质地完全不同的激情,就像在地壳下穿透岩石的岩浆,他的力量是内省的、私密的、不可见的,但是也让人目眩,甚至带着毁灭性和可怕的洞察力。在聂鲁达那里,悲伤是令人愉悦的,而在巴列霍这里,快乐也隐隐让人不安。巴列霍的《同志爱》的正文,就字面而言没有什么明确的主旨,但是阅读的过程让人想到基督式的博爱:“今天没有人来问我问题;/今天下午,没有人来向我问任何东西。//我一朵坟头的花也没看到,/在这样快乐的光的行列里。/原谅我,上帝:我死得多么少啊。”这首诗和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构成隐含的对比。里尔克的诗有一个最终把注意力转向抒情主人公“我”的结构,“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里尔克这首诗写作的重点,是世界上的人的哭、笑、生、死与“我”的相关。而在巴列霍的诗中,也涉及人与人之间隐微的、心灵感应式的联结,但是其指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反过来的,“原谅我,上帝:我死得多么少啊”,它不是里尔克那里现象学式的凝视,而是一种对于“我”而言切切实实的“承担”,敏感的诗人甚至隐约把这份“承担”转换成了罪愆意识,诗人认为,与形形色色的死亡和坟墓相比,自己感知到的快乐是可疑的。《给我的哥哥米盖》也是一首杰作,它叙述孩子世界里的捉迷藏和成人世界理解的死亡(消失)之间的关联,让人想到威廉·华兹华斯不朽的《我们是七个》,尤其是结尾的部分,“啊哥哥,不要让大家等得太久,/快出来啊,好吗?妈妈说不定在担心了”,寓深沉于童稚,用捉迷藏的口吻表达了对哥哥的追悼和怀念。
尼古拉斯·纪廉的诗从1959年就被翻译到中国,成为和聂鲁达一起被中文世界接受的拉美人民诗人。《黑白混血女郎》以带有“大男子气”的诗人视角,写自己追求一个“混血女郎”而不得,以至于要气急败坏咒骂对方长得“难看”,“我知道,黑白混血女郎啊,/黑白混血女郎,我知道你说/我的鼻子/扁平得像领带结。//啊,看看你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大大的嘴巴,/红通通的卷发”。情绪转折过程中的讽刺与自得感溢于纸上。尤其是最后一节,“但愿你啊,黑白混血女郎,/能了解真相,/我已经有我的黑女郎,/我一点也不爱你!”这种求爱失败后略显“尴尬”的自找台阶下的过程,很少能在之前的经典诗人那里读到,它展现的情诗范式也不再是忠贞、骑士之爱抑或是波德莱尔式的“擦肩而过的女人”,而是用调侃的语调表露了“诗人”尖酸、刻薄、羞于认输的一面。
切也在纪廉战斗性的作品中选了一些抒情性的诗,比如《蒙特罗老爹的葬礼晚会》《记忆之水》《炉中石》。尽管《蒙特罗老爹的葬礼晚会》的主题涉及对一个黑肤老人的悼念,但是结尾几行却留下唯美的记忆,译诗也遵循了美妙的节拍:“今天在我家院中/拂晓时出现月亮;/她以弯钩凿开大地,/牢牢地嵌入土壤。/孩子们将她捧起/为她洗净脸庞,/今晚我把她带来/请你枕在这轮白月上。”纪廉的诗是这几个诗人中突出处理拉丁美洲混血文化,尤其是黑人文化的,比如《两个祖父之歌》,把两位“祖父”分别取名为费德里科和法昆多,根据译者注释,这两个名字分别来自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和阿根廷作家、政治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也象征着西班牙文化和拉丁美洲文化的融合,这无疑也表明了切的精神追求。
莱昂·费利佩是一个在中文中还比较陌生的名字,跟洛尔迦、维森特·阿莱桑德雷同为西班牙著名文学流派“二七年一代”的成员,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无法归类的诗人。这不仅因为他的风格多变,而且因为他作为药剂师、翻译家以及生活于墨西哥的西班牙流亡群体领袖的身份。虽然《绿色笔记本》选他的诗最少,只有9首,但是其中的《大冒险》这首长诗长达30多页,行数比聂鲁达的《马祖匹祖高地》还要多。切只抄录了《马祖匹祖高地》中的第八、第九部分,对《大冒险》则抄录了全文(除了最后两行,进行了切诗人式的改写——省略),因此总体上,费利佩在笔记本中占据的比重并不低。费利佩的诗歌是四人中欧洲背景最强的,其他三人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土地和文化有很深的认同,虽然费利佩1938年就作为共和党激进分子被西班牙驱逐,流亡到墨西哥,且晚年长期在墨西哥生活,但他的诗中频繁引用塞万提斯等西班牙人的作品,而且充满来自《圣经》的宗教隐喻,具有很明显的欧洲文化色彩。在切的笔记本所选的诗中,有好几首都指向与《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在诗中是“大司铎”)的对话。不过,在形式和内容上,费利佩的诗是富有先锋派色彩的,很多长短不一的、口语化的自由诗,在意象跳跃的幅度上很接近聂鲁达最晦暗时期的《地上的居住》,一定程度上,这些诗也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在《大冒险》中,他还流畅地使用了元诗策略,跳出来就自己的写作方式进行辩护,并多次向读者、译者发言。比如,“另外,我认为这种修辞/最容易翻译成所有语言。/如若一句诗需要飞行很远/——这首诗就会飞行很远——/这双翅膀是最合适的。”这首长诗以热情的理想主义歌颂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盲目”行为,也许切即是被诗中人物身上的这种精神所感染。
在四人的作品中,纪廉和聂鲁达都涉及西班牙内战以及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的遇害,比如在《我述说一些事情》《哀歌第四》中。除此之外,诗中还有玻利瓦尔、蒙特罗老爹、埃米特·提尔等或杰出或平凡的名字。这些名字也许构成了除了四位作者之外的补充信息,告诉我们切的生活受到哪些历史人物的影响。不仅编选者和译者,想必这本书的每个读者,都感知到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解谜过程。毕竟我们对切的一切都如此感兴趣,不会放过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任何细节。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的英雄,一个有诗人和文学家眼光的革命者,在他的日记和《论游击战》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理想主义是如何通过物质性细节落实的,其中有很多对革命行动所作的纯粹技术性的指导:如何搭帐篷,如何收集食物,如何破坏敌人的基础设施……他像是一个不厌其烦的“管家”,把一个普通士兵所需要考虑的饥寒、体能问题当作头等大事。其所有论述的前提是,游击队的弱势地位和物质匮乏,以及政府力量的强大,因此需要用最小的损失、最高的效率来完成最有爆发力的行动,需要分散兵力、化整为零,这几乎使游击战术变成了一种意象主义诗歌原则的对等物。埃兹拉·庞德强调,诗歌要用“凝缩”表达情感的复合体,不要使用过多形容词,而要多使用动词。切的文体也跟意象主义的观点具有同构性,他的文风经济、简约,词汇密集、富有效率,不作过多的修辞,内容平实、可靠又高屋建瓴,富有实践性。这也反映在他对诗歌的认知中。在编者序中,我们读到:
切从未将《走吧,预言黎明的炽热先知》这首诗送给菲德尔。显然,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首好诗,只想把它留作纪念。
几年后,《绿色橄榄树》杂志的主编莱昂内尔·索托发表了这首诗,切愤慨万分,传信警告他不应该未经允许发表任何作品,更何况是‘这些糟糕透顶的诗句’。切将他的诗歌视作隐私。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切务实、诚恳、接近完美主义者的自我约束的态度。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局限,就此而言,他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些诗也从侧面传递了切自己对革命的认识:革命不仅是一种武装斗争的实践过程,而且也涉及“新人”“新文化”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的创生过程。弗兰茨·法农等6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也颇有先见之明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切携带着一本诗集去闹革命,并随身带着自己的手抄诗集死去,这个细节本身也是一个象征,是理解他留给我们的遗产的重要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