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的故事该如何讲述? ——关于《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一席谈

T.S.艾略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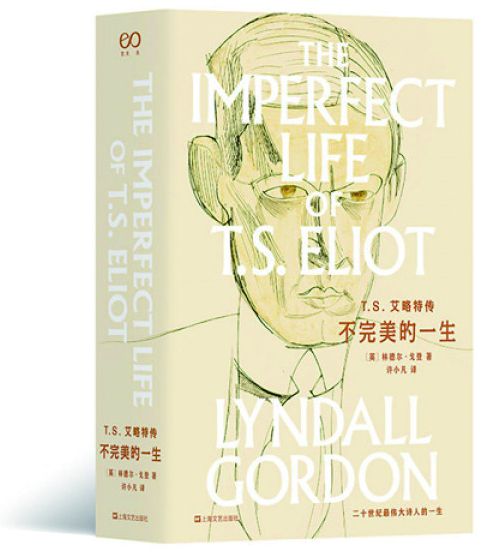

张新颖 许小凡 张定浩
主持人(本书编辑):很荣幸邀请到张新颖、张定浩、许小凡三位嘉宾,来一起谈谈《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这本书。张新颖老师的传记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大家可能都读过或者有所了解,张新颖老师也是极熟悉艾略特的读者,他有一篇流传非常广的文章《T.S.艾略特和几代中国人》,文章从徐志摩、叶公超、赵萝蕤、卞之琳、穆旦到袁可嘉,一直绵延到如今自己这代人。张定浩可以说是这本书的起因,因为他读艾略特,促使我想重新读艾略特。张定浩是诗人,这几年以写批评文章出名。如果说在批评文章中他有什么师承的话,我想艾略特一定是最重要的人。我也很幸运地遇到译者许小凡,如果没有她,我肯定没有这个勇气在这里跟大家推荐这本书。许小凡用了两年时间,一字一句地打磨它,像磨镜子一样,这样才成就出这样一部作品。
我想从一个简单的话题开始:你们是怎么接触到艾略特的,怎么开始读他的,以前读他和现在读他有什么不同?
张新颖:在80年代中后期,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的文学正好处于实验、探索的阶段,所以当时的人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有非常强烈的兴趣。我作为学生,正好赶上这样一个时代,今天看起来很难读的东西都是在那时候读的。我最早读到的是8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本书的主编是袁可嘉,他选的是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选了穆旦的译文,《荒原》选的是赵萝蕤的译文。那时不觉得这些作品那么难读,当然其实也不一定读懂了,稀里糊涂就卷入到对这些作品的兴奋中去了。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看到了和以前不一样的文学,而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寻求这种不一样。我们对那些一样的、熟悉的东西可能是厌倦了,所以那个时候它引起我们心智上的兴奋。那个时候我很年轻,现在老了,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人读一个东西的时候,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艾略特自己也发现了。艾略特曾说我年轻时候写的东西比较受欢迎,年老后写的不太受欢迎。年轻时写的东西语气明确,很决断,当然也很率真,稍微老一点就变得复杂,变得犹疑,但是都充满了智慧。所以我们对艾略特的了解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一开始让人很激动,慢慢地我们会理解除了激动之外更多、更复杂的东西,因为他的诗属于那种不是一下就能理解的诗。今天读和不读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怕引起误解,我要解释一下:你读过的东西会嵌入你的身体里,它会变成你的一部分,即使以后不读它了,它也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抹也抹不掉。
许小凡:艾略特在国内还是一个现象,但其实他在英美学界已经慢慢成为边缘了。在我们国内的英语系,大家最开始接触的都是艾略特。因为他的诗不管从音律层面还是从内容层面,确实都太美了。我一开始接触到的是《普鲁弗洛克》,后来在国内英语系读到《小吉丁》。我上研究生时,在20世纪英美诗歌的课上跟着读了这本传记,还接触了海伦·文德勒对艾略特的批评,当时选了一篇讲《荒原》的。后来误打误撞,我走上了艾略特研究的道路。回过头想,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循章摘句地读,我们会把艾略特视作一个警句式诗人。但是当我进入知识生产系统之后,我可能更多地关注艾略特作为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的身份,比如出版商、编辑。我记得书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艾略特当时做了一本文学刊物,叫《标准》。创立《标准》就是为了打破既有的文学建制,打破那些将死的文学传统,想要引入一套新的传统。他管自己和庞德这些同道中人、能够带来创新的人叫“囚徒”,意为从文学内部突围。但这套新的传统只能够有策略地建立,他做《标准》时,有个策略是大规模地刊登已经出名了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但是在里面插入新人的作品,就好像从内部炸开一个保险箱。
张定浩:我很惭愧,因为我很晚才读艾略特。像《荒原》,因为很有名,很多人以为自己读过,但其实没读过。我就以为自己读过,结果25岁后才接触到它。最早看到的是艾略特的评论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他的诗歌我接触得太晚,可能没有对我的写作产生太大的影响,这是很诚实的想法。我觉得他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比较和分析,喜欢用强硬的判断和给人排列次序的等级制的区分,这些东西让我印象很深。尤其在这样的多元时代,大家不愿意做等级式的区分,只是强调不一样。但是在艾略特心里好像有一个严厉的天使,读他的文章像被这个严厉的天使带领着,有一种俯瞰式的视角。
主持人: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读一个诗人的传记,读一个作家的传记,读一个哲学家的传记,有必要吗?这种阅读有意义吗?
张定浩: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就好比,关键不是传记好不好,关键是谁写,写得如何。今天这本书的作者不在场,我就不表扬了,译者要好好赞美一下。这是我读得特别舒服的一本书,从中文语感来讲我特别喜欢,就好像用我喜欢的语言写成的。其次,在现代中文世界里,关于现当代汉语诗人,几乎没有这样有分量的书。我们的诗人传记常常是做一些很无聊的琐碎的史料研究,以至于大众对于诗人的印象出现各种扭曲,这和这些传记多少有些关联。比如泛滥成灾的林徽因的传记、海子的传记、穆旦的传记,等等。
许小凡: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从两个角度想。第一,为了生活读。有人觉得传记不值得读,奥登也这么说过,没有必要通过传记解读作品,因为传记不可能全然真实,根据对一些传记事实的悬想解读作品的话,会有相当大的问题。但是为了解决你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这本传记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这绝非一本八卦式的传记,里面有很多非常细腻的铺陈与分析,关于感情,关于知识分子在重大历史时刻的选择。阅读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对艾略特发生认同之后,我们会关注他在做重要选择时是怎样思考的。我觉得这是读传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认同感,且有介入点。要做诗歌研究的话,传记是要谨慎看待的。目的不一样,传记对读者的作用也不一样。
张新颖: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人们对从作家的人生经历来解释作品的方法特别厌烦,我上大学的时候,新批评的主张已经变成了文学理论最基本的观念。那时奠定的观念就是要把文本和作者区分开,要关起门来读文本。当然,不存在可以被关起来的文本,一定要把这个文本和写下这个文本的人割裂开来,声称没有关系,这是自欺欺人。为什么是这个人写下这个文本,而不是我?其中当然是有关系的,并且这个关系是无法被取代的。只不过是说,我们的研究有没有能力在作者和文本之间建立起更可信赖的联系,不是说要否定这个联系。不少人反对所谓的外部研究,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很差的外部研究和很差的内部研究一样糟糕,也有光读文本读得一塌糊涂的。我其实是持比较简单的、开放的态度。如果我们相信文本的丰富性,相信它包含着很多信息,我们就不应该拒绝各式各样的手段,只使用一种手段是不对的。当然,前提是传记是个好传记,传记是需要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以前读艾略特的诗时,很少考虑到他的宗教问题,即使考虑到也是模糊的。但是读了这本传记之后,很多以前想不明白的问题能够弄明白了,这就是传记可以告诉我们的。
主持人:请三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印象深刻的段落或者句子。
张定浩:读了这本传记之后,我有一种在炮火当中、在防空洞里与各种人一起听《四个四重奏》的感觉。艾略特跟社会是有关系的,只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产生关系,而不是直接迎合他的时代,是在慢慢塑造这个时代。我觉得这是我读这本传记后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我以为《荒原》只是一个隐喻,读过以后发现它里面潜藏着很多感情,那些生活中不堪的事情,那些难以面对的时刻。好的传记是对一个人的内部研究,作为文本来讲,传记是外部研究,但是对于一个人本身来讲,传记又成了内部研究。好的传记尤其是作家的传记,应该触及这个人如何面对生命中最艰难、最不堪的时刻。周围人不会知道那么多,只知道一点点,那些都是碎片,只有他自己知道如何挨过生命中特别难挨的时刻,等待着未来某一刻一个人把所有信息拼在一起,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一天这个人抵达了,这是特别动人的时刻。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跟普通人一样,有各种各样难堪的时刻,但是不同在于,他可以用艺术把它们转化成一种不朽的时刻,把这种历史时间转化成一种永恒时间,把每个人都遇到过的时间转化成会不断重复的永恒的时间。这个人是如何做到的?这是好的传记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戈登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一般传记都会围绕传主说话,写传记的人会是传主的粉丝和研究者,对传主周围的人态度会比较轻蔑。而这本传记的作者对艾略特周围的女性都抱有同情的态度,但也不是要拔高她们。她特别理解她们,理解艾略特身边每个人,尽力做到了一种平等,平等地对待一个伟人和在伟人光环照耀下没有那么重要的人,这也是特别难得的。艾略特的第一个妻子去世之后,艾米莉以为他要和她结婚了,我们从书中能够读到,从一个爱着艾略特的女人的角度来看,这会是怎样一个故事。这段很短,是作者的感慨,但这些话特别精彩。艾米莉是艾略特年轻时的初恋,他们后来又遇见了,等于有二三十年的情感纠葛,两人互相写了很多封信,据说这些书信今年10月份才能公开。
许小凡:这确实很让人怅然。大家一直在等着这批书信解禁,我个人不太敢看这些信。艾米莉写给艾略特的信,他让朋友烧毁了,另外一部分今年解禁。刚才张定浩老师讲的这些我都非常认同。艾略特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如何与历史、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产生一种有效的联系?比如很多人批评艾略特在二战时没有写下明确反对德国纳粹的作品,没有写过带有政治性的东西,但同时,《小吉丁》算是一首爱国诗、战争诗,也是艾略特对于战争的反映,它是艾略特在战争中对英格兰产生的一种新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恰恰是通过返回种种历史时刻来达到对当下有距离的理解。这两天为了准备这场活动,我重新读了艾略特有关诗歌批评的一些文章。艾略特很明显地表达过:如果你是一个对世界漠不关心的诗人,你写出来的批评也只能是漠不关心的批评。艾略特绝对不是一个对现实漠不关心的诗人,他对现实是有关切的,他的作品都是他走向大众的一种形式。他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看似与当时的英格兰现实没有关联,但其中也有对现实的折射,二战期间他的诗剧被各种剧团到处巡回演出。在这本传记中,我读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如何在世间行走,如何与现实发生关联,我对这点印象很深。
简短地说一下另外两点,我也在译后记里面写到了。这本书帮助我们理解了艾略特的宗教情结,从他年轻时一直存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戈登一直用一个词叫“寂静”。表面上戈登把他的皈依写成突然的事件,但实际上,戈登写出了他内心中的自然连续性,比如他年轻时有禁欲情结,向往圣徒生活。但是戈登写了一句话: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罪,尚且不需要宗教。所以在皈依那章,戈登从艾略特的婚姻开始写,因为皈依使他对在婚姻中犯的罪有了反思。戈登写到了艾略特的皈依与他生活中其他行为之间的联系,把它们写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点我是非常佩服的。另外让我感受很深的是书中对他晚年的描写,写艾略特晚年离群索居的孤独,我觉得是这本传记最成功的地方。因为艾略特的晚年在各种传记中相当于空白,大部分传记事实只能从档案馆里搜集。戈登只能靠各种材料的拼接以及对艾略特心灵的理解,写他功成名就后如何用孤独来保护自己的诗。这是我很佩服的一点。
张新颖:我看这本书的第一个印象是,翻译得太好了。翻译的不足足以扼杀我们的阅读兴趣,哪怕是一本很好的书,而这本书翻译得这么好。单看中文呈现出来的版本,都能感受到这本书很难译,因为要面对很复杂的问题。中文译本的读者其实是有福的。从头到尾我都觉得挺好,所以我就不挑其中某段了。第二,《不完美的一生》这个书名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完美的力量。书从头到尾就是在完美和不完美的张力中推进,所以书名很好,但要读了以后才能知道这个书名的好处。
主持人:许小凡在后记里就说,艾略特比谁都渴望完美,但是他应该没有达到。在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他说他自己没有达到,但是他把这个“完美”交给后世的我们,也许我们可能享有这个完美的人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几位,对于材料,传记应该怎么做取舍?要不要讲那些完全发生在内心的故事?
张新颖: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面对不一样的传主,写作方法就不一样。写艾略特和写穆旦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写作者不一样,所以会面对不同的条件。我觉得不存在一个模板式的传记的写法,只能根据写传的人和传主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写法。这个回答听上去很平庸,但确实是实话。关于写传的人和他拥有的材料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不同的木料适合做不同的家具。木料不够,只能做小板凳,反过来,做大柜子的木料来做小板凳,那是浪费。要对得起那种材料,要做到合适。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好的木匠。有一堆垃圾,所有木匠都认为是废料,但是偏偏有一个木匠觉得这些东西不但有用,而且比好木料还要好,用这些做出了更好的东西。很多伟大的传记用的材料在一般的作家眼里就是没用的材料,但是好的传记作家能够焕发出它们的能量。
许小凡:作为译者,我自己也没有写过传记。但是我有两个跟传记写作有关的问题,是我在读沈从文传记时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看到张老师写的传记里大量地引用了《从文自传》,这些材料不知道您会不会做一些筛选?还有一个问题是,传记与传记小说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张定浩:相信对于张新颖老师,把沈从文那本书叫作传记,他是勉为其难的,这是一部作品。从作品角度讲,真正的客观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接近。你要理解一首诗,你要写一首新的诗,你要理解一个杰出的人,你就要努力去让自己成为杰出的人。如果做不到自己写出一部杰出的作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去努力理解。比如谈论苏东坡时,好像怎么谈论都可以,但是这样的态度就无法对自身有益。因为你面对一个比你更杰出的人,首先要做到准确地接近他。传记也是这样,你要做到准确地接近他,并不是要还原他,那是件虚妄的事情,你只是为了在准确地接近他之后,让自己呈现出更好的面貌,通过自己面貌的好映照出他的好,其实是通过自身映照他,你自己成为镜子一般的东西,这种时候就体现出了精髓。第二,艾略特有一篇谈论丁尼生的文章。丁尼生对社会政治宗教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在对语音的感觉上,别人难以企及他。声音的感觉是在表面,只有真正进入表面,才能深入内部。这本传记也是,作者没有偏见地面对艾略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进入他的内部。艾略特谈论丁尼生时,说到要进入这种内部,进入深渊般的悲伤里面去。艾略特觉得最好的批评是让你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但不是去解释,而是让你看到之后,自己在那个地方独自待着,让你自己去面对他。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前面一定要用到《从文自传》的材料,因为《从文自传》这本书太有名了。要引用是因为沈从文本身已经写了,再重复没有什么意思。《从文自传》只写到20岁,20岁以后要我来写。《从文自传》是他30岁时写了他20岁的事情,30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所以他在叙述他20岁以前的生活时,那意气风发的状态会被带到他对以前生活的回忆中。所以他写的以前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是整个基调非常明朗,甚至是欢快的,而他真实的生活可能不是这样。他为了突出从边缘地区来的野孩子的形象,他写自己“逃学来读社会这本大书”,但是沈从文小时候读书读得很好,他为什么逃学?因为他上学之前已经把很多东西都学会了,上学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学校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智力需求,他有意地把这一面去掉了。没读过什么书,整天在野地里玩,这是他的自传建构出来的形象。我只能借助不太多的资料,把他有意忽略的那部分补上,试着把明朗的调子换成也许不那么明朗的时刻。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时,大量地引用了他书信的内容。有人问,你怎么敢这样用?我还挺敢这样用的。很少有人能连续地记录自己几十年的精神活动,好在沈从文把这些东西记下来了,他不是记下回忆,而是记下了当时的感受,所以这些材料我就直接拿来用了,当然我可以有我的分析。当你需要相信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勇敢地去相信它,不要犹疑,在一个瞬间果决地献身。这也需要勇气,我有这样的勇气。
主持人:最后想请几位谈一谈,诗人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艾略特一定是对时间领会最深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诗不是在写时间的,像《四个四重奏》开始那段,包括刚才读的那些诗。
张定浩: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的第二部分里有一句话,“老年人应该是探索者”。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像尤利西斯也是,回到故乡重新启航,第二次远航,这种气象特别好。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写的衰老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因为一个年轻人特别缺乏能力,而一个年老的人拥有了很多心智,所以应该是探索者。我有时候也会说,诗人是克服时间的人,类似于张新颖老师说沈从文是一个时间胜利者。我觉得他克服了历史时间,所有艺术家包括诗人面对的是复活,这也是诗人传记难以表达的东西,简单的生平八卦无法呈现复活的时刻。所谓永恒的时刻,好诗人就是能把时间挽回,把已经失去的东西召唤回来。因为他的存在,所有东西都依旧存在。似乎这也是古希腊哲人的话:爱让所有元素聚集在一起,恨让所有东西分离。对于好诗人来说,他使用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因为爱的能力让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最真实的东西重新聚集在一起。过去的空间和时间里他觉得最珍贵的东西,因为他的爱重新聚集在一起,而这种东西不是知识能带给我们的。比方说艾略特最喜欢的但丁,但丁是一个导师,是比他更为渊博和宽阔的人。但丁可以带他经历现实,但如果要抵达一个更为崇高的层面,导师是没有能力做到的,必须把他交付给一个爱的力量,让他继续向上攀登。可能某一刻这样的人并不存在,但不能说因为这个人没出现就不能写出好作品,其实是反过来的:你自己拥有了爱的力量,杰出的人才会出现,或是出现在你的作品当中。
张新颖:把时间的问题变成空间的问题,我们可以讲讲中国人读艾略特的历史。我们这几年翻译了奥登,我前些年在芝加哥教书的时候,因为要讲到穆旦,就让学生去读奥登,可是奥登在美国没人读。一样东西换了空间之后,换了环境之后,它起的作用确实不一样。我们从20年代开始读艾略特,他对于我们的作用确实不像他在英语世界里的作用,卞之琳个人的经历就能说明这一切。卞之琳当时是北大学生,有一门课叫英语诗歌,老师是徐志摩,讲浪漫主义的东西,讲得天花乱坠,学生也很高兴。这门课上到一半,徐志摩的飞机出事了,换了一个老师,同样一门课完全变样,变成了叶公超讲艾略特。对于学生来讲,这个转变非常大,所以很多年以后卞之琳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对于中国新诗来说,从30年代到40年代的转变起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卞之琳说了一句话,当然这句话其实包含骄傲的成分:经得起检验的,今天还能够读的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就是现代主义。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卞之琳做学生的时候译了一本,到了40年代,穆旦他们的时代,和卞之琳做学生的时期又不一样了。穆旦整天读艾略特的杂志《标准》,那就更不一样了。到了今天,我给研究生上课,每年会让他们读一本艾略特,我会挑选艾略特的书中最容易读的《批评批评家》让他们读,比较薄,很多都是演讲,不是那么难读。文学作品似乎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在另外一个时空中获得生命,就是张定浩说的复活,艾略特可能没有想到他在中文语境里会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