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原野》:一百年前墨西哥革命的文学分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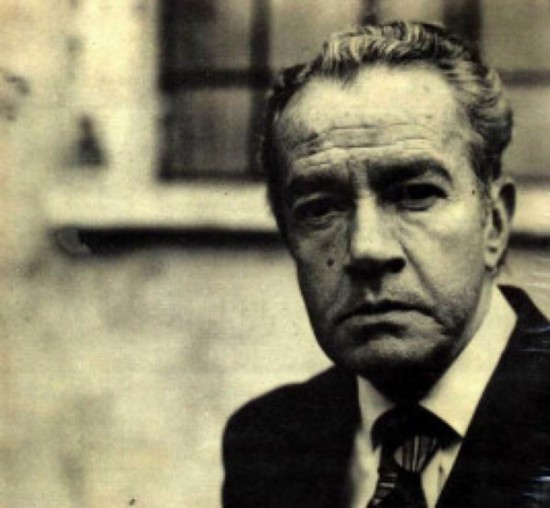
胡安·鲁尔福(1917.5.16-198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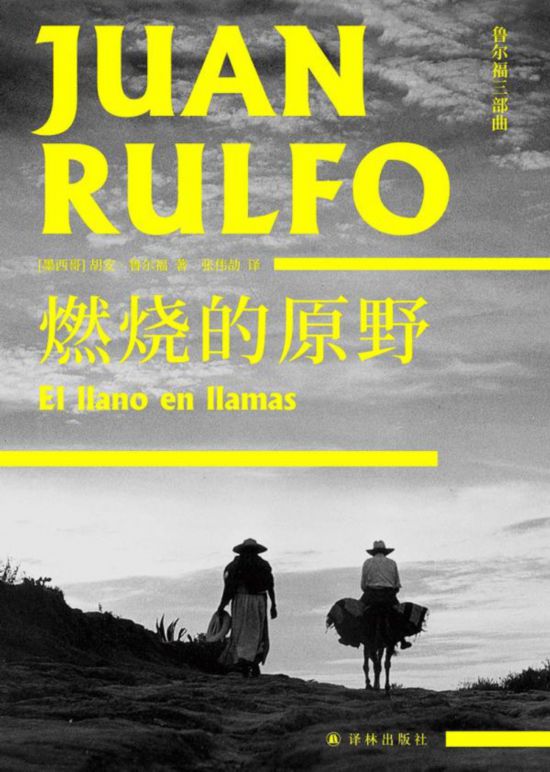
《燃烧的原野》,[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著,张伟劼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204页,48.00元
2020年初,游历墨西哥的我乘坐从瓜纳华托到哈利斯科州的长途汽车,迎面而来的,是受水土侵蚀而成锯齿状的山脉和季节性干涸的河谷,土地袒露,野草稀疏,一支扣着草帽的马队哒哒行进,扬起发白尘土。
一年后,鲁尔福短篇集将我重又带回那片灼热的原野,这一次在文学世界里去往道路更深处的内陆腹地,看一百年前的村庄如何灰飞烟灭,毁于大火。
走入鲁尔福的世界不能不提到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它以推翻独裁政府为起始,历经十年派系混战,建立共和国为结束。鲁尔福于1917年出生,父母双方皆来自哈利斯科富有的地主家庭,但家族产业在内战摧毁殆尽。父亲于1923年被枪杀,母亲死于革命的余波——1927年的基督战争时期。父母双亡的鲁尔福由奶奶和亲戚抚养长大。
这场对鲁尔福一生起了重大作用的墨西哥革命,影响还将延绵几代人。它一方面代表了土地平等的正义诉求,如壁画运动所展现的那样,同时也以百万流血伤亡造成民族创伤。当新政府施展一系列大计方针,从土地、教育到宗教,急于将墨西哥一步推入现代文明社会,墨西哥被击败的传统的乡土的那部分以强大的惯性裹足不前,与进步的愿景再度撕裂。
鲁尔福笔下的乡村便是墨西哥的后一种分身。承受了内战的巨大破坏后,农民的境遇并没有因土地改革而变好。《我们分到了地》里,“我们”名义上分到了整个平原的大片土地,却是滴水不沾的不毛之地,硬得像牛皮,烫得像饼铛。对此,负责分地的官员漠不关心。《科马德雷斯坡》中,土地虽然平分给了农户,实质却被豪强的托里柯兄弟控制。敢怒不敢言的乡亲们默默抛弃了耕地,一个个远走他乡。
穷山恶水没有法律,尊奉的还是暴力至上的丛林法则。托里柯杀人抢劫,为霸一方,却被邻村更加强大的恶霸打死。暴力一旦开启,便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那个人》便是这样的冤冤相报。一个“男人”在山上不停赶路,一个“追赶人”在他身后紧紧相随。追赶人等待男人力尽疲乏走入死路,好对他后脑勺放上一枪,因为那男人深夜杀了自己全家。而男人之所以那天摸黑进了追赶人的家,也是为向追赶人报杀(兄)弟之仇。哪怕男人此刻非常后悔,他已没有了回头的路。追与被追,如一条圆环赛道,身份随时可能互换。故事的后一部分,发现了男人尸体的牧羊人被抓审问,主审的法律人员则是完全隐身的。正义不仅迟到,还会永远缺席,甚至本来无辜的牧羊人也卷入漩涡。正如《科马德雷斯坡》勤恳的叙述人最后手上也沾染鲜血。
暴力循环是鲁尔福作品一个不断复现的主题。《求他们别杀我!》中,最开始矛盾是土地不均,堂佩卢老爷家牧草青青,胡文西奥的牲畜濒临饿死。胡文西奥偷偷打开护栏放牲畜去吃堂佩卢的牧草,引得堂佩卢勃然大怒,威胁要杀了那些牲口,反被胡文西奥杀死。原本的财产矛盾迅速升级为血仇。堂佩卢的老婆悲伤过度去世,两个孩子成为孤儿,加重了悲剧。胡文西奥贿赂法官最终也失去了牲畜,此后他像染了瘟疫的人一辈子躲藏。暴力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让所有人的境遇变得更糟。胡文西奥在几十年折磨中偿还了自己的罪,但这并不是终结。堂佩卢的儿子长大成为上校,最终取走他性命。
“明知自己赖以生存的东西已经死掉了,还要成长,这的确很难。”(张伟劼译,译林2021版,下同)未露面的上校在竹墙后面说道,半是对胡文西奥,半是自白。他怨恨父亲的缺位,以恨意滋养求生意志。这份意志必须依附一个更为坚固的实体,于是他将仇恨转嫁到胡文西奥身上。哪怕此时胡文西奥已衰朽不堪,报仇也必须像使命一样完成。故事的最后,胡文西奥的儿子将他的尸体放到驴背上驮回了家,那满是枪眼的画面继续传递给孙儿,传给下一代。
由此我们看到鲁尔福作品中,与循环暴力伴生的另一主题——代际对立。外来西方文化与本土土著文化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强制和征服性的,“他不仅把她给驯服了,还从那道口子钻进她的身体,钻到很深的地方,让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出来”。从殖民时期,到独立战争,再到墨西哥革命,每一阶段的混乱还未平息,便粗暴地被下一个时代的来临覆盖。承上启下的平稳接替并不存在,新的时代弑父而生,一出生便无依无靠。国家命运换位到个人身上,要么父亲已死,成为暴力的借口,如中篇《佩德罗·巴拉莫》中父亲卢卡斯在婚礼中被枪杀,佩德罗·巴拉莫便誓言杀死婚礼所有人报仇。要么父亲形象是暴戾的,胡安·普雷西亚多之所以来到科马拉千里寻父,便是因了母亲临终的嘱托,“他该给我的东西就从来没给过我……孩子,他早把我们给忘了”(屠孟超译,译林2021版)。佩德罗·巴拉莫抛妻弃子,本身即是一位失职的父亲。
非但儿子记恨父亲,父亲也怨恨儿子。《北渡口》中,父亲会制作炮仗,只要镇上仪式庆典不绝就不愁挨饿。但对儿子他坚决不传手艺,防得像贼。儿子贩鸡卖猪的生意不济,向父亲托付妻女,借款去美国闯荡,父亲转手就将儿子的房子卖了抵债,使他从边境回来人财两空。镜像的对话出现在《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意欲向北逃难的养父向养子索要财产反被打死。《玛蒂尔德·阿尔坎赫尔的遗产》里,阿尔坎赫尔被马撞死,老欧雷米奥便与还是襁褓中的小欧雷米奥结仇。他恨儿子的啼哭惊吓了马匹,他恨妻子摔倒时为保护儿子宁愿牺牲自己。他神神叨叨说,“错全在这孩子身上……他对我什么用也没有。她要是还活着,准能给我生更多的小孩儿”。
这些俄狄浦斯式对抗是双向的。父亲戒备儿子学会手艺夺走自己的生存权,或是嫉妒儿子分走了对妻子的绝对占有。犹如敦煌变文里的《未生怨》,儿子与父亲成为敌手,对立关系在出世之前便已决定,他只是被动接受了这种命运,就像胡安·普雷西亚突然被告知自己要去寻找父亲。当他像古典英雄踏上自己的征程,追寻注定是徒劳的——父亲已于多年前去世。同样阿尔坎赫尔的死使父与子在对其的竞争中都失败了。没有赢家,拮抗和挫败即是故事本身。鲁尔福对父子关系的处理融合了古希腊悲剧与弗洛伊德的现代分析,再融入本土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鲁尔福的作品不足三百页,却呈现出索福克勒斯般经久的生命力,便有这层道理。
藉由另一篇父子题材,深受君特·格拉斯喜爱的《你听不到狗叫》,我们再来分析鲁尔福的语言风格。该篇几乎由二人对话组成,除了一些简短场景动作提示,如萨缪尔·贝克特的舞台剧。从对话我们得知,杀人越货的浪荡子伊格纳西奥被父亲憎恨诅咒。但当他伤重垂危,父亲虽然骂骂咧咧,还是背起他沉重的身躯去托那亚求医。儿子被父亲扛在身上,被月光投出加长的黑影,两人如连体的怪物,走在寻求救赎的旅程上。视觉风格强烈,同时象征意味浓烈(另一篇《塔尔葩》也是抽象了的治病朝圣之旅)。故事开头父亲问儿子有没有听见声音,儿子只零星回答一两句,看不见,难受。当他们到达村子,力竭的父亲靠着栅栏把儿子松松垮垮地放下来,才因为儿子手指松开终于听到了狗叫,与开篇相应。苏珊·桑塔格曾援引鲁尔福的话说他写作中充满寂静。他没有使用诸如“夜里的村子静得可怕”这类外在描述,有什么能比当手指松开突然四面响起狗叫更能表达村落之前的寂静呢?
之前提到要理解鲁尔福必须将作品放入时代背景,而要赏析鲁尔福,写在纸上的内容和没写的同样重要。第一是因为鲁尔福创作短篇小说的高度自觉。他曾在访谈中提到《佩德罗·巴拉莫》之所以能精简到现在的篇幅,是短篇小说训练了他的凝练。短篇小说的体裁要求在较短篇幅内呈现一个有完整发展脉络的故事,类似剧本的一幕。对银幕时间精打细算的电影编剧知道,精简剧本的一个技巧是把场景开头和结尾几行台词删掉,如昆汀·塔伦蒂诺常做的那样。观众并不需要知道完整的头尾,当他们被扔进场景中段,自然会根据内容弄懂状况。鲁尔福不仅提前运用了现代编剧的技巧,对自己作品的精练更加严苛。《你听不到狗叫》一开篇你便已置身故事的核心,父子俩已经在路上了,就像开头可能存在的数段铺垫——为什么受伤,为什么不能在本村治疗——已被砍去那样。当你读完又会发现,这个故事只有核心。村子到了,听到狗叫,就结束了。除了场景的剪裁,内容披露同样俭省。《科马德雷斯坡》中,“托里柯兄弟不管吃什么东西都要加石盐,但吃我的玉米的时候是不加盐的”,表面说玉米的吃法,实则透露的是,村里唯一与托里柯兄弟交好的“我”的劳动成果也会被他们霸占。鲁尔福的作品短,但你无法一目十行扫完,需要不断主动补充被省略的细节,甚至关键信息。“炮仗每响一声,在我扔掉雷米希奥尸体的那个地方就会飞起一大群兀鹫。”当你从如此精简的一句话里展开一群秃鹫啃食托里柯的尸体,随着远处邻村烟花的燃放而不时惊吓起飞的完整画面,又会得到莫大脑力互动的享受。
第二则是鲁尔福有意识地在作品里隐去作者的声音。《佩德罗·巴拉莫》没有一位全知全能的作者,情节来自十来个角色碎片对话。角色之口也占据了短篇的主体。大体由对话组成的有《卢维纳》等。完全对话组成的二篇。第二人称一篇。第一人称八篇。明显外在叙述者的第三人称仅两篇,《清晨》和《那个夜晚,他掉队了》,各自也有一半对话成分。这些故事呈现的乡土,有愚昧,有残暴,也有道德沦丧和荒唐可笑。鲁尔福不对它们作价值判断。佩雷达那样充沛使用形容词也为他所不喜。它们不会自文盲口中说出。对话与叙述的一致要求叙述也必然采取说话人平实的语汇。鲁尔福的功力也确实能做到,仅通过自然环境和叙述人第一晚的见闻,便能实现阴森的氛围营造,让一个堪比科马拉的偏远鬼镇卢维纳跃然纸上。
去做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与鲁尔福天性相违。他对自己的声音太克制了。如果不看生平,很难想象《求他们别杀我!》那个因为牧草争端被杀死的堂佩卢老爷的原型,竟是鲁尔福自己的父亲。上校一句喃喃自白,已是他允许自己心声的最大流露。小时候的鲁尔福曾亲眼见到基督战争中死去的人被吊在树上。残酷童年记忆落到故事,“他们给吊在马场中央的一棵牧豆树上,晃来晃去。从篝火堆上升起的烟模糊了他们失去神采的眼睛,熏黑了他们的脸,而他们对此好像并无知觉”。暴力本身即令人惊骇,平静反而是最好的语气。
鲁尔福笔调平静到了抽离的地步。精英领导的墨西哥革命号称代表农民抢夺地主的土地,鲁尔福并未因为自己是被革命一方的地主之子的出身站边。同名故事《燃烧的原野》里,起义军与旧联邦军同样残暴。全书最接近地狱的图景,玉米待收时节被点火焚烧,风吹火焰点燃整个平原。放火享受这“壮丽”景象的就是起义军。革命结束起义军成为新的政府,与教会之间爆发基督战争。说革命是代表人民意愿的官方叙事很难将这不得人心的内部分裂容纳入内。这种失谐反映到文学上,无论是作为政府职员的鲁尔福,还是上过天主教孤儿院和两年神学院的鲁尔福,都没有因个人处境选择立场。《那个夜晚,他掉队了》里,要是让基督兵漏网,政府兵准备随便射杀一个平民充数。《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里基督兵用卡宾枪顶着卢卡斯的背逼他承认没犯过的罪。两边谁都可以成为更恶的一方。末尾两个诙谐讽刺故事平分给了民间神棍和饭桶州长。
鲁尔福在写作中是沉默的,因为他把话语交给了角色,尤其是广大农民。机关供职时鲁尔福便常游览群山,担任轮胎公司旅行推销员和汽车杂志编辑的职务之便给他更多自由周游全国。这些经历为他摄影的爱好提供了素材,一方面使他对山川地理尤其是哈利斯科州本乡有了深入不毛的熟悉,比如《燃烧的原野》的战场阿尔梅里亚河。旅行带来更重要的经历是,鲁尔福可以去到乡村,倾听那些不会读书写字,沉默大多数的农民的声音。他从他们身上,得知了第一手最真实的乡土,扩充了比个体见闻更为丰富的经历。鲁尔福寡言少语,但他喜欢倾听。他听着老乡们的故事,留意词汇和语气,包括给翻译家带来些微麻烦的方言,还带着十六世纪卡斯蒂利亚语的印迹。这些对当时墨西哥城市居民也十分陌生的语言,被鲁尔福艺术性地保存下来,创造,转写,更是还原。
还原不等于保持原材料的粗粝。鲁尔福对字句的加工是极谨慎的,比如书名原文的El Llano en llamas,原野的llano和火焰的llama押着头韵。每次重版富尔福都会对个别字词再调整,比如1980年版起,Llano转为大写,特指哈利斯科州南部的大平原。人物的名字系悉心挑选,比如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由基督战争中两位死对头名字各取一半组成,加重讽刺。《那个人》里男人和追赶人则因角色可能动态互换故意模糊姓名。小说语言做到平白如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用词精确,无一词突兀或脱离角色,除非他在模仿州长刻意滑稽。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到,若是把《佩德罗·巴拉莫》的时间线改换一种方式,便会凌乱不堪。《科马德雷斯坡》也是类似,时间线在荒村的现在与村霸的过去之间跳跃,当你试图变更则会发现每一段都已被固定在它应有的位置。甚至托里柯兄弟与我交好,和托里柯是我杀的,这样强转折所留的间隔也恰到分寸。鲁尔福的短篇里你不会感觉有任何东西是随意放在那里的。
鲁尔福写最乡土的故事,但他的手法是现代的,他写的是毫无疑义的现代小说。他的文学养料,不是十九世纪西班牙传统文学,而是墨西哥本国历史,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还有美国的当代文学。一些先锋性技巧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碎片化叙事、时间视角无标记地突然转换被鲁尔福采纳并娴熟运用。鲁尔福因战争中断学业,不喜的人攻击他没有受过完整大学教育,喜欢的人赞叹他是天赋型选手。双方都不应忽视的是,鲁尔福不仅上过人间这所大学,还从广博的阅读中完成了自我教育。作家朋友说,鲁尔福几乎阅读了当时所有翻译到西班牙语的文学。受世界文学启蒙的鲁尔福,原创性地将本土文化与现代技法融合,启发了马尔克斯等后辈,作为先导者以爆炸的拉丁美洲文学回馈了世界。短篇集《燃烧的原野》在西语文学界的影响力,大概仅次于博尔赫斯的《虚构集》。博尔赫斯本人是这样评价鲁尔福的:他的小说是西班牙语文学中最好的之一,甚至可以说任何语言里。最优秀的文学超越语言。广受大师激赏的鲁尔福作品中译再版,来到中国读者面前,实为我等之幸,可堪重读和品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