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批评、阅读和阐释 ——与洪子诚先生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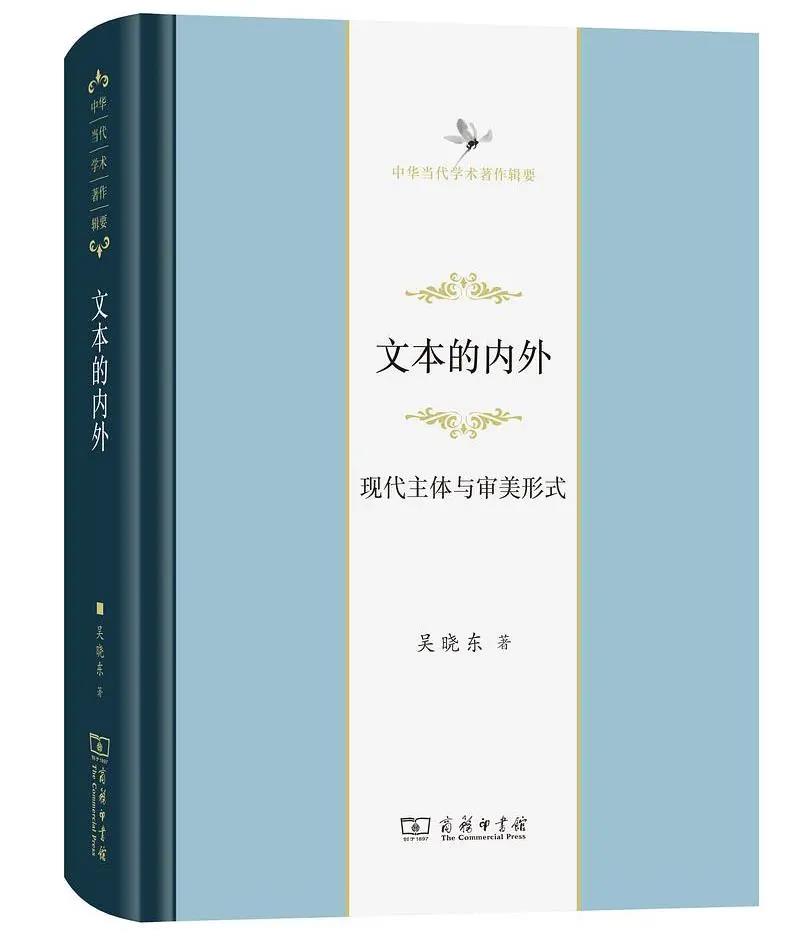
洪子诚:文学教育中,很重要的是作品的阅读、阐释。但现在是否有过分重视理论,以阐释理论作为挑选作品的这种倾向?另外,前些年我们都参加过“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研讨会,这是为了突破文本分析的封闭性,而放置到更广阔社会、大众空间的努力。好些年过去了,这种承担的效果你觉得怎样?你好像并不太理会这一诉求?或者说,你考虑的,更多是从文学、诗学的角度上来发掘这种参与的可能,如你选择北岛、王家新那样?
吴晓东:过分重视理论,以阐释理论作为挑选作品的标准的这种倾向在我的一些研究中也有所体现。我现在开始警惕这种理论先行的研究。但我对理论依然有无法舍弃的情结,总似乎觉得理论会增加文本阐释和分析的某种深度。也经常有学生问我关于理论的作用以及如何运用理论的问题。理论可以是一个视角,一道光束,照亮对象和客体;可以是我们思考的中介,就像过渡,过了河后,可以舍筏登岸,直达客体的秘密。理论就是过渡的船和中介。我很欣赏李欧梵与罗岗的对话中李欧梵先生的说法:“理论应该像灯光一样照射进来,一照,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当然,如果不作具体研究,只亮几盏理论灯光,恐怕照来照去还是这几个样子。”换句话说,理论还应该具体落实到细节研究。我还想补充的是,你所借用理论的灯光可能非常亮,但是你自己借助于理论灯光到底能发现什么,毕竟取决于你自己的眼光和主体意识。有些人发现的只是他想看到的东西。
理论运用得恰到好处的话,也有助于突破文本分析的封闭性,如您所说把文本“放置到更广阔社会、大众空间”。我其实在这些年的小说解读中有意识地尝试这种“突破文本分析的封闭性”的拓展工作,虽然做得可能不够好。比如对王家新的分析,就关注他与俄罗斯精神传统的关联性以及他的近期诗歌表现出的重建生活伦理学的征象。
洪子诚:在一篇文章里,你谈到读鲁迅散文《腊叶》的感受,说它透露了罗兰·巴尔特式“世态沧桑”感。你说,鲁迅将一片病叶夹在书中是在“暂得保存”一种“病”的意义,而在挽留这个“意义”的同时,他也发现“意义”如同旧时的颜色一般销蚀。你说,这是“意义”无法挽回的本质,最终祛除“病”的附加语义,而还原了生命形态的本真性。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就没有鲁迅的这篇感人文章,同时也没有你面对鲁迅“世态沧桑”感的“感怀不已”。这些且放在一边,如果发挥地说,在阅读、作品分析的问题上,我的问题是,在解读中,我们的注意力,重心是在“复原”文本的“原初”情境,还是立足于阅读者的、不被那些具体情境支配的立场?
吴晓东:也许不同的研究者对一部文本的不同解读方式,恰像从不同的角度照到文本上的光亮。有时光亮太弱,就无法照亮文本,有时光亮太强,就会遮蔽文本,有时角度太偏,也无法切中文本的主体与中心。重要的是洞幽烛微,为读者揭示文本的真正有待发掘的秘密。有些作家的确创作出了需要阐释的复杂文本,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就是需要阐释和解读的范例,因为作者刻意设置了阅读障碍或者隐藏了深层结构,所以就需要去“复原”文本的“原初”情境。当然研究者真正理想的状态,也是像一个普通读者那样,“立足于阅读者的、不被那些具体情境支配的立场”。不过想坚持这种立场,在具体的文本阅读实践中,不是始终行得通的。因为读者阅读严肃作品的时候,通常面对的不是那种清澈见底的透明文本,有时就需要专业研究者对文本的“原初”情境加以“复原”。
有时作品内涵的“意义”可能是连作者也不自觉的,我分析鲁迅的《腊叶》想揭示的就是“病叶”上潜藏着鲁迅也许不自觉的某种心理结构,我把它视为“病”的意义,最终“意义”却如同旧时的颜色一般销蚀。但我承认阅读这篇《腊叶》完全可以不顾我的关于“意义”的分析而直接被鲁迅疼惜病叶的心境打动。
洪子诚:在批评和文本阐释中,批评家往往强调要立足于艺术,不要以意识形态分析作为根基。昆德拉在文章中讲到对索尔仁尼琴的看法,说:“这位伟人是伟大的小说家吗?我怎么知道?……他那引起巨大回响的坚定立场(我为他的勇气鼓掌)让我相信,我已经预先认识了他所说的一切。”你同意这个看法吗?如果挪到奥威尔的《1984》来,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评价?
吴晓东:我最近又重读了一遍奥威尔的《1984》,这部小说令我产生前所未有的震惊体验。我惊异于奥威尔在写作这本书的1948年对未来极权主义的想象化情境的设计。这部小说虽然也是十足的意识形态性的,但是小说中想象出的关于未来的一个个具体的情境却着实惊人,有着令人惊诧的情境意义上的真实性。这也保证了《1984》的小说性以及您说的艺术性。我完全赞同您的判断,即使对一部作品进行意识形态分析,也要以这种艺术的水准以及真实性为根基。但昆德拉仅仅根据索尔仁尼琴的“坚定立场”就判断“已经预先认识了他所说的一切”,而且在《相遇》中说“我从来不曾打开任何一本他的著作”,就有点先入之见了。“坚定立场”不一定妨碍索尔仁尼琴的艺术性,如果精神性的维度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精神性会增益作品的艺术性。
洪子诚:文本解读、分析的目标之一,好像就是要将含混的、暧昧不明的东西清晰化。提供明晰答案,似乎是不少分析所立定的标的。但是,就你所特别重视的文学的自觉、感性等特征而言,就像有的人说的,“在创造性的激情、原始的直觉和思想的客观成果之间永远存在着悲剧性的不协调”;“思想必须说出来,人应当完全这个行为。但是下面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始终是正确的:‘说出的思想是谎言。’”(别尔嘉科夫《思想自传》)——这不仅指写作,也可以引申到阅读上来。你在这方面持慎重态度。你体验到这样的困境吗?如何处理?你觉得有时也应该保留某种含混、某种不确定的空间?
吴晓东:前些天读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书中有一节的小标题很吸引人,叫“文学的陌生性”。米勒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它们互相之间都是没有可比性的。“每个都是特别的、自成一类的、陌生的、个体的、异质的。”“强调文学的陌生性,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很多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功能(更不要说报刊文评了),就是遮盖这种陌生性。……文学研究隐藏了文学语言的独特性,试图去解释它,使它自然化、中性化,把它变成熟悉之物。……无论如何,这些文学研究都有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平息人们对文学真正陌生性的自觉不自觉的恐惧。每一作品都没有可比性,这令我们生畏。”从陌生性的角度说,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干的是南辕北辙的事情,是使文学去陌生化,或者说是祛魅的活动。
米勒把“文学的陌生性”上升到文学的基本特征的高度来论说,“陌生性”成了界定文学本体论的重要因素,这与您引用的别尔嘉科夫的话有暗合之处。在这个意义上说,追求某种非确定性把握和判断,应该是文学研究者职业伦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而这种职业伦理,我其实主要是当年从您的课上和著作中最早体悟到的。
洪子诚:前面说过,那种细密的、有明确理论支持的“科学性”分析,目前成为潮流,而印象式的感悟批评的地位下降。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如你说的,采用何种方法,与文本的性质有关。针对“现代主义”的诗、小说,传统批评方法并不能揭示其中的奥妙。另一个原因是理论方法本身的发展带来的解读、分析面貌的改变。但是,印象式的、感悟性的批评是否已经过时?我们有时候还很怀念刘西渭对作家作品的那些耐人寻味的点评,觉得有时候比洋洋万言更有意思。况且,如你说的,1980年代那种“非功利”阅读中遭遇的“尖锐的针刺所带来的痛楚”,那种柔软感和痛楚感,很可能消失在这种“科学”分析中。回过头来说,那种敏锐的艺术自觉和感性判断,似乎是一个重要基础。
吴晓东:印象式的、感悟性的批评在文学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刘西渭当年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和判断也屡遭作家本人的反批评,认为不符合作家创作的本意,但是文学的魅力之一就是无法实证性。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必须先在地接纳和涵盖这种文学感悟,才称得上真正“科学”。文学的固有禀赋,如带给心灵的顿悟以及感动与科学性多少是矛盾的。所以“敏锐的艺术自觉和感性判断”,无疑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您的研究给学界的印象。
洪子诚:这样,我好像更喜欢你融入更多个人感受、体验的那些文本分析,如你写读《尺八》的文章。我们有时候其实更重视某一个有见地的读者(批评家)是如何阅读、看待某部作品的,而不完全更重视他提供某种方式和结论。因而,你讲到的竹内好、伊藤虎丸等学者的那种对作家作品的“原体验”,虽然有某种“玄学”的神秘意味,但想想是有某种迷人的风采的。
吴晓东: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有魅力的地方可能就在执着于对本源性、原理性东西的探索。他们不是扼杀文学的神秘性,而是小心翼翼地呵护文学固有的神秘。他们的鲁迅研究中表现的方法论,有一种本质直观的特征。这种“本质直观”就其玄学化来说未见得是好的品质,但对于弥补我们的研究中洞察力和想象力的缺乏,却具有相当珍贵的启示意义。
最后非常感谢老师您对我的并不成熟的文字如此认真的阅读与批评,奖掖后学的呵护之心令我深深感动。您提出的问题中表现出的关于文学以及批评的洞见,远远超过我的研究的承受度,彰显的是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的良知和尺度。
本文节录自《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