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汗青对话育邦:“飞越真理与存在的争辩”

育邦,1976年生。著有诗集《体内的战争》《忆故人》《伐桐》,小说集《再见,甲壳虫》《少年游》,文学随笔集《潜行者》《附庸风雅》《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等,诗歌入选《大学语文》《新华文摘》及《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度文学排行榜(诗歌类)等,曾获金陵文学奖(诗歌奖)、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诗歌奖、中国诗歌网“2019—2020 年度十佳诗人”等,为当代中国70后代表诗人之一。现居南京。
赵汗青:您的诗歌似乎有着两种相对立的气质,正如您一次演讲的主题——《鲜花与尘埃》。读者能感知到的还有“生长与死寂”,“纯净与污浊”,“微笑与鲜血”等;诗作中既有对纯粹的渴望,孩童般强烈的好奇心,又有苍老的,忧郁、哀伤的吟唱,伴随强烈的毁灭感;在无声的黑暗中孕育着一股“爆裂”的力量,形成悖论美。挑选一句诗来概括就是:“微弱的悖论/引导你走向自己”(《薄伽梵说》)。这样的句子在诗集《伐桐》中随处可见:“每一生都有一个死去的童年/我们从那个男孩的死亡中诞生”(《无题》)。“水冢……飘来歌声/蕨类植物展翅飞翔/我们在黑暗中毁琴,断弦”(《与仁波切夜游锦溪》)。“蕉下的蝴蝶,在死亡中受孕”(《云中鸟》)。“料峭春风中/死亡之灯熠熠生辉”(《夜访七曲山大庙》)。读者被引领着进入一个奇异的,充满矛盾和迷思的世界,如《迷楼》一诗所言:“留下了琼花、谜语和一连串非确定性王国”。这个文学的私人花园兼具西方现代主义的荒诞感与东方哲思中朴素辩证的美感。这应该和您阅读偏好、审美趣味有关?
育 邦:是的。我试图在世界的微弱悖论中抵达某种诗歌美学。悖论,不确定性,荒诞,历史循环等等,不过是我们看到的世界的某一个侧面。在各种气息交互的文本中,我们依然围绕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书写。我们的思辨为了一种洞察,一种警醒,为了发出朴素和谐的声调,即便其本质是尖锐的。谈到读书对于写作的影响,这可以写成一本书。简要地说,我认为我的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几位导师的话来表达:
1,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渊明)
2,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
3,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
4,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博尔赫斯)
5,伟大导师的作品是环绕我们升起而又落下的太阳。(维特根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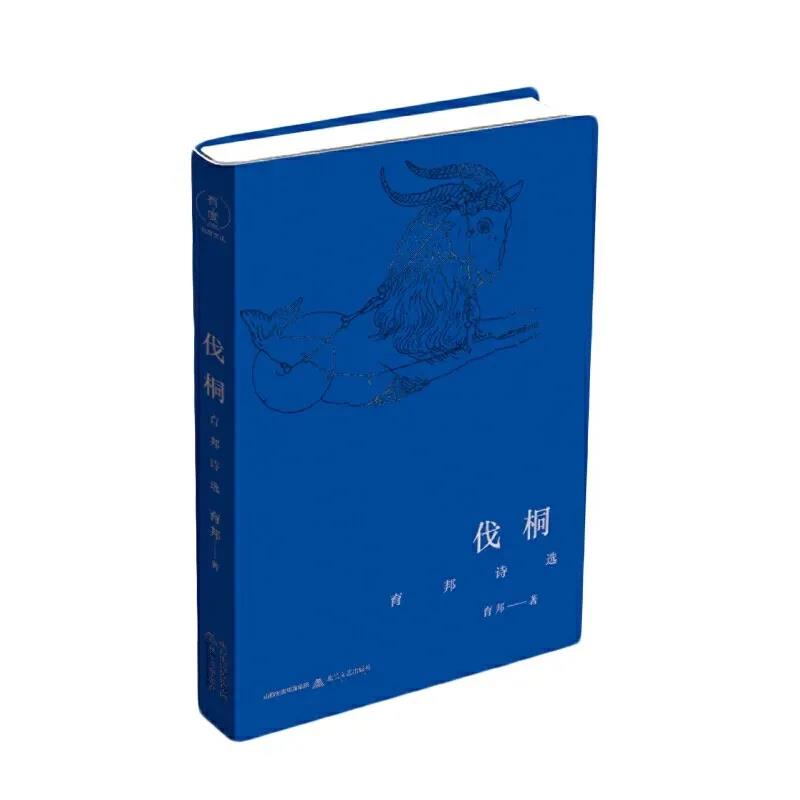
赵汗青:在继承古典性的同时,将诗作赋予强烈的现代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绝非是将古体诗转译成白话那样的简易工程,而是涉及到了新诗创作最核心的秘密。“他若无其事,砍下那棵青桐”(《伐桐》)看似是东方典故,却不尽然。中国传统意象虽十分明晰、鲜活,但象征较为单一,可“伐桐”却有着西方诗歌意象的奇崛性,隐喻与象征的丰富性。您是如何经营此类隐喻和象征的?
育 邦:其实,我没有刻意地去“经营”。它们是自然生发的,富有生命的。但在写作的时候,还是有意识挖掘我们日常生活中、平常世界中可能产生独特“诗歌形象”的意象。古与今,中与外,生活与想象,日常经验和阅读经验……它们之间不再有明确的边界。伐桐,这一意象,你也许以为是从我的脑海里臆想出来的,是想象力催生的结果。但事实是,有一次我去山中游玩,正遇到一帮人在清理一个风景怡人、三面环山的山洼子,而这个平坦的山洼子中间有很多亭亭而立的青桐。他们正在砍伐这些青桐。青桐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梧桐”,就是《诗经》中“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中的那颗树,它站在历史与文化的深处,站在中国人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基因之中。“孤桐北窗外”,它是孤独而高洁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它自身又是散发出淡淡忧伤的“呼愁”。也许读者总能看到更多。诗歌意象的构建,既是作者主动为之的“发现”,也是世界给予写作者的“恩赐”。也可以说,作者的选择与意象的降临,是一个“双向遴选”的过程。
赵汗青:在我看来,您的意象群像是被严格管控和筛选出来的。作品中相对较少出现直观上的现代意象,如“铁路”、“高楼”、“工厂”、“手机”等。您更多使用的是“河流”、“云影”、“蝴蝶”、“湖石”、“慕雪”……同时加了一些限定,使传统意象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开发,使看似古典的意象具备强烈的现代性;诸如“焚毁的星辰”、“迷惘的琴弦”、“暴动的花朵”、“误入尘世的白鹳”等。李商隐对待意象的方式和他那个时代的诗人不太相同,让我们产生了他是个现代人的错觉。当然他的现代性与真正的现代精神又是大不相同的。您怎么看待自己诗歌意象群的构建对自身创作风格的影响?以及诗人的意象群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
育 邦:你说我作品中“意象群像是被严格管控和筛选出来的”,吓得我一身冷汗。因为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管控和筛选”,但是文本呈现不可避免地展示了这种微妙的景观。至于你所说,古典意象的现代性,我觉得是必然的。在某些方面,我们与所有的古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有着相近或相似的洞见与情感,但表达方式上,作为一名当代中国诗人,你自身就携带着中国人与现代性这两种本质属性。你读李商隐,包括更多的伟大诗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卓越品质。诗人的意象群如一滴水,能够成为观照其所在时代的镜像;如一粒尘埃,也包含着时代的混沌和幽暗。一个个意象,也许就是诗人在其时代走过的一个个渡口。进一步说,诗人需从时代的日常情境中跃升出属于他自己同时也属于其时代的“异境”,如我的诗中表述的那样,“我有别于我自己”。
赵汗青:智性与感性的平衡问题一直是个充满争议性的文学话题。诗人有时也被粗暴地划分为艺术家式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式的诗人。您说过自己对知识分子和传统文人的敬仰来自学生时代一位代课老师的影响。《伐桐》正如一座古典与现代交织的迷宫,入口看似敞亮,一不小心却会迷失其中。这恰恰像是您童年时在万花筒中看到的“一个立体的迷幻世界”。在迷宫中读者偶然也会走入里尔克、佩索阿、博尔赫斯、齐奥朗、普鲁斯特、卡尔维诺、乔伊斯等作家的遗迹。在《伐桐》的部分诗篇中,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较为抽象的表述,如“疾病的隐喻”、“时间的暴君”、“道德之轴”、“真理与存在的争辩”等。这类经过了现代思想编码的词汇,有时需要破译才能被大众读者理解,诗人使用起来有一定风险,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育 邦:也许,我们需要某种平衡。正如我在《鲜花与尘埃》主旨演讲中提到的那样:鲜花与尘埃要达成和解与平衡,他们既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是爱与恨的交织,也是生与死的现实存在。但我们试图通过蜿蜒曲折的诗歌小径走向无限广阔的世界之时,智性与感性之间是否需要平衡,古典与现代之间还有分野吗,抽象而危险的剃刀将会危及诗歌的命运吗,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呈现”我们眼中的世界。我们需要“飞越真理与存在的争辩。”这两日,我读到诗人吕德安的一句话:“每一首诗都应该有其形象,能令人联想到生活。”深以为然。为了表达,我们需要攻破汉语中陈词滥调的堡垒,戳破那些无病呻吟、岁月静好的假面。而从修辞上说,我的诗歌正如耿占春老师所言的那样,“在现象与隐喻、感知与象征之间寻求着平衡”。
赵汗青:福楼拜说:“我不过是一条文学蜥蜴。我相信,一名作家,他不应该有过多的欲求,他能够‘取暖度日’就足够了。”您很认可这一说法;也曾写道:“一名作家一旦要进行创作,他是‘弃世而独立’。”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技术上是可以造假,尤其对于年轻诗人而言,这一诱惑巨大。部分作家和世界的关系持续紧张,恰如策兰所言“对抗着人世的/分秒”;另有一些作家也许会与世界达成某种短暂的和解。您作品中既有严酷的对抗性,如同一场“体内的战争”,又有某种超越性;这些诗作背后隐约站着一个超然的迷思者,又或是一个隐逸的反抗者;也许对世界的妥协和超越只是一个作家为了到达所处时代更高的文明程度而向下兼容的过程。可否谈一谈在阅读与写作这个层面上,您和世界的关系经历过哪些阶段?或仍在进行何种修炼?
育 邦:我在2000年左右,写过一个文论叫《对抗之路》。在文中,我写道:“写作者跟现存世界是对立的。他们的对立方式隐匿而沉默,从不惹人注目。……这种对立必将走向对抗。对抗是正常的,没有对抗就没有个人的位置。假如对抗彻底消失,那么艺术也将丢失它应有的位置。对于个人来说,想在对抗消失的情况下从事艺术创作也是不可能的。在对抗中,个人才可能取得位置。”那时我只是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但即便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它没有修正的必要。卡夫卡的道路是对抗之路,他与存在于他身边的世界和秩序一直是抗挣着的,艺术或者说文学写作是他对抗外部荒诞世界的唯一武器,他别无选择。虽然在此期间,他极度渴望实现艺术与现实的统一,甚至他个人与外部世界有过短暂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也是一瞬即逝的,表面和形式上的。加缪写作《西西福斯神话》就是他以无比的勇气面对死亡和荒诞作出的抗争。他对这一行为的巨大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写道:“反抗贯穿着生存的始终,恢复了生存的伟大。对于一个目光开阔的人来说,最美的景象莫过于智力和一种超越他的现实之间的搏斗……”我们就要“在人间”进行摔打、锤炼、锻淬,处处惹尘埃,如巴别尔一样契入生活的深处。而不是隐居在山中,沉溺在书斋中。尘埃就是我们面对的外部世界。既是风花雪月,也是日出月落,是屈辱,也是喜悦,是泪水,更是荒诞,是希冀,亦是绝望……是人世种种的烦恼,是大千世界的存在真相。我们来此世界,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得道高僧,成为一个位列仙班的人。我们生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成为一个人。我觉得只有处处惹尘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作者单位:《雨花》杂志社
文章摘自:《新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