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议”:关于女性报告文学作家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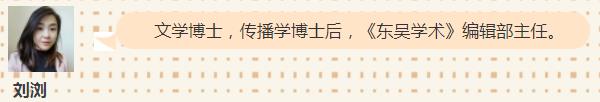
刘浏:在我的观察中,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群体中女性作家的数量是明显少于男性的,与散文、小说等文体相比,这种“男女比例失衡”现象是长期存在的,也是极为明显的。但是,从创作质量上来看,女性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却是极富个人魅力的。她们关注到了许多男性报告文学作家并没有关注到的话题,叙事方式独具风格,语言细腻度也更高等等。我的这一想法,在与《中国作家》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佟鑫交流之后,得到印证。受她的支持与鼓励,我诚邀四位作家和评论家一起参与到这次“圆桌会议”的讨论中。他们分别是资深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者、教授、主编丁晓原先生,资深报告文学作家(女性)长江老师,青年评论家、副主编曾攀先生,以及青年女性报告文学作家杨丰美。我们的“圆桌讨论”,圆桌是虚拟的,但是讨论是丰富的、鲜活的。我们用了电话、微信、邮件等各种交流方式,克服了地理上的讨论困难,实现了云对话的自由与深入。从人员构成上来说,兼顾了性别、专业和年龄,大家平等对话、畅所欲言。期望我们的讨论能为女性报告文学创作的研究提供一些素材,也为女性报告文学创作加油鼓劲。
谈到女性报告文学创作者,长江是绕不开的名字。我在硕士阶段学习新闻学时,就看过长江的电视新闻作品,在深入学习报告文学时,又大量阅读了她的文学作品。有一些问题一直放在心里,借此机会,我一并向长江老师提出了——报告文学是难度很大的写作,对采访要求很高,对作家身体和心理提出很大考验,尤其还是女性作家。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采访困难的?又是如何克服的呢?是什么支撑着您,这么多年始终保持创作热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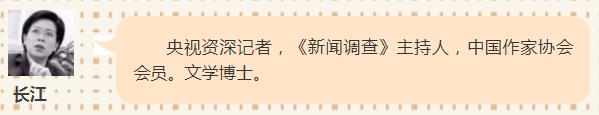
长江:首先非常感谢刘浏邀请我参加这次对话,让我有机会回头审视一下自己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初衷:报告文学之于我,如何形成一种精神高地,吸引着我不断地引颈、攀爬。
在我走上报告文学写作的这条路,我并没有强烈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作者,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有何优势?有何劣势?这一方面跟我的名字有关,1958年我父亲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接到来电,知道我在北京出生,望着滚滚东逝的江水,就给我起了一个“长江”的名字,这名字,气势如虹,势不可挡,让人天生地就不好意思娇羞吴侬似的。而且长大了,我又做了一辈子的记者,职业的关系,走南闯北,必须飒爽。再有我的民族与经历,也无不关涉强硬。
我爷爷是蒙古族,奶奶是旗人。我从小生活在北京,一个传统封闭的家庭。我是蒙满混血,大约我的血液里还残留着驰于草原、挥鞭于辽阔的一路绝尘。
到了“文革”中期,我随父母到了湖北农村的“五•七干校”。父亲养猪,我心疼父母,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光着脚丫子,挑着两个硕大的箩筐,跟着父亲上山去打猪草。曾经一只脚被竹签几乎扎透,哭得地动山摇。那年我9岁。
因此要回答“报告文学是难度很大的写作,对采访要求很高,尤其是女性作家。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采访的困难?又是什么支撑着您这么多年始终保持着创作的热情?”我的回答是我没觉得采访和写作有什么苦,尽管报告文学的灵魂是“真实”,要“7分腿、3分笔”,无论如何,采访与写作都是一份苦差事,但于我而言,看跟什么比较。我总觉得,靠自身能克服的困难,就不叫困难——谁让你想成为一个“写作手”呢?
“文革”后期,我有幸当兵,短暂地获得过一丝时代之宠——小女兵嘛,何况还是文艺兵。但我性格里的倔强、刚烈,使我“不识时务”,致使军旅生涯累遇坎坷。不过也恰恰是因为这一走向社会的“不顺”,我开始“忧愤出诗人”,后来有了写作老师,慢慢地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同时自学外语,考大学,直至今天,整整36年,我先后在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做记者、编辑、主持人,没有一天不是在用自己的选择发声,也没有一天放弃过写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写作就像丁晓原教授所讲的是中国历史呈现于人文舞台上的一幕“大背景”,前所未有,震撼人心。我偏巧赶上了这个时代。“问题报告文学”始终是我的主攻方向。尽管几部获奖的作品《天歌》《山野斯人》《走出古老的寓言》《中方雇员》等等的都是正面的题材,但我依然认为报告文学是一支“敢死队”,我能够成为这支“特种部队”中的一员,内心是骄傲的,情绪是高昂的,这样也一次次地让我忘记了性别。
立足今天,我们再看中国20世纪80年代突然爆火的“报告文学”,它是历史的一座里程碑,是异军突起于传统文学生态最耀眼的样式、一抹新绿,但究其原因,那不过是因为国家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长久被压抑了的信息饥饿、认知饥渴便如久旱的大地,呈现出一段历史上罕见的需求旺盛期,报告文学也恰逢其时地给了人们以精神的食粮,其能成为“文学的宠儿”是有着鲜明的时代“启蒙”特征的。这一点就像如今,文学界已经开始担忧“报告文学”正被边缘化,在凋零,在走向末路,甚至“这种文体有可能会消亡”,这种境况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那也不过是今天,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冲击,人们每天都浸泡在海量的消息里面,而融媒体、自媒体又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观察家、演说家、作家,报告文学再一盆一碗地送上“我看到的”“我写给你们的”,那就不可能收获读者的“如饥似渴”“饥不择食”。
但有生活,报告文学就不会消亡,人们需要有价的信息、需要纯金的真相,同时也需要思考、需要引领。这倒是给当下的报告文学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末路”不一定,但“路”更难走了倒是真。
但“问题报告文学”,说老实话,直到近年,我在实践与思考中,渐渐地在放大着它的外延,这是我想说我的改变。
刘浏曾问:“在您长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特别是选题方面,有什么倾向性?或是说,哪些选题,比较能吸引到您?”
重新再写报告文学以后,我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对“问题报告文学”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这跟咱们今天的“对话”,专谈“女性报告文学”,倒有了一些更紧密的关联。
2020年,圆明园罹劫正好160周年,我从一次讲座中了解到:圆明园是帝国主义给中国人留下来的残酷的“课堂”(周恩来总理1951年讲的),但今天:86处地面遗存因常年风化,很多都已经处在了一种“亟待进行抢救性保护”的地步,令人震惊。另外,消失了129年的“马首”2019年终于回国,但捐献者何鸿燊先生执意要让“马首”既“回国”又“回家”,就是要回到圆明园的母体。
比如遇到了这样“问题”,我还是会“不能放过”。于是我做了《新闻调查——守卫圆明园》,也写了报告文学《“马首”要回家》,强烈呼吁,力陈事实:救救圆明园!你所不知的圆明园!发表在2021年第2期的《中国作家》上。
尽管遇到“问题”我不会绕开,但我的变化在于“目标选题”,过去不觉得重要的一些事情,现在,视野不同了。
比如:1998年我的父亲惨死在一个酒后拉沙子的年轻司机的一脚油门之下。2007年,母亲因为错过透析而使心脏憋炸突然意外去世。这两件事曾经让我愤懑滔天又难过无奈,生命的无常与惨烈,一次次轰炸着我,让我思考什么是“生命”,让我忍不住要去回答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生命”?这样的选题——算“问题”吗?值得我研究、追问、写作吗?
我觉得值。
2019年以后,我连续在《北京文学》发表了《我的生命“谁”做主?》《养老革命》《向肥胖宣战!》,还将续写《别做“小糖人”!》《“猝死”年轻化》《家庭医生》《精神肥胖》《中国的人口往事》……同时我也完成了很多电视专题,其中《你立遗嘱了吗?》我就大胆地走入忌讳,审视和鼓吹起我们国家应该倡导“遗嘱文化”,同时又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学会谢幕》,以介绍“生命预嘱”,把“一旦生命救治无望,你还愿不愿意让人把自己推进ICU?”——推到了读者的面前……
这都是有关“生命”的题材。一直沿着“生命的系列”。我还在前行。
刘浏:丁晓原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长期专注于报告文学研究的学者,在向他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曾就多次关于女性报告文学创作有过交流,在《2020年报告文学:当“轻骑兵”遇上非常年》《2019年报告文学:时间的年轮》等文章中,我们也以对具体文本的评论方式表达过观点。这次,我更期待丁晓原教授能从宏观的层面谈谈他的观察和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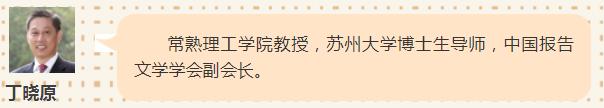
丁晓原:在现在的各种文学门类中,小说无疑是“主角”,但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写作似乎也不再是配角。事实上,它已经是一种全球化的重要写作方式。本来,报告文学就是一个舶来之词,表示着它是一种国际性文体。只是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浸润了许多中国特色,以至于不少写作者和研究者以为报告文学是中国独有的文体。在此语境中,作为一种没有专属指向的普适的书写,无论是哪种性别,都可参与其事。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报告文学被指认为是男性作家的天地,这样就把女性在其中的创造给不同程度地遮蔽了。因此讨论女性报告文学这一话题显然有着它重要的意义。
作家选择何种文体写作,这是基于作者多种因素而决定的。报告文学的写作,既是一种写作方式的选择,即选择以非虚构的(调查采访、亲历亲验等)的写法生成作品,同时从某种程度上又可显示出作者的写作态度、精神立场的取向,即对无谓虚构的放弃,对客观实在中故事及其蕴含的追寻。从这一角度看,女性报告文学的写作,是女性自我现代性的一种表征。从逼仄的自我世界走向漫溢的宏阔生活,从沉浸于私我空间到关注流动的时代现实,体现出的是女性的某种主体性存在的自觉。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由文体附庸变成蔚然时潮,这一时期也正是女报告文学作家集体出场之时,茹志鹃、刘真、黄宗英、柯岩、草明、陈祖芬、李玲修、孟晓云、霍达、何晓鲁、鲁娃、刘茵、谢致红等老中青年作家,她们的创作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四次全国优秀报告文学的评奖中,获奖的女作家有23人次,获奖作品25篇(内含与男作家合作完成的作品5篇),占获奖总数25%强。到了新时代女性报告文学的写作再一次显示出其亦柔也刚的力量,参与写作的作家队伍更为壮大,广东丁燕、黄灯、彭名燕,湖北梅洁、周芳、朱朝敏,重庆李燕燕,陕西杜文娟、浙江方格子,上海薛舒、杨绣丽,江苏唐晓玲、肖静、周淑娟,山东李玉梅、朵拉图,黑龙江张雅文,辽宁孙学丽,新疆毛眉,北京长江、梁鸿、李琭璐,湖南更有余艳、王杏芬、王丽君、杨丰美、何宇红、张雪云、谢慧等一批女报告文学作家。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女性非虚构写作,不说能说在这类书写中占有“半边天”,但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她们的写作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叙事的设置,还是在自我进入书写客体等方面,都有着诸多的特质,许多作者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刘浏:在当今女性报告文学创作者中,杨丰美算是比较年轻的。私下里,她是个阳光且温柔的人,经常能从她的朋友圈看到她可爱的女儿以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当然还有她采访和写作时的记录。她不怕吃苦,是几次当面交流时留给我的印象。现在想想,好像女性报告文学作家都是挺能吃苦的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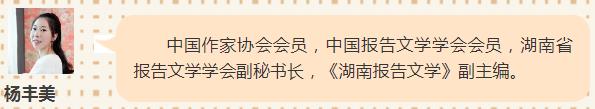
杨丰美: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报告文学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确实会面临一些针对性别的,所谓的优势和劣势。比如,我在写湖南省全局扶贫的作品时,沿着北西南东的逆时针方向,在外头整整跑了近50天没着家,走访了湖南省14个市州的40多个县(市、区)。这个采写的过程是有点难度的,在当时,当我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的时候,别人通常会有两种反应,首先是觉得你一个年轻女作者,要做这么一个事情相当不容易,很愿意给你提供帮助;紧接着呢,怀疑就来了,你一个年轻女作者,能写好这么一个宏大的作品吗?这就是我目前所遇到的最普遍的情况,机遇和怀疑并存。这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平静的。我觉得有机会就是好事,至于怀疑嘛,任何时候都需要用实力去证明。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在写作上对性别、对年龄有所区分的。特别是报告文学这种重在采访调查的纪实性文体,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若是区分太多,我觉得不利于一个作品的成熟表达。我觉得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应是集严谨的逻辑思维、富有特色的文学表达、深刻的思想内涵于一体的。要达到这样的写作水准,定是需要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兼备。我目前还差之甚远,还在不断求索的过程中。不过我在努力让自己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忘记自己是个女人,也忘记自己是个30岁出头的写作者,仅是盯着文学创作本身,尽己所能地克服一切困难去做求真求实的采访调查,又尽己所能地去做恰如其分的文学表达。
我想,天下之所以大,大在有容。我希望自己通过在报告文学这条道路上的漫漫求索,终能成为一个胸怀天下且怜爱众生,包罗万象又返璞归真的时代记录者
刘浏:在这次“圆桌会议”中,曾攀老师是我特别要感谢的人。其实我一直很期待能听听并不是专注于此话题但对文学研究有见解的学者的想法。在当初邀请嘉宾时,因各种理由被数人婉拒过。曾老师雪中送炭,慷慨参与,使我们的讨论更加有趣和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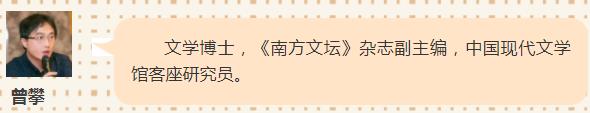
曾攀:关于当代中国的女性报告文学书写,我读得不多,但也有一定了解吧。在我看来,报告文学本无所谓性别之分,但一定在男女间划出一种区隔,那么则需要在写实性的文本里,体现出真正的女性意识,这是不简单的,而且容易造成含混和局限。关键在于话语修辞中的形式技艺和表达姿态,其中不可避免地会裹挟着预设的性征、立场甚至偏见,从而形成独具调性与洞见的女性意识;进一步说,女性报告文学固然立意聚焦当代女性的观念、情感和态度,这就需要建立在深刻理解女性的现实处境、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基础之上,在写实文学的内在肌理中,蕴蓄性别的征兆甚或症状,传达出真切的女性声音,拒绝被篡改与被遮蔽,构筑一种真正的众声喧哗,还原其间的丰富多元;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并不是说女性意识置于文学文本中就只有千篇一律的细腻柔弱、敏感多思,女性也可以时常呈现大江大河般的宏阔,投射深切的底层意识与人文情怀,如是都代表着当代中国的女性报告文学正在走向深远广大。当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医生、企业家、军人作为主体形象在报告文学浮露,传递出了女性意识在时代政治、社会制度与文化结构中的交互,触及当代中国社会较为关切的话题,这无疑需要更为宏大的视野乃至胆识,能够塑成鉴照甚而反思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