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谈新作《革命者》《雨花台》 文学要让党史和革命史“立”起来,“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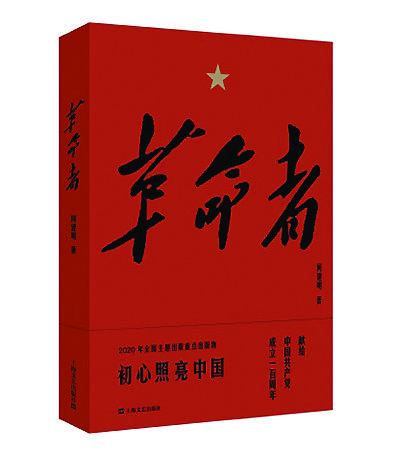

党史不仅仅是已经过去的革命史,党史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创作要和当下社会发展,党的引领下的历史和时代,以及和世界的关系密切关联,呈现新的党的历史,呈现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记者:从十年前出版的《忠诚与背叛》,到去年出版的《革命者》,再到今年四月推出的《雨花台》,这一系列写作是有计划的吗?
何建明:其实没有计划。《忠诚与背叛》2011年出版,当时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写这本书的起因是我在重庆参观红岩纪念馆,发现小说《红岩》里写的和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并不完全一样。特别是看到当时诞生在黑牢里的“狱中八条”,也就是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后凭借记忆整理出同志们在狱中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写成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深受震撼,今天看来,“狱中八条”对党的建设和党员修养等方面仍有非常重要的警鉴意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红岩”的故事里体现出人性和党性的复杂性,并不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要把它真实地呈现出来。
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重点要探讨的是“忠诚”问题,忠诚无价,出卖了忠诚,必然走上歧途。只有绝对忠诚,才能永葆坚定的政治定力,在任何诱惑和考验下站稳脚跟,把正方向,永葆本色。这是文学的启示,也是历史的真实。
记者:那么《革命者》和《雨花台》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海和南京可以说是斗争最复杂和激烈的地方。
何建明:《忠诚与背叛》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我是江苏人,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南京的雨花台,它拥有的红色资源丰富程度,远远超过很多地方,是文学创作的巨大宝库。2014年,我去雨花台采访,第一天到那儿,就准备去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就义的地方,结果半途遇到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他建议我去写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那一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于是我转而去写了《南京大屠杀》。
2014年春天开始,我踏访多地追寻早年共产党人的活动足迹,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是这段追寻的开始,在中国革命历史中,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因其地位特殊、意义重大,牺牲的革命者难以计数,当我看到那些革命者留下的日记、书信等珍贵史料时,常常感动得不能自已。《革命者》就是在这样的情绪推动下写成的。
但是雨花台一直留在我心底。最开始触动我的是丁香烈士的故事,她的经历让我想起了母亲家族一段充满伤痛的往事,在我心里,这位22岁就牺牲在雨花台的年轻女性就像一个远去了的亲人,似乎与我生命中的一分子基因有关。我先把这个故事写成了纪实体散文《雨花台的那片丁香……》,在《人民日报》发表,引发许多关注。2020年初,我全身心投入《雨花台》的创作中,终于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面世,向建党百年献礼。
回头看这几部作品,如果重庆的斗争用“复杂”来形容,而上海和南京的斗争可谓惨烈,如今上海到南京的高铁只要一小时,但在中国共产党刚诞生的1920至1930年代,从上海迈入南京,对于中共党员来说就是跨越生死之门,也正是在这种残酷的考验之下,愈见共产党人敢于牺牲的精神,和他们身上信念的光芒。所以我一直说,上海的革命史是最宝贵的,完全不亚于战场上的革命史。
记者:报告文学写作强调先期的采访和材料的收集,你在追寻早年共产党人的活动足迹的过程中有什么独特的发现吗?
何建明:收集资料、采访这都是作家的基本功,最关键的是我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和感觉。我选择书写的人物不是首先看他的重要性,而是看这个人物身上有没有打动我、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打动我的人和事,也能打动读者。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有多少精彩、动人的故事啊,当你走近这段历史,会发现这是个取之不尽的文学富矿。
2017年走访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我特别注意到了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今年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这两兄弟为大众所熟知,可当时他们只是难以计数的牺牲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和革命者中的一分子。但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动,这是两个多么优秀的青年,一年内先后为革命捐躯,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革命者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精神。
《雨花台》里写到一个被捕的少年,敌人问:才十七八岁,不后悔吗?他昂首挺胸地回答:杀一千次都不后悔!可转头,他对狱友说:现在死了有点可惜,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呢!写《忠诚与背叛》的时候,我用了很大篇幅去叙述这些革命者在牺牲前做些什么,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在写诗,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信仰,歌颂光明,鞭挞黑暗。这些都是很震动我的细节。
当你面对一个人、一件事,所有的材料都在那里,关键在于如何抓住一闪而过的感觉,把它叙述好,去完成它,实现文学的理想——把真实的东西呈现为艺术化,使得真实更精彩。报告文学的难度就在这里,它必须是真实的,但是要写得活。
《革命者》里,我用黄炎培和他的儿子黄竞武的故事作为开篇。我在看材料时发现,1949年10月1日正是黄炎培的生日,当时我激动得都快跳起来了。你想,一个老人,一生追随孙中山革命,没有成功,但最后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71岁生日那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新中国的诞生,多么有意义。可是就在四个月前,他的次子黄竞武的遗骸在上海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监狱所在地被发现,在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夕,黄竞武为了保护属于人民的财产,惨遭杀害。我想象当时黄炎培的心情,一方面是改天换地喜的极致,另一方面是痛失爱子的极度悲伤,这样的解读完全是文学的解读,所以这个故事我是按照小说的方式来叙述的。
在《雨花台》里,我写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我抓住了他人生中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五四前后的他,天之骄子,意气风发,“偶像”级别的人物;第二个是他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忙碌奔波,虽然因为工作需要没有成为一大代表,但他实际上担任了中共一大会议秘书长的职责;第三个是他被捕后,视死如归,第二天要上刑场,前一天还在给狱友上党课。革命者的事迹不是单向和独立的,他们的血迹与足迹是融入历史洪流的,我的书写就是尽可能让人物跟历史风云走,让人物的精神随信仰而行,我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记者:我注意到你的写作有很强的主体性,叙述者“我”常常会出现在字里行间。
何建明:是的,这是我写作的基本观点,我的爱、我的恨都在我的作品里,这可能也是我的性格所致,在写作中一定要把自己放进去,我思考的问题,也同样是读者会思考的,我要带给读者同样的情绪,把作家的现场感和直接情感融入文学中,这是对叙述对象的敬畏和亲近感,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导读。毫不夸张地说,我写作写到激动的时候会抽筋,高兴的时候得意飞扬,痛苦的时候想跳楼,看到感人的人和事时真的会流泪。
记者:在你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反思性和批判性常常是评论家和读者谈论你作品时提到的关键词。
何建明:其实在我看来,反思性、批判性与歌颂性并不是矛盾的两极,真正好的作品不在于批判还是歌颂,而在于是否把故事讲好了,是否能打动读者,让他们的灵魂感到震撼,受到教育。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批判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革命者就是为了批判不革命者。我常常会打一个比方,不同的题材以不同方式处理,就好像我们有时是以太阳的光芒照亮月亮冰冷的部分,有时是用月亮的寂寞感、冷却感来反观太阳的光线是不是太刺眼。
记者:这几部作品推出之后,社会反响非常强烈。
何建明:这几年,我去很多地方讲党课,有些故事说出来后,台下的听众都会流泪,我想,这可能就是文学的魅力,把典型形象通过文学性的叙述呈现出来,这是党史写作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忠诚与背叛》写完后,我在想,党史的写法是可以探索的。一部《红岩》,尽管作家用了小说手法,有些人物和情节并不完全与真实的历史相符,但他完成了对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念的凸显,太教育人了,以至于很多人把它当成了真实的历史,由此可见文学的力量。
以前的很多党史写作是从文本到文本,可读性不强。而我在写的时候,首先确保材料都是真实的、有出处的,然后用文学的手法把它叙述出来,效果很好。所以我提出,要让党史和革命史“立”起来、“活”起来,抵达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灵魂深处,这样才能实现“以史为鉴”“以史正人”和“以史育心”的目的。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的,有教育意义的。从我的这几部作品的反响来看,党史写作的功效和魅力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淡化,这是让我很欣慰的。
记者:在《革命者》和《雨花台》中,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革命者中,来自江南的人士特别多,这是不是与江南文化中的某些特性有关?
何建明:确实,当时的江南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也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先行地区,各种思潮激荡之处,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善于思考,善于创新,他们有自觉意识,有思考问题的意识,要走出一条路,红色文化在这个地区酝酿、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江南,这块土地、环境确实适合知识分子革命,救国,实现自己完美的人生。
记者:在《雨花台》之后,你是否还有计划进行党史的写作?
何建明:我们要认识到,党史不仅仅是已经过去的革命史,党史正在进行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些年书写过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上海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新的党史”。我们的创作要和当下社会发展,党的引领下的历史和时代,以及和世界的关系密切关联,呈现新的党的历史,呈现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现在和今后继续写党史的意义,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呈现文学的价值。
记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近年来对于城市题材的关注,也可以视为一种新的党史写作。
何建明:可以这么说。我一直认为,中国作家对农村社会的书写非常成功,但是对当下的和未来的城市认识不够。写完《浦东史诗》之后,我意识到,上海是一个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它有革命的意义,有改革开放的意义,有从老城市到新城市的意义,也有从中国城市到世界城市的意义。我有一个判断,对城市题材的书写必定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高峰。现在的世界变化得太快,过三五年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对文学观念也要调整,作家不能等着生活,有些事一闪而过,要抓住当下的生活,最触动你感情的生活,把自己融入环境中,完成对世界的书写,顺势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