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虚构挑战真实”——2020年非洲法语文学综论
内容提要 非洲独立六十周年(“非洲独立年”为1960年)之际,2020年非洲法语区涌现了大量文学作品。从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到迷失在城市的外乡青年,从怀抱梦想的售票员到不得不冒险渡海的难民,丰富的人物构成了不同的声音,展现了后殖民时期非洲法语区特有的文学景象。此外,针对非洲法语文学,出版了多部有价值的研究论著,探讨了文学形式上的实验、文本中的殖民记忆以及非洲文学的跨文化性。
关键词 非洲法语年度文学研究 后殖民时期 迁移 成长
非洲法语区涵盖了具有不同文化与传统的广袤地域,那里有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以法语作为第一或第二语言。非洲法语作家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创作方式共同构建了他们的“非洲想象”,相对于以勒克莱齐奥为代表的书写旅行小说的欧洲作家与以莱奥诺拉·米亚诺为代表的长期移居欧洲等地的非洲作家,生活在非洲本土的作家对非洲有着不同的敏感性与丰富的观察视角。非洲法语文学在最近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不无关联,它们催生了非洲法语文学言说世界的特殊方式。2020年非洲法语区产生的重要文学作品涉及十个国家和地区:马格里布地区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尼日尔、科特迪瓦、喀麦隆、刚果,印度洋西南部岛屿地区的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法属留尼旺。相关的作家中既有优瑟夫·阿米·埃拉拉米(Youssouf Amine Elalamy)等老一代作家,也有盖勒·贝雷姆(Gaëlle Bélem)等文坛新秀,这些非洲法语作家以富于活力与创造性的书写在文学场域中展现出新的探索与追求。
一、投影到当下的历史
反思历史、探讨当下与过去的关系是非洲法语小说的年度热点。通常,历史被视为对过去的客观重建,记忆则被认为从情感、爱与怨恨中孕育生成。文学虚构总是与历史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使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阿尔及利亚到马达加斯加,从著名的历史事件到“沉默的历史”,非洲法语小说以虚构的方式重建历史,同时对当下与殖民时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主观探察,体现出文学特有的认知能力。正如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所说,“文学无法改变世界,但文学可以挑战真实,将真实化为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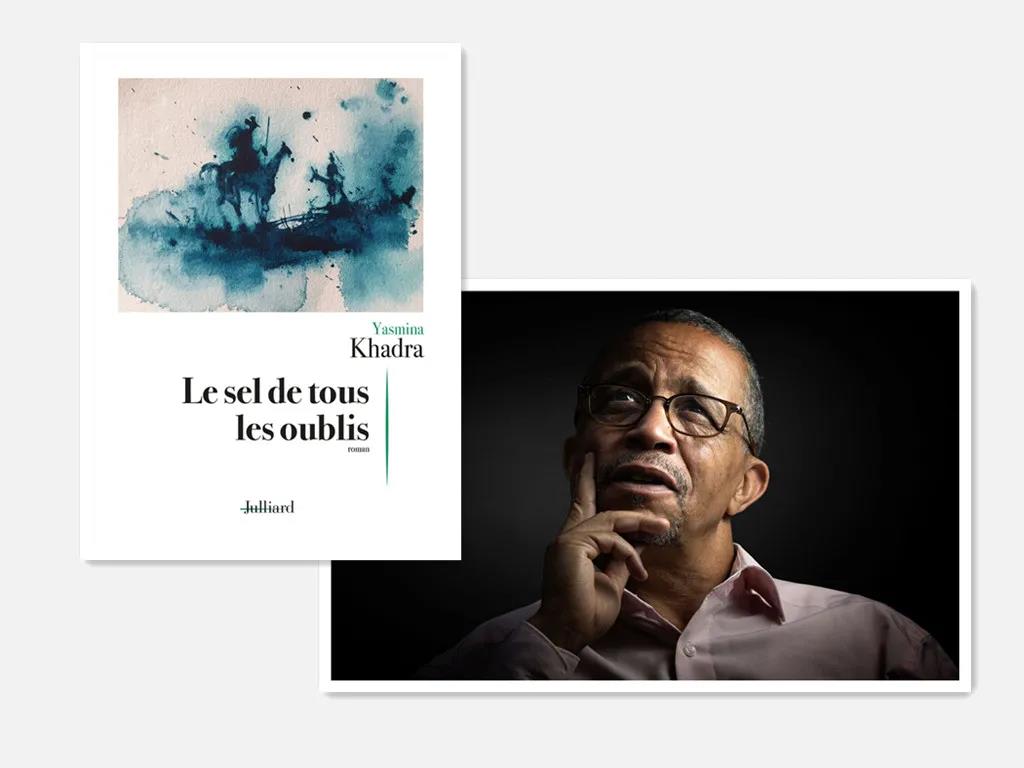
(《一切遗忘的妙趣》与雅斯米纳·卡德拉,图片源自Yandex)
阿尔及利亚作家穆斯塔法·本福迪尔(Mustapha Benfodil)的小说《阿尔及尔之密集日记》(Alger,journal intense,2020)涵盖了阿尔及利亚后殖民历史上的多个重要时期与重大事件。如1988 年的“十月骚乱”、历时十一年的惨烈内战等等。小说通过男主人公卡里姆生前遗留下来的日记、女主人公穆妮娅在丈夫去世那天开始书写的日记交替展开叙述。作家以拼图的方式建构起人物的日常生活,巧妙地在两人的故事中隐藏了1968 到2014 年之间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发展史,融合了个体经历与后殖民一代的集体记忆,体现了这一代阿尔及利亚人推动该国政治发展的努力。小说以挑衅性的笔调挑战传统理念,结合民间口述,集幽默与讽刺于一身。小说在形式上也颇具实验性,两个人物的日记分别使用直体和斜体,并辅以涂改杠、照片、留言、包装纸、图画等外文本形式,获得了穆罕默德·迪卜文学奖。阿尔及利亚的另一位作家雅斯米纳·卡德拉(Yasmina Khadra)的小说《一切遗忘的妙趣》(Le sel de tous les oublis,2020)则讲述一位突然遭遇妻子离家出走的乡村教师,离开熟悉环境,踏上了如现代堂吉诃德般的流浪之旅。透过主人公的旅途见闻,小说展现了独立之初的阿尔及利亚所面临的困境、地方政府的权利争斗及其对贫困阶层的影响。此外,小说中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压力、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阿尔及利亚当下状况的回声。
与上述两位作家对后殖民时期种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具有积极性的一面不同,毛里求斯作家达维娜·伊托(Davina Ittoo)的小说《苦难》(Misère,2020)更多地描述了毛里求斯独立后仍处于殖民阴影中的乡村。主人公是小镇上一个被抛弃的六指儿童,这个脆弱而缄默的孩子讲的唯一一个词语就是“苦难”。镇上的小伙子阿尔琼收留了他,音乐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奇特联系。这里的人们处于祖辈传统与狂热现代性的冲突矛盾中,同时依然被殖民幽灵所困扰。小说作者曾在法国生活十二年,回到毛里求斯后开始文学创作生涯。故事的发生地就是作者童年的居住地,但小说所表达的远远超越了这一城镇的边界,饱含着作者“对她的祖国毛里求斯的全部的爱”。

(乔哈里·哈瓦洛松,图片源自必应)
马达加斯加作家乔哈里·哈瓦洛松(Johary Ravaloson)的小说《爱情、祖国与螃蟹汤》(Amour, patrie et soupe de crabes,2020)也塑造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儿童人物——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街头流浪儿童埃里。埃里被位于市政厅前的“爱情广场”上竖立的喷泉景观所吸引,梦想可以到水池中洗澡,于是就“用他的小胳膊使劲晃动爱情广场四周围起的钢制栏杆,试图掰弯或拔掉它们”,广场的安保人员见状便挥棍殴打埃里,直至他昏迷倒下。在这里,广场是政权、权力的象征。“爱情广场”原名“5月13日广场”,因1972年发生在首都塔那那利佛市的“五月革命”而得名。“五月革命”被认为是马达加斯加的第二次独立,人们为呼吁国家政治经济改革并清除法国的影响而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市政厅在示威者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中被焚烧。2009年市政厅被重建,两年后政府又将其四周用路障封闭起来。作家在小说里以男孩埃里代表人民,并使用了马达加斯加过去一位总统的名字,赋予该人物以反抗性与希望,正如埃里所说:“我有一天会成为总统,改变世界……我要拆除喷泉周围的栅栏,使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它。”“螃蟹”则隐喻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强权势力,他们无视人民的贫困,愚蠢、浮华而自私。小说借鉴了中国皮影戏与西方木偶戏之间的戏剧手法来操持叙述主线,描绘的人物丰满而深刻,该小说是本年度非洲文学大奖决赛入围作品。
突尼斯作家海拉·菲基(Hella Feki)的小说《茉莉花婚礼》(Noces de jasmin,2020)与萨博·曼苏里(Saber Mansouri)的小说《七位勇敢的死士与一位端坐的诗人》(Sept morts audacieux et un poète assis,2020)同样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二者均以2011年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为小说背景。前者从内部描述了“茉莉花革命”,包括革命前的九天本·阿里独裁的覆灭及整个革命的过程。小说表达了人物的希望、创伤、恐惧和想要改变一切的抱负,将个人的声音与集体的命运相联系,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后者是一幅史诗般的肖像画,涵盖了突尼斯被法国人占领的时期、独立初期直到卡扎菲时代的历史。小说讲述了在2026年即“茉莉花革命”发生的十五年之后,突尼斯的民主尚在路上。
2020年入围非洲图书橘奖决赛的一部作品在内容上与众不同,它是摩洛哥作家阿卜杜拉·拜达(Abdellah Baïda)的小说《一本书的遗言》(Testament d’un livre)。该小说以一本被抛弃在摩洛哥菲斯图书馆的角落、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书的视角,回顾了自己的历史、书的历史,同时也涉及人类的历史。在重温它与作家、读者们共度的默契而美好的时刻中,中世纪发生在摩洛哥的焚书事件、纳粹在柏林的焚书事件等书籍所遭受的灭顶之灾打破了书的温馨回忆。该作品是一首献给图书的颂歌,它透过人类历史的不同时代与空间,讲述了图书家族的真实经历,并探讨了纸质图书的未来。
二、漫漫离乡路
在非洲法语小说中,背井离乡是一个沉重、广泛、持久的主题。尤其非洲人为到达“遍地黄金”的欧洲而穿越地中海的“自杀式移民之旅”,在文学作品中由来已久。对于小说人物来说,背井离乡往往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放逐,常与记忆的哀伤、身份的迷失相连。他们选择背井离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战争冲突、贫困、宗教、不完善的家庭关系等。为了生存和更好的前途,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了迁移之路。迁移中一类为“外部迁移”,指跨国迁移,另一类为“内部迁移”,指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的迁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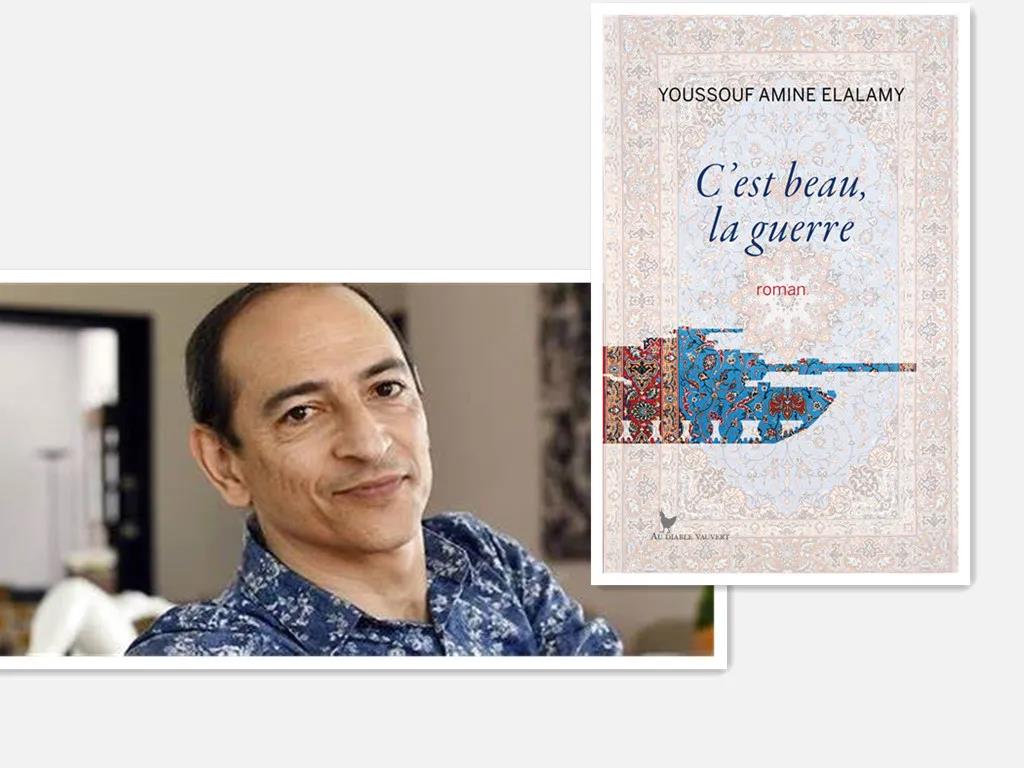
(优瑟夫·阿米·埃拉拉米与《战争是美好的》,图片源自必应)
摩洛哥作家优瑟夫·阿米·埃拉拉米(Youssouf Amine Elalamy)的小说《战争是美好的》(C’est beau,la guerre,2020)这部标题充满反讽色彩的作品获得了年度非洲图书橘奖。故事叙述者是一位年轻的男演员,为逃离内战,他登上一艘破旧的航船,走上流亡之路。经过漫长而危险的海上旅程,他抵达了彼岸一个满是度假人群的沙滩。在一处难民营,他发现周围的女性同胞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位至亲,或是丈夫、情人,或是儿子、父兄。为减轻她们的痛苦,他决定一一倾听她们的讲述,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使逝者重现。“她们向我说起她的他,我就代他去看,代他去讲,代他去拥抱如此想念他的女性,代他用双手拭去她为他流下的泪。”主人公力图用艺术治疗这些饱受战争创伤的移民的心灵。
喀麦隆作家赫姆利·布姆(Hemley Boum)的小说《日子来又去》(Les jours viennent et passent,2020)也以因困境而选择背井离乡为主题。作者以历时性叙事讲述了喀麦隆三代女性的命运:暮年安娜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在喀麦隆与法国之间的颠沛流离,女儿阿比为远离家庭冲突而选择移居法国,年轻的蒂娜则因现实困境而被暴力组织所蛊惑,卷入致命的招募。三名女性的声音相交织,反映了当代喀麦隆的暴力、流亡与文化传承等问题。小说获本年度阿马杜·库鲁玛文学奖。科特迪瓦作家高兹(Gauz)的小说《黑人马诺》(Black Manoo,2020)则通过一位非洲青年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的社会下层与巴黎美丽城之间的游走经历,讲述了初到巴黎并准备定居的非洲无产阶层移民的生存策略。小说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叙事节奏快,人物描写细腻、简洁,笔调带有维勒贝克式的讽刺与辛辣,提出了“我们为什么去向他处?”这一尖锐问题。
与以上几部所描述的或多或少具有主观意愿与目的的迁移不同,法属留尼旺作家让-弗朗索瓦·萨姆隆(Jean-François Samlong)的小说《放逐的太阳》(Un soleil en exil,2020)中的跨海迁移则与一场集体性犯罪相关。作品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书写而成。1962年的留尼旺岛虽已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但殖民阴影依然没有散去。岛上资源有限而人口在不断增长,法国政府便认为该岛青少年是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尤其考虑到法国大都市周边的乡村需要廉价劳动力,于是一场儿童迁移事件发生了。1962至1984年,两千多名留尼旺未成年人被流放到法国克勒兹省等地,其中最小的只有六个月大,造成了一系列悲剧与灾难。小说主人公艾娃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遭遇,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来自留尼旺的贫困家庭,当社会福利员巧言许诺美好的未来时,贫困的母亲们便在同意政府收养孩子的文书上签了字,以致孩子丧失了原有的身份,丧失了自由。艾娃和两个弟弟到达法国后被迅速分开,到了晚年,她才重回家乡。小说以艾娃寻找两个弟弟为主线,展现了这些“被偷走的儿童”背井离乡并几乎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艾娃用善良与爱去面对种族主义、剥削、冷漠所带来的苦难,用书写治疗了伤痛。该作品入围了年度墨提斯小说大奖决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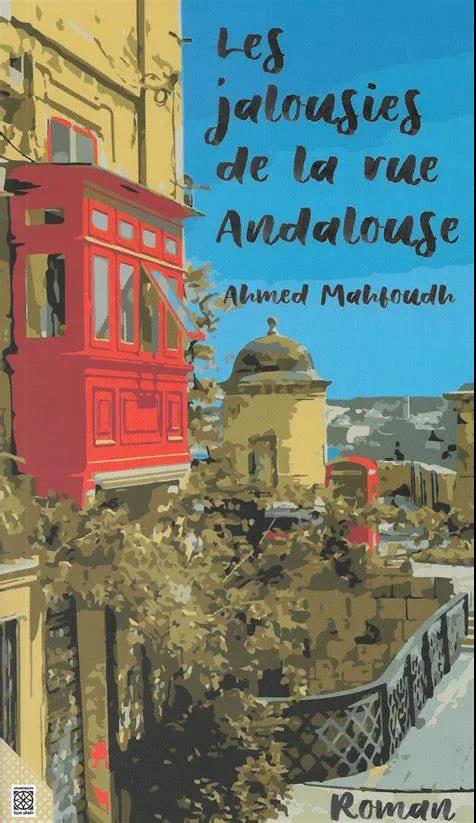
(《安达卢斯路上的百叶窗》,图片源自必应)
在涉及“内部迁移”的非洲法语小说中,“城市里定居的市民与外来乡村流动人口之间的古老战争”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主题,突尼斯作家艾哈迈德·玛哈福德(Ahmed Mahfoudh)的小说《安达卢斯路上的百叶窗》(Les jalousies de la rue Andalouse,2020)是这类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主人公阿兹祖兹系大户人家佃农的儿子,从突尼斯乡下到首都学习法律,期盼有朝一日穿着黑色长袍,“被老百姓称为律师大人”。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正值突尼斯社会巨变、新旧秩序更替的转型时期,暴发户、野心家组成的新阶层替代了旧时代的政治-文化精英而成为新的上升阶层。阿兹祖兹在所谓“器物的现代性”的洗礼中很快发现这一变革意味着什么,并掌握到相关机制,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重大时机。这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卑微出身,全力投身这场变革之中,从处于社会边缘的乡下人成为律师、不动产投资人,但最终在事业与爱情上均遭失败。小说折射出了为社会巨大变革所裹挟的人物命运的荒诞性。
三、成长的烦恼
成长小说长久以来一直在非洲法语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非洲法语小说塑造了很多寻找自身位置的年轻人形象。欧洲18世纪的启蒙文学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建立起成长小说的传统,尤其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广泛影响了当代非洲成长小说。近年非洲法语成长小说具有一种新的倾向:人物的“成长”不再仅是自我“建构”,不再单纯表现从最初的理想或幻想转变为清醒的实用主义,去适应现实,去寻求与世界的相符,而是更多地强调人物要对现实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加以应对,并在流动变化不断加剧的现实中寻求自身与世界的结合。在规则不完善或缺席的情况下如何成长?面对复杂混乱的现实,是否应该抛弃自己最初理想的“建构”?这些正是本年度非洲法语成长小说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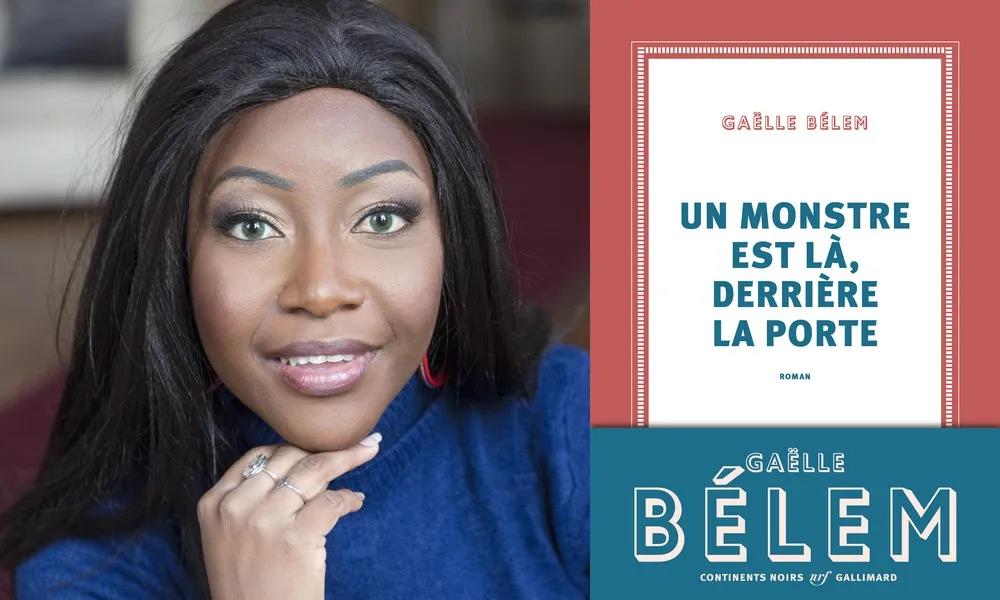
(盖勒·贝雷姆与《门后有妖怪》,图片源自必应)
法属留尼旺作家盖勒·贝雷姆(Gaëlle Bélem)的首部小说《门后有妖怪》(Un monstre est là,derrière la porte,2020)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留尼旺贫困家庭中一个小女孩德森特的成长故事,获得年度墨提斯小说大奖。作家的目光完全没有停留在留尼旺作为度假胜地的光鲜亮丽上,而是投向了存在着贫困、暴力、失业、酗酒、迷信等社会问题的平民区,在这里奴隶制的历史印记混杂了各种粗俗的弊病。七岁的德森特清醒地看待她周遭的人及她的生活,意识到贫困下隐藏的暴力危险,“我在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因为我没有手枪”。书名“门后有妖怪”中的“妖怪”,有双重寓意:一是令父母烦恼的小姑娘德森特,一是门后等待着小女孩的各种困难,如社会决定论,出身低微的人注定一生艰难前行,还有种族主义的冷漠。“留尼旺是法国领土上不平等性最为严重的地方”,盖勒·贝雷姆如是说。除了外部环境的严酷,小姑娘面对的家庭内部环境也令人堪忧。父亲重男轻女,恐吓式家庭教育使她一出生就面对憎恶与暴力,而阅读、书写、见证、驱邪、斗争、存在是德森特从小萌生的愿望,她希望成为“施魔法的作家”和“超越自身的身份与生活环境”,梦想与父辈不一样的生活。小说以德森特的视角书写了她出生后二十年的成长岁月,内容沉重严峻又不乏轻柔与诗意,笔调时而尖刻时而温情,是一部优雅风趣又令人心酸的作品。
科特迪瓦作家亚雅·迪奥曼德(Yaya Diomande)的小说《阿波波·马雷》(Abobo Marley,2020)的主人公穆萨也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物。穆萨是小镇上的公共汽车售票员,被称为“摇摆者”,每天在城镇之间来来去去,招揽乘客。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去欧洲工作、生活,他凌晨开始工作,做过擦鞋匠、机械技工学徒、司机,从事过相当危险的工作。在作者看来,科特迪瓦是一个特权社会,年轻人缺少上升途径而不得不远走谋生。该作品旨在揭示科特迪瓦的社会现实,为社会底层发声,主人公以孩童般质朴的声音讲述了一个年轻人永不言弃的奋斗之路。作品被称为“现代版《奥德赛》”,语言生动而富有感染力,获得本年度非洲之声文学奖。
成长的过程必然充满变化与曲折。巴赫金曾经说过,“[这一类小说中的]成长中的人物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在非洲法语成长小说中,有的人物面对贫困和暴力的社会现实选择了奋斗与抗争,有的人物则在成长中走向扭曲与畸变。如小说《日子来又去》中的女青年蒂娜,其家境并不贫困,但因殖民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和权力阶层的腐败堕落而最终选择了出走,加入了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小说分析了喀麦隆的极端主义与暴力问题的根源,抨击了被博科圣地召集起来的年轻人的暴力活动,强调了在青少年成长中教育的重要性。又如前文提到的《安达卢斯路上的百叶窗》中出身寒门的青年主人公在努力进取之后,为金钱所诱惑,成为如同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一样的野心家。他加入到既无信仰也无原则的社会新阶层中,使自己的人格走向畸变,最终在空虚与失落中了却一生。
2020年非洲法语小说除涉及以上几大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小说聚焦生态问题。如法属留尼旺作家拉露(Lalou)的探险小说《树的脚》(Pieds de bois)被称为“一部绿色小说”。主人公展开航海旅行,驶向一个住着神奇居民的、时间暂停的岛屿,那是一个尊重环境、尊重自然的世界。然而,当海上暴风雨停歇下来,利益的暴风雨接踵而至。“公司”的到来使该地所守护的文明灰飞烟灭,“公司”为利益所驱动而对大自然进行剥夺,采用不正当手段致富。该小说是大自然的一声呐喊,为昨天与今天的消费主义的泛滥敲响警钟。《安达卢斯路上的百叶窗》则展现了作家玛哈福德对城市生态问题的担忧。玛哈福德被称为“城市作家”,他的所有小说都与突尼斯旧城和欧化新城有关,对“失去的城市”的探寻是他小说中的重要观照。20世纪80年代以降,混乱无序的建筑潮随着现代性的突飞猛进席卷了突尼斯。森林、滨海地带遭到破坏,在环礁湖上、河边……甚至在考古遗址上也修建了房屋。曾经位于城市中心(即旧城)的文学咖啡馆、电影院等文化空间被银行、商业中心所取代,纪念性的古老宅院变成了贫民窟而遭到损坏,正如小说中作为文化遗产代表的安达卢斯老宅被其继承者变成了储存商品的仓库。城市纪念性建筑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它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衰落,作家在小说中呼唤对城市文化遗产进行保护,重建与传统之间的连续性,维护城市的文化生态。
针对非洲法语文学,本年度有多部研究论著问世,它们从不同侧面剖析了非洲法语文学近年来的新动向:
其一,关注文学形式上的实验与探索,如加拿大作家、学者利兹·高文(Lise Gauvin)、法国学者罗穆拉德·丰库亚(Romuald Fonkoua)与弗洛里安·阿利克斯(Florian Alix)主编的论著《论当代法语区小说》(Penser le Roman francophone contemporain)探讨了法语区小说在形式上的贡献,其中尤其谈到印度洋西南岛屿地区方兴未艾的“碎片美学”。从1999年至今,毛里求斯、法属留尼旺与马达加斯加出版了诸多体量相当短小的文学作品。它们以极短的虚构叙事为特征,处于小说的边界,被称为“断片之书”或“散书”。这种“碎片美学”受到解构游戏、元虚构与后现代的自反等因素的影响,体现出另一种叙事思维。一方面,它折射出后殖民主体面对当代世界与自身复杂处境所感到的深刻不安,该地区的奴隶制历史、人口贩卖史、殖民史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历史”,它们留下的阴影仍然影响着那里的所有人,造成“主体意识的脆弱性”;另一方面,“碎片美学”也承载了主体的内心流浪,承载了一种“根本的反抗征象”,它体现了双重的诉求:恢复主体经验,反对所有带有欺骗性的、固化的普遍概念,并以坚定的态度对习俗惯例进行重新思考。
其二,关注作品内容传递的声音。加拿大学者菲利普·巴萨波斯(Philippe Basabose)与约西亚·塞穆扬加(Josias Semujanga)主编的论著《法语区小说与殖民档案》(Le roman francophone et l’archive coloniale)从小说的历史维度研究了法语区小说如何书写了殖民记忆,它们通过在叙事、话语与语义上的多样化表现,使殖民记忆构成了法语区作家文学想象的一部分,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构成法语区群体的观念史的一部分,同时考察了当代文学中对殖民时代的不同观点以及这些作品在法语区后殖民社会中的接受。加拿大学者阿历克西·切亚普(Alexie Tcheuyap)与美国学者埃尔韦·楚姆卡姆(Hervé Tchumkam)的论著《非洲法语小说中的恐惧与不安全感》(Avoir peur,insécurité et Roman en Afrique francophone)则从殖民经历出发,分析了恐惧持久地存在于一代又一代非洲小说家笔下的原因,提出恐惧是否是非洲后殖民经验的基本范式的疑问。作者通过对非洲法语小说的跨学科分析,阐述了在这些文本中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的历史与当下的复杂原因,诸如暴力、恐怖主义、战争、流行病、政治斗争等。其中,经济因素使人产生的不安全感也不容忽视,如尼日尔作家伊迪·努乌(Idk Nouhou)在小说《蠢蛋们的国王》(Le roi des cons)中谈到的由强国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所导致的“不可见的力”使跨国公司严重制约着非洲国家。在阐释文学中的恐惧与不安全感这些征象的同时,该论著还探讨了国家与政治的意义。
其三,关注文学的跨文化性。法语区文学是一个异质的复杂整体,非洲法语区文学因其带有不同文化地域的符码而呈现出多元而独特的身份。如小说《门后有妖怪》体现了法属留尼旺的世界性与混合性文化特征,书中混合了法语、克里奥尔语、拉丁语、阿拉伯语、马约特语,甚至还有中国的普通话,使书中呈现的留尼旺这个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岛屿犹如一座巴别塔一般。针对非洲法语文学的跨文化性,摩洛哥学者阿法·扎伊德(Afaf Zaid)的专著《从文化多元性到文学的活力:摩洛哥法语文学的声音》(De la diversité culturelle au dynamisme littéraire:voix marocaines francophones)与学者达尼埃尔·德拉(Daniel Delas)、摩洛哥学者哈立德·泽克里(Khalid Zekri)、德国学者安妮·贝格纳特-诺施费尔(Anne Begenat-Neuschäfer)主编的论著《马格里布地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叙事混合与张力》(Hybridations et tentions narratives au Maghreb et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前者强调摩洛哥文学以其丰富智识充实了摩洛哥的文化场域,增强了它在世界文学中的认知度,多元性的文化使摩洛哥当代小说孕育生成了新的美学特征,其中非洲口头文学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摩洛哥法语文学中得到传承;后者则聚焦马格里布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建立起来的象征空间,分析了在文化混合的语境下作家所使用的书写策略以及这些书写策略所产生的价值。
2020年对于非洲法语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独立六十年后如何重建与历史的关系、如何面对移民问题与青年问题构成了本年度非洲法语文学的三大主题。在针对非洲法语文学的研究中,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实验场域所传递出来的后殖民主体的声音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矛盾中尚存选择,苦难中尚存希望,难以忍受但并不使人消沉是其中诸多作品呈现出的共性特征,这也被视为当下非洲法语文学所展现出来的勃勃生机的原动力。刚果小说家、著名学者阿兰·马邦库(Alain Mabanckou)在法兰西学院讲授黑非洲文学史时曾说道,“法国不是法语世界的唯一重心”。在全球化的今天,非西方文学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非洲法语文学的勃兴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