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读《杨宜治日记》—— 晚清士大夫的阴阳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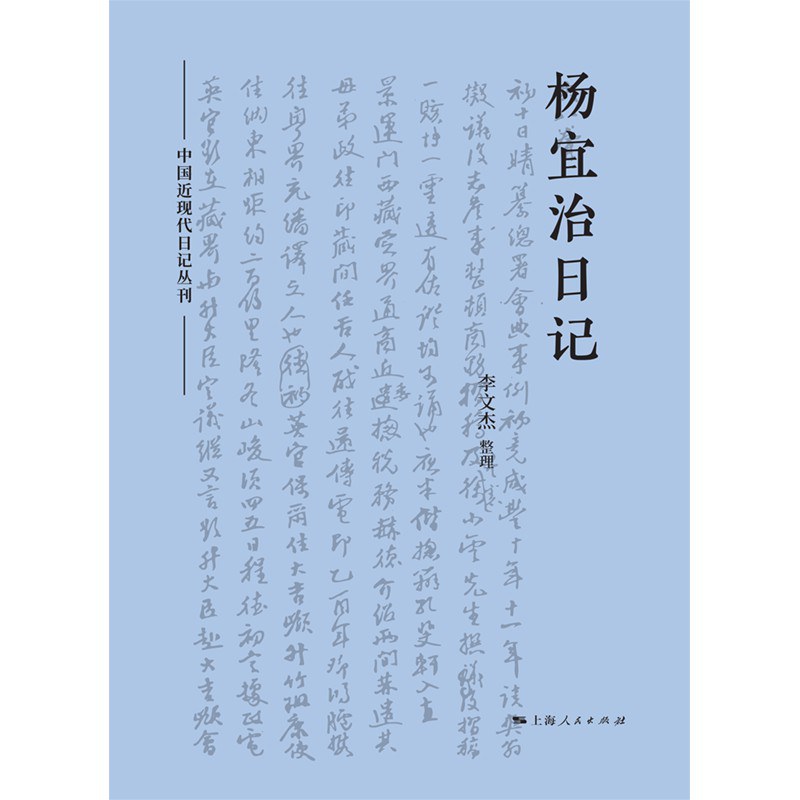
《杨宜治日记》,李文杰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光绪年间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的日记,共三部分,覆盖中法勘界(1885-1887)、京官生活(1887-1890)、随使俄国(1894-1895)三个时间段,经李文杰整理出版,阅读甚便。日记内容丰富,李文杰《整理说明》已有详细介绍,并在附录中对杨宜治的京官生活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笔者在李文杰既有成果基础上,剑出偏锋,尝试抉发日记中一些隐秘,审视晚清士大夫“阳面”之外的“阴面”。
士大夫与杂学
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约1845-1898),字虞裳,四川渠县人,以举人考取内阁中书,1884年传补章京,入总理衙门,先后在司务厅、英国股工作,后升总办章京,是办理外交实务的骨干人物。1885年夏,中法两国约定共同勘定中越边界,杨宜治被勘界大臣邓承修奏调为随员,除在广西、粤西现场工作外,先后在广州盘桓颇久,经常向其师李文田请益,两人有不少共同爱好,交往极密。
李文田(1834-1895),字仲约,号若农,广东顺德人,1859年一甲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历迁各职,官至侍郎,学识渊博,官声甚好,在元史研究、西北史地、金石书法等多个方面均有成就。1882年,李氏丁忧回乡守孝三年,居广州西关。在野史笔记中,有几个作者谈到他“善风鉴”,也即精于相术,说得神乎其神。杨宜治日记披露了李文田在风水学方面的造诣,从侧面证实野史所说“善风鉴”有一定可信度。1885年10月11日,杨宜治写道:“李若农师邀游白云山麓,视太公葬地。地由白云开账,楼阁重重,脱卸秀嫩,坤艮下脉。入手起定正龙,西去三节,卸落平阳,结省城腰落,横列三台。中台另起化生脑,开小坪两台,为夹耳砂。枝脚转抱为牛角蝉翼,前唇兜起,内局紧密,外局平远,明堂收三江之水,生气远出,穴法最当。”(第16页)
笔者不懂风水之学,但也能看出杨宜治这段话外行人写不出来,他跟李文田都是同道中人。第二天,杨宜治又得读李文田精心注释的杨筠松《撼龙经》,大赞“令后来读者如夜行见烛,千古之下,独具只眼”。杨筠松,窦州人,被誉为风水学“江西派”鼻祖,《撼龙经》也是风水学最重要经典之一。李文田在序言中,考订杨筠松为五代后唐时人,并非人们热衷吹捧的“大唐”;李氏并以他渊深的学识,校正传世版本的不少错误。
帝制时代,读书人以十三经、历朝正史、诗古文辞为正统,天文地理、星象医卜、奇门六壬谓之杂学。然而,普遍的情况却是,读书人至少都熟悉一门杂学。正经正史板着脸孔说教,不免审美疲劳,反而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杂学有着特殊吸引力,还具有一定实用性。通过日记,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晚清官场的“阴阳”两面,即朝廷一面提倡正经学问,也不反对士大夫从事“杂学”,容忍他们研究堪舆、相术。
堪舆之学的消极一面是常被晚清士大夫用作阻拦改革的借口。1888年12月15日,杨宜治听到广东顺德人、同治十年状元梁耀枢在山东去世的消息,遂大发议论,说去年在广州时,跟风水师杨厚馀勘察形势,杨厚馀认为广州龙脉从西北来,张之洞办机器局,龙脉被凿伤太甚,联想到这一年有四个广东“贵人”相继病逝,即前闽浙总督何璟(香山人)、同治十三年榜眼前云南粮储道谭宗浚(南海人)、谭宗浚同科进士姚礼泰(番禺人)、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番禺人)。(第201页)杨宜治觉得杨厚馀的说法似乎灵验,机器局破坏了广东龙脉,导致五个精英人物丧命,今日看来殊为可笑。
李文田与闱姓开禁
闱姓赌博对晚清政治、经济与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淮系两广总督张树声主张严禁,湘系名将彭玉麟、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弛禁,朝野各方为严禁、弛禁形成生死博弈,弛禁派曾面临着极大政治风险。两广总督英翰曾拟在广东开禁闱姓以增加赌饷收入,因饱受朝野攻击而落职。闱姓弛禁可带来巨额收入,使张之洞增加了底气,在中法战争中敢于放手一搏。闱姓赌博的合法化,打破了多年来的禁忌,使其他非法赌博在广东进一步泛滥,是清末民初广东社会治安恶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闱姓多被认为是赌博的一种,实际上应归类于彩票。据赵利峰的研究,闱姓“主要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姓氏作为猜射投注的对象,最早出现在嘉庆年间的佛山。闱姓主要开设售卖于广州、澳门两地”。这种生意一度成为澳门的经济支柱。(《尴尬图存: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第75页)1867年广州严厉禁赌后,闱姓生意在澳门获得迅猛发展,造成“利权外溢”。为给中法战争筹措军费,1884年底兵部尚书彭玉麟、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廷于1885年1月批准在广东开禁闱姓,由赌商集团承办。何汉威、赵利峰等学者先后对闱姓做过精湛的研究。赵利峰认为,彭玉麟是闱姓开禁的关键人物,但此前很多学者都将功劳(或者过错)算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头上。
张之洞莅粤仅及半载,在处理有关中法战争的紧急事务外,要在短时间内权衡闱姓合法化的利弊、确认闱姓赌商能够筹集巨款,并不容易,需要十分熟悉广东、澳门情形的人士提供意见。将《杨宜治日记》与李志茗对《赵凤昌藏札》的研究相结合,笔者深信:奏请闱姓开禁的前台人物是彭玉麟、张之洞,出谋划策并促使彭、张下定决心的则是居于幕后的李文田。
杨宜治此次到广州,李文田不仅带他一起勘查祖先墓地,也多次招饮,赠送珍贵碑帖拓本,两人共同语言甚多,近乎无话不谈。杨宜治在对闱姓运作条分缕析之后写道:“某先生居林下,有清望,当轴就请任团练筹饷”,趁机提出利用闱姓筹款的方案,其十分有力的论证是:“输之闾阎,不若取之闱姓,以无益为有益,款易集而民不伤。”(第18页)“居于林下”,应为退职居乡的粤籍官员;“有清望”,则不会是以敛财著称的“浊流”人物,而是清廉著称的学者型高官,这样才能得到张之洞、彭玉麟的信任。张之洞既以“清流”健将著称,彭玉麟也是名满天下的清官,他们不容易被商人买通,却容易为李文田所说服。
李志茗长年研究《赵凤昌藏札》并写成《幕僚与世变》一书。赵凤昌为张之洞核心幕僚之一,《藏札》里面收录了李文田给张之洞的不少密函。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李文田有一函复张之洞:“闱姓、禁蟹、扛鸡等票充饷出于鄙说。昨承派交郡伯核办,可谓得人。”(李志茗《幕僚与世变》第375页)
李文田在密函中自承,开禁闱姓赌博用于充饷,出自他的倡议。作为张之洞敬佩的翰林前辈,李文田的建议与其他人的建议,效力完全不同。当时,澳门赌商担心广东弛禁闱姓冲击他们的生意,花钱买通京官出奏力主严禁,挥舞道德大棒加以猛烈抨击,其真正意图是:若广东继续严禁的话,澳门闱姓生意就有了保障。另一派赌商为争夺这笔大生意,同样买通京官,向朝廷奏请弛禁。以李文田的清望,张之洞不相信他会被赌商买通,纯粹是出于公共利益作此建议。李文田的出谋划策乃是推动闱姓弛禁最为关键的一环。
李文田、张之洞均探花出身,都是科举制度最大得利者。闱姓以科举考试考中者姓氏为投注对象,消解了科举的严肃性,特别是县试、乡试环节,考官容易被赌商买通作弊,影响科举考试的公正。尽管意识到可能出现这些弊端,李文田、张之洞两个探花为解决迫在眉睫的饷需问题,仍愿意承受闱姓对科举制度的冲击。闱姓开禁,在六年内为广东贡献四百四十万两饷银(1886年广东全省岁入仅得四百五十六万两),张之洞督粤后期兴办铁厂、织布局的启动资金出自闱姓赌商的“报效”,铁厂、织布局设备后随张之洞改运武汉,成为汉阳铁厂、湖北纺织四局的最初基础。
闱姓开禁一事,彭玉麟、张之洞身在明处,因职责所在不得不挺身而出,承担政治风险;李文田以丁忧在籍绅士,藏身暗处,以精密的通盘策划说服张之洞,利用他的威望在赌商与彭玉麟张之洞之间沟通协调,终促成这一褒贬参半的重大举措。历来爱惜名声的彭玉麟为何也能下此决心,似乎是受其直接下属、会办湘军营务处郑观应影响,这在郑观应呈彭玉麟禀稿可寻得蛛丝马迹。一事之成,往往是阴阳相辅的结果。
杨宜治与潮州鸦片商
杨宜治在日记记录了十分频繁的饮宴和收藏活动。晚清京官普遍清苦,若无额外灰色收入,诗酒酬唱、书画碑帖收藏恐怕难以为继。李文杰在本书附录长文中,对杨宜治的交往活动与日常生活有深入全面的分析,唯对他与鸦片商的交往未及注意。
日记中,杨宜治多次提到与广东潮州籍商人的交往,并反复提及一家名叫“德盛”的商号。作为四川人,杨宜治与广东潮州人士并无科举、学术、文艺方面的渊源。杨氏的交往圈子极其清晰,即同乡、科举同年及前后辈、师门、同僚、其他官场人物,他跟潮州籍商人的交往活动,明显不合常规,笔者认为此中隐藏着利益输送的秘密。
“德盛号”是潮州商人在上海及各口岸设立的商号,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华人鸦片商。潮阳商人与鸦片贸易挂上钩,始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南澳岛、汕头妈屿,两地乃是鸦片趸船的主要停泊地。潮阳商人掌握了鸦片的内地分销渠道,跟随英国人进驻上海,西进镇江,北上烟台、天津、营口,几乎垄断了沿海、沿江的鸦片贸易。
潮州商人很早就到苏州、上海经商,对外统一建潮州会馆,内部却分为三帮:海澄饶帮,潮惠帮,揭普丰帮,其中潮阳商人为后起之秀,以经营鸦片著称,尤以“德盛”为翘楚。1839年,因林则徐厉行禁烟,其他两帮对潮惠帮经营鸦片颇有微词,遂另立潮惠公所,后毁于战火,同治五年在十六铺码头附近重建“潮惠会馆”,捐资商人中,“德盛号”列第一位,捐银六千四百二十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25-326页)
1874年,合伙经营德盛号的潮阳范氏、郭氏拆伙。1874年8月底《申报》发表范德盛号声明称:“启者。德盛号向系范、郭合伙,嗣缘分创,乃于本年三月十五日凭公亲调出,议立笔据,所有上海存欠帐目各认一半,旧行基址议归范氏,住家房屋议归郭氏,各自出姓,以分界划。天津、烟台德盛字号以及帐目存欠统归范氏承管,自收自理,与郭无涉;营口德盛字号以及帐目存欠统归郭氏,自收自理。范氏在营伙友于端节一概交盘分手;并两沙逊往来帐目,已经会同过伙当面交割清楚,与范无涉。现在范氏在营另创范振记字号,精选顶庄大小洋药发客,倘蒙贵行商赐顾往来,请分别认明,庶不致误为幸。范德盛主人谨白。”
拆伙之后,范德盛、郭德盛两个商号分立。上海的资产负债两家均分;原商行建筑归范氏,住家房屋归郭氏;天津、烟台德盛号资产负债归范氏继承,营口德盛号资产负债归郭氏。两家为免日后纠纷,各自在德盛号前面冠姓,但杨宜治仍含混地叫做“德盛”。
1888年1月8日,杨宜治在北京,“晚赴德盛号便酌,同座吴君在陶(昌坤,举人),陈君明初昆弟,主人姚柳阁、姚湘舟、范炤丹、方君。湘舟明日回津。皆潮属人”。(第157页)范炤丹,本名不详,他跟两个姚姓商人既然是这次宴请的主人,可以认为代表了范德盛号。这年4月6日,北京大栅栏发生大火,杨宜治记道:“焚广德楼至鼎和居十数间,德盛几危。”(第166页)大栅栏大火,杨宜治独独关心“德盛”安危,内有深意。1895年7月7日,杨宜治跟随王之春祝贺俄皇加冕回国,路经上海,“访德盛范秉初”。(第327页)范秉初,也写作范炳初,据研究即是范德盛号东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416页)月底,范秉初设宴为杨宜治饯行,另有一次作陪,可谓殷勤之至。(第329页)
1887年9月28日,勘界工作结束后杨宜治从广东北返抵达上海,寓外洋行街潮州会馆,会见郭子清、陈雁初等潮籍人士。(第141页)杨宜治若入住四川会馆,或上海道台安排的其他住处均属正常,入住潮州会馆则很不寻常。次年6月12日,杨宜治在京,“潮人陈雁初自沪来拜”;6月20日,又约陈雁初等人在聚宝堂饮酒。据宋钻友对上海潮州会馆档案的研究,陈雁初潮阳人,鸦片商行“聚成行”老板,也是上海潮州会馆董事。(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第72页)日记另有两处记录与“陈明初坤弟”会面,推测陈明初应为陈雁初的兄弟。从1889年8月31日《申报》“潮阳郭子清启”可知郭子清为潮阳人。至此,杨宜治与潮阳鸦片商之间的交往,可大体看出端倪。
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负责官方外交外,也管理协调多种“洋务”事宜,包括解决中外商人之间的重大纠纷。1884年老沙逊洋行决定辞退买办陈荫棠,要求保人范德盛赔缴陈氏所欠洋行款项,遭到拒绝后,向上海会审公廨提起诉讼。公廨判令范德盛先缴银六千两,其余再限期缴还。范德盛不服,向上海道台邵友濂上控;上海道与两江总督支持范德盛的诉求。12月,此案上诉到北京,由总理衙门与英国驻京公使进行谈判,总理衙门支持范德盛,与英方据理力争,将案件发回上海复审。1885年4月12日邵友濂作出判决,裁定老沙逊的索赔要求应由陈荫堂的未付薪水等抵消,范德盛在此案中取得完全胜利,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巨额损失。(曹英《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问题研究》第238-242页)
笔者猜测,范德盛在此案发生后,认识到结好总理衙门章京的重要性,因而刻意笼络杨宜治。总理衙门堂官(大臣)均属兼职,具体事务多由章京、总办章京负责办理。1887年9月回京之后,杨宜治担任英国股章京,处理对英交涉、各国通商与征税事务,与德盛所从事的鸦片生意有密切关系。按照一般官商关系的逻辑,若杨宜治能及时提供内幕消息,或通过各口岸海关道为鸦片商提供“方便”,在与洋商发生纠纷时加以撑腰,那么鸦片商的“回报”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再三、再四宴请只是笼络感情,背后的交易内容,杨不会披露,但仍给人以想象空间。
日记的“补史”功能
内容足够详细的日记,有助于填补其他史料的“空缺”,重现事件、人物的更多细节。杨宜治在广东、广西甚至上海停留期间,接触人物众多,日记记录了从张之洞、郑观应、刘永福、冯子材、梁鼎芬到大量中低层官员的言动,足可“补史”。对晚清史研究来说,《杨宜治日记》可利用之处甚多,笔者随手撷取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邓承修曾将勘界之行写成日记,收录于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成修勘界资料汇编》,限于当时条件,讹误颇多,不便利用。中法战争前,李鸿章派出安徽桐城人马复贲潜入越南刺探情报,绘制成《越南今地舆图》,对中方的战场指挥有较大帮助。邓承修南下经过天津时,让马复贲参与勘界。此人官职虽低,却是中法战争中不可复缺的人物。广西版《邓成修勘界日记》里面,马复贲多次以“马太史”出现,这是较严重的错误。笔者虽未见《邓成修勘界日记》原稿,但依据《杨宜治日记》,可认为这三个字应该是“马大使”,当时马复贲的职位是盐大使,属正八品“风尘俗吏”,“太史”则是对翰林的尊称,在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杨玉书原是山西候补道,张之洞抚晋时的老部下,后被张之洞调任广东。1885年杨玉书出差,在轮船遇见辜鸿铭,十分赏识他的才学,把他推荐给张之洞,辜氏得以成为入幕之宾,成就日后大名。1886-1887年间,杨玉书受命负责海南开发,功劳卓著,备尝辛苦,不幸感染“瘴气”英年早逝。此前,学界对杨玉书了解甚少,籍贯、字号均失载。朱寿朋《清代人物大事纪年》误记杨玉书为湖南湘潭人,当是因同名人物而致误。1885年10月2日,杨宜治写道:“午后访杨次麟(玉书)……诸乡人,皆不遇”,可知杨玉书为四川人,字次麟。其后两人多次见面。
笔者颇赞同戴海斌的“中等人物”说,即对晚清史的研究,不能仅仅聚焦于名气最大的几个“大人物”。大量不处于“第一线”的人物,或曾在幕后推动了重大决策,如李文田对闱姓赌博解禁的贡献,或曾在特殊时期扮演过关键角色,如八品小官马复贲充当“间谍”测绘越南地图,或实心任事英年早逝而名声不显,如为开发海南而殉职的候补道杨玉书。杨宜治与鸦片商的密切交往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可令人对晚清士大夫的阴阳两面加深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