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真实内心”的悖论——重释西方现代小说的兴起
摘 要 英国及法、德现代小说源于“虚构真实”观念和“内心”观念同时兴起并相互交叉的历史。启蒙时代的“内心”观念是对早期现代主体观的延续和回应,它一方面认为人可以通过反思来把握自身意识的“真相”,赋予自我一种完整性和内在性,这种反思和自我对话是知识的来源,也为人的社会性交往和公共领域的缔造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也深刻意识到个体与环境之间在生理、社会层面的种种龃龉,对个体拥有自主而自为的“内心”观念进行修正。启蒙时代“真实”与“内心”观念的内部张力和复杂性体现于现代小说起源的过程。现代小说秉承并发展了早期现代欧洲罗曼司和短篇小说的叙事手法,与同时代文化和社会思想持续对话,不仅发展出许多肯定和描摹“内心”的叙事手段,也同时不断将“内心”放置于流动的社会环境中,说明它无法真正具有内在性的特征。
在西方现代小说“起源”的叙述中,“小说”(novel)与“罗曼司”(romance)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问题。“现代小说”之所以在18世纪成为一个叙事范畴,是基于它与盛行于中世纪并在17世纪欧洲复苏的罗曼司体裁之间的差异。小说(即“新故事”)这个名称预设了与取材历史传说的罗曼司的距离。然而,罗曼司包含多种风格,其内部有很大的张力。堂吉诃德阅读的那些长篇罗曼司,有些在小说中被烧毁,有些则被保留。被烧毁的包括典型的骑士传奇,如众多模仿阿马迪斯风格的充斥魔法与离奇故事的拙劣之作;而田园或史诗风格的长篇叙事作品,如塞万提斯自己的《伽拉苔亚》(La Galatea, 1585)和埃尔西利亚的史诗传奇《阿劳加纳》(La Araucana, 1569—1689),则受到称赞。它们与骑士传奇不同,承接的是西方罗曼司的另一支流,即由古希腊史诗和长篇散文叙事所开创的英雄罗曼司传统。在这些作品中,主要人物品性高洁、情感真挚,虽然经常被瞎眼的命运女神(古希腊语中的Tyche和拉丁语中的Fortuna)玩弄,但还是能在几乎不可能的挫折和考验中坚守本真。因此,18世纪兴起的现代小说与罗曼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小说何以成为小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从罗曼司到小说的转折不仅是文学史内部的变迁,也与早期现代欧洲文化观念转型互为因果。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崛起的现代西方小说见证了早期现代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叙事体裁的嬗变、周转与融合,也是启蒙思想和文化发生、发展的场域。已经有众多批评家从各自角度出发分析有关现代小说形成的历史动力和条件,这些不同叙述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亟须仔细整合、梳理,以此为基础重新阐释小说兴起的文化史和观念史。
在贝克(Ernest Baker)的《英国小说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Novel, 1924—1939),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1957),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的《叙事的本质》(1966),斯泰维克(Phillip Stevick)的《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 1967),肖尔沃特(English Showalter)的《法国小说的进程》(The Evolution of the French Novel, 1972)等专著之后,又有戴维斯(Lennard Davis)的《事实性虚构》(Factual Fictions, 1983),麦基恩(Michael McKeon)的《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1600—1740, 1987),亨特(J. Paul Hunter)的《在小说之前》(Before Novels, 1990)等第二波有关现代小说起源的论述,随之还有很多专题研究在不同维度上深化讨论。黄梅的《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2003)是国内梳理西方现代小说起源的经典之作,将小说与主体的诞生相连,为今天进一步探讨小说兴起的复合语境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纷繁的既有研究中整理出两条主要线索,用以重新阐释西方现代小说崛起的历史。一条线索强调现代小说呼应现代科学精神,建构了实证性“真实”,在素材上取自同时代生活,手法上具有反思或反讽的功能,这条线索经过几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已经得出了一个共识:现代小说的真实性不仅仅指涉现世生活,与罗曼司相比,小说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划出一道更为鲜明的边界,随后又将两者糅合,形成了一种以“虚构真实”为主要内涵的叙事文体。另一条思路基于早期现代意识理论和话语的勃兴,将小说放在西方现代性主体观念(即个人“内心”观念)形成的过程中来考察,这条线索还有许多可待发掘之处。这两条线索彼此交织:“内心”观念的出现依赖“真实”观念的形成,只有在人们相信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和情感作为反思对象,并对其“真相”加以把握,才会认为人具有一种自洽而有别于外界、需要受到保护的私人“内心”世界。反过来,18世纪小说的“真实”诉求也有赖于“内心”观念的形成,它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内心”的真实,即具体情境中的人应该如何在情感和判断的层面应对道德戒律的制约,怎样形成新的社会交往规范。
一、 作为文化史关键词的“虚构真实”
我们首先要厘清经常与现代小说联系在一起的“真实”概念。在很长时间里,“真实”概念对叙事作品而言并不重要,叙事作品要么基于代代相传、经常保留真实事件影子的神话或传说,要么是对历史事件的演绎,两者之间没有清晰的区别,也都可能与更为纯粹的虚构夹杂在一起。早期现代欧洲(约15—18世纪)出现了大量直接标注自身真实性的散文、书信、日记、历史、新闻以及纪实等叙事体裁,与实验科学和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中被清晰化的“真实”概念相呼应,催生了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时期还比较模糊的“事实”与“非事实”的分野,也在罗曼司之外孕育出具有真实性的虚构叙事作品[1]。
有趣的是,有明确真实性诉求的虚构叙事最早是以谎言的面貌登场的,这类作品往往假托实录或真实手稿之名,以掩盖自身的虚构性。15世纪和16世纪法国、西班牙兴起的短篇小说、书信体小说通常宣称自己为真实故事,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18世纪中叶。古老的虚构叙事体裁先是借用纪实的外壳证明自身的真实性,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描摹人物及其环境的手法,随后在18世纪逐渐抛弃了纪实这根拐杖,建立起一种与真实似远实近的关系。美国批评家盖勒格(Catherine Gallagher)据此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观点:18世纪出现了一系列“可信而又不刻意使读者相信的故事”(believable stories that did not solicit belief),构筑了一种新的“虚构性”(fictionality),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虚构真实”[2]。虚构的写实小说与史诗、历史、幻想、寓言都不一样,标志着一个新的叙事文类和“思维类别”(conceptual category)[3]。法语文学研究者佩奇(Nicholas Paige)通过大数据算法对1681—1830年的法语小说进行分析,延续并在细节层面上补充了盖勒格的论点。他发现,在18世纪初,小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真实性诉求,试图再现同时代生活的虚构叙事开始在长篇叙事作品中占据主要地位,其中一部分声称是纪实,另一部分明确标注或至少不回避自身的虚构性,这两种虚构叙事在18世纪中叶有大约七十年左右在数量上基本势均力敌[4]。到了18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标注自身真实性的虚构叙事数量激增,成为取材同时代生活的叙事作品的主要形式,这意味着虚构性渐入人心,作者和读者都已经认为虚构作品不必再依附纪实体裁,具有独立表现真实生活的价值。
“虚构性”或“虚构真实”观念的发生至少依靠两个语境。首先,它与作者、读者之间逐渐达成的默契密切相关。现代小说不仅是具有再现“真实”功能的虚构叙事体裁,更是一种崭新的、强调“相关性”(relevance)的交流模式。这种交流模式注重的是文本与读者经验是否高度相关,而并非文本是否符合机械定义的经验性真实[5]。也就是说,现代小说并不仅仅是伊恩·瓦特所说的小说中一系列描摹、再现现实生活的“叙事方法”[6],更是一种让真实和虚拟想象得以并存的交流模式,基于认为读者想要将虚构叙事与自身经验相关联的意愿。法国阅读史研究名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指出,理查逊的小说在18世纪中叶英法读者群中引发了强烈的情感效应,读者纷纷将自己代入小说中的人物。狄德罗肯定这种阅读倾向,特别撰写了《理查逊礼赞》(Éloge de Richardson, 1761)一文,认为理查逊赋予了小说一种新的道德意义[7]。18世纪文学和认知研究学者尊施恩(Lisa Zunshine)也曾对这种以相关性为中心的小说阅读习惯加以概括,即读者虽然明知小说中的人只是“(虚构)人物”,是“站不住脚的构建”,却又赋予他们与自己相通的情感和思想[8]。可以说,18世纪的读者一方面在再现和实证性真实之间做出区分,另一方面又在它们之间构建了相互融通的关系,标志着认知和阅读模式的转折。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在19世纪初提出“悬置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理论[9],认为即便是不合寻常经验的文学元素,仍然可以让读者感觉是真实的相似物。这种浪漫主义诗学观念自然可以一直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信”比(通常意义上的)“可然”更重要的美学原则,但与18世纪形成的新的阅读习惯的形成也有着莫大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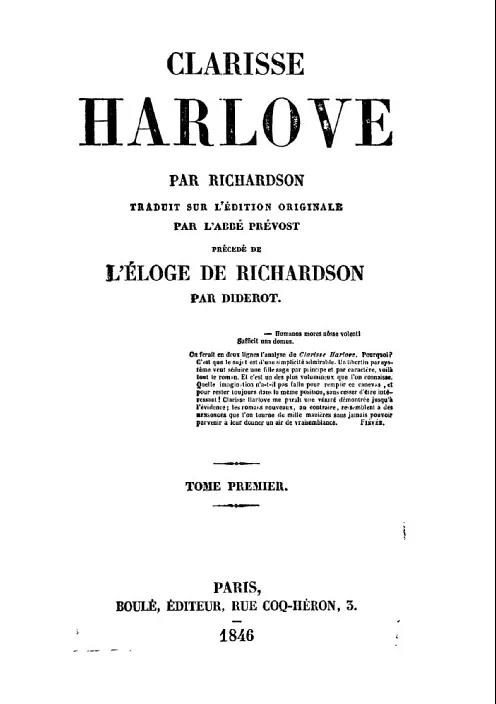
1846年法文版理查逊小说《卡拉丽莎》,附狄德罗的《理查逊礼赞》
“虚构真实”观念也同样依靠现代小说的形式创新。奥尔巴赫提出过一个富有洞见的论点。他认为18世纪的戏剧和小说,如莫里哀的戏剧和普雷沃(Prévost)的《曼侬·雷斯戈》(Manon Lescaut),可以视为一种“中间”体裁,既有很多指涉当代现实的细节,但情节的人为性又很强,套用了喜剧或悲剧的形式,因此与经济、政治肌理交接不多[10]。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深化奥尔巴赫的这个观点。17—18世纪的长篇小说的确具有开创性体裁的特征,也可以称之为“中间性”体裁,它们摒弃古希腊直至17世纪各类罗曼司将小故事松散连缀在一起的叙事套路,开始系统探索构造连贯性长篇叙事的方法。通常做法是,要么使用书信体的多声部叙事来显示不同性别、阶层迥异的认知和情感模式,要么构筑人物网络来表现人性或社会构成的某种规律。然而,虽然现代长篇小说避免程式化结构,试图贴近读者的生活经验,但又不得不大量依靠误解与巧合产生叙事秩序,与传统戏剧中的“机械降神”手法很难区分。这种将随物赋形的新叙事手法夹杂在传统叙事套路中的形式杂糅,也是“虚构真实”观的根基。英国学者卢普顿(Christina Lupton)指出,18世纪作家经常对长篇叙事内含的人为设置进行有意识地反思,倾向于认为巧合和突转代表“随机性”(contingency),它使得叙事引人入胜,但又不与可能性发生明显的冲突[11]。以菲尔丁为例,他在《汤姆·琼斯》第8卷第1章中阐明自己的创作原则,即在“可能性的范围”里勇于展现“令人惊奇”之处[12]。许多18世纪作家都认同菲尔丁拓展“可能性”让其具有随机特点的做法,认为读者不应该因为情节具有令人惊讶的元素而轻易苛责其不合理[13]。坎伯兰德(Richard Cumberland)说过,作者要尽力做到“一方面避免搁浅在乏味的海岸,一方面绕开不可能的岩礁”[14]。
必须指出,“虚构真实”观念的形式内涵,即对随机性与可能性的协调,不是现代小说独自做出的发明。现代小说的形式创新是启蒙时代文化观念转变的一个环节,体现了18世纪独有的对人类个体和社会的理解。18世纪的哲学和生物学经常勾连起生物物种、人类个体和社会机体,将自然界和人类意识都想象为自我构成的系统,没有更高法则可循,充满随机性,但又具有进步和自我完善的态势。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就是这种思想的充分体现,单子是精神性实体的最小单位,任何生命体都可以分解为无数的单子和与其有关的躯体,因此生命体可以视为“具有神性的机器”,从“先成的种子”变化而来[15]。科学领域则出现反对“先成论”的观点,英国和德国的医学界和生物学界都倾向于“渐成论”(epigenesis),提出生物体(包括人体)的结构并非预先形成,而是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观点。18世纪晚期,康德从生物学中汲取养料,将这条思想脉络加以集成,明确提出所谓自然有机体是“自我组织”的机体,具有目的性,但他不像经验主义那样将“自我组织”(sich selbst organisirendes,也译为“使自己有机化”)的特性归于自然界生物自身,也不像莱布尼兹那样将自然机体的发育视为神所预先设定的和谐,而是将其变成人类自我形成和自我组织能力在自然界的投射,彰显人的自由[16]。“自我组织”的概念向我们显示,18世纪西方哲学中一条关键脉络是将基督教思想和经验科学这两种相异的理性加以整合,它肯定经验具有开放性,没有预设的规律,但同时坚持人类个体与社会具有某种由自身所确定的发展态势。既然如此,那么人类个体和社会的真相既属于经验范畴,又具有超验性,可以通过人的实证理性和超验理性的协同运作来认识和把握[17]。
启蒙时代的科学理性与神学理性不断互相吸纳和转化,孕育出人类个体和社会既开放又可以被人自身所把握的观点,与崛起中的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不谋而合又互相影响。所谓“虚构真实”,指的就是用虚构方法描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真实,协调随机与秩序、再现与真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逐步走向现代虚构性和现代写实观的同时,18世纪小说主要致力于呈现个人和社会的“真相”,将个人置于由人、物和环境构成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揭示个体的本来面貌及其与社会状态的关系。这样一来,现代小说中的“虚构真实”观念就与另一个显著特征——专注于呈现人物“内心”和情感——联系在了一起。这两个特征经常被研究者割裂开来,但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紧密的关联。18世纪的研究者对“虚构真实”的信念与认为人的内心可以被人自身所把握的观点互为因果也彼此渗透。
以下两部分集中探讨现代小说与启蒙时代“内心”观念的互动。首先梳理早期现代小说“内心”观的演变,揭示其文化语境和基础;其次说明现代小说“内心观”的直接来源,分析它如何承继并改造短篇小说与罗曼司这两大叙事传统。
二、 “内心”的早期现代史
前文指出,虚构叙事文体早已有之,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经历了现代转型,先通过假扮成纪实作品在“虚构”和“真实”之间划出界线,后又经由“虚构真实”的概念使两者重新整合。同理,探索“内心”也不是18世纪的专利,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早期现代乃至中世纪。如麦基恩指出,“私人”与“公共”这对概念在17—18世纪历经了一个“显性化”过程,彼此之间的界限日益分明,但同时又彼此依赖和渗透[18]。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内心”概念的显性化,“内心”与外部环境之间在概念层面上形成对立而又互相协调的关系。
启蒙时代的“内心”观一般可以这样概括:自笛卡尔哲学开始,人成为知识主体,知识即人头脑中的观念,人可以也只有通过自省和反思来辨认观念是否可靠。这种反思能力基于人与自身观念的直观联系,也依赖理性分析和道德考量。这样,头脑被赋予一种自主和自为的特性,内在于自身,独立于外部环境,可以认识自身,也可以驾驭外物,这种特性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内心”[19]。当然,在启蒙思想的语境中,“内心”虽然独立于外物,但并不因此成为孤立的原子,其缔造也被认为是人的社会性交往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内心”与外部环境之间虽然有一道清晰的鸿沟,但可以彼此协调,人与人之间可以达成和谐一致,在没有超自然力捏塑的条件下凝聚成有序的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内心”观贯穿18世纪哲学、美学和同时代的社会及历史理论。如查尔斯·泰勒所说,启蒙时代认为可以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在其中每个人在为他人的幸福和谐劳作的过程中获得自身最大的幸福”[20]。这也是哈贝马斯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的基本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功能和性质,使之将管理经济和税收作为最重要的职责,限制了国家机器的功能。18世纪见证了由个人权利支撑的私人领域的崛起,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型公共领域,让拥有财产的私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公共事务、参与国家权力。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共同发生和相互作用,锻造出一种可以深刻剖析自身又能与公众沟通的现代主体,同时拥有自主性和公共导向,即“观众导向的私人性”[21]。需要强调的是,“观众导向的私人性”描绘的是18世纪的“内心”观,是理论层面的推测和愿景,不完全等同于人们的实际体验。这种“内心”观折射出18世纪文学、哲学、美学、政治社会理论等不同话语领域对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构建良性社会秩序的设想,构成了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
但启蒙时代不是一个孤立的世纪,哈贝马斯勾勒的启蒙时代的“内心”观并非18世纪突然发生的现象,而是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研究者已经就18世纪之前是否存在类似的“内心”观进行了深入探讨。在18世纪之前,人们已经开始描写个体与宗教、政治、法律以及习俗等外在约束之间的冲突,表达个体具有内在于自身的思想和情感的观念。今天看来,18世纪的“内心”观回应了延续至少几个世纪的思潮,让“内”与“外”的冲突得以凸显并将之调和,提出了兼具独立性和社会性的主体观。启蒙时代的主体观在前现代和早期现代不清晰的主体与现代、后现代时期逐渐被瓦解的主体之间构筑起一道乐观的长堤。
关于“内心”或内在自我的观念在18世纪之前是否存在或以何种形式存在的问题,一般总要提到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格林布拉特1986年的文章《精神分析与文艺复兴文化》富有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精神分析学说是否适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他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现代主体在构建、维护自身连续性和完整性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但这种主体意识直到18世纪才得以建构,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体不过是“一种位置标志符,标志由所有权、亲属链条、契约关系、习惯法权利和伦理义务构成的复杂网络中的位置”,并不具有主体地位[22]。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体只是一个位置,由人际网络和权力关系所决定,不仅不独立,而且缺乏独立的观念。
这个论断问世后引发许多共鸣,也受到诸多指责和修正。格林布拉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自主而自为的“内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刻产生的观念,并不适用于18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史,但他的论断过于强调18世纪与之前时代的差别,割裂了历史联系。早期现代与精神分析理论并没有根本冲突,以弗洛伊德、拉康等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是阐释主体外在于自身(即由外在影响和规训构成)的理论体系,而个体与意识形态的“询唤”(interpellation)或“象征体系”之间的拉锯,贯穿中世纪以来的整个西方文化史。格林布拉特抹杀了早期现代时期就已经萌生的与外界对抗、富有独立性的主体观念。
欧美中世纪学者普遍认为,中世纪时期是否存在启蒙意义上独立和自发的“内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世纪文化相信情感需要操练,情感并不彰显个体独特的精神世界,而是由宗教或政治群体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日常仪式所决定[23]。个人被宗教和社会习俗力量裹挟,没有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作为与环境有一定疏离,具备一定独立性的“内心”观在中世纪文学中还是有所体现的。12世纪,奥西坦语抒情诗和之后的骑士罗曼司很早就开启了西方文学的“内心”传统。传奇中的骑士不断展现愁容和哭泣,执着于所爱之人和个人荣誉,因此产生一种富有歧义的寓言,一方面将爱变成宗教信仰和道德操守的比喻,另一方面以“内心”来对抗宗教桎梏,另立宗教[24]。
同样,我们也可以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内心”层面的解读。莎剧中的人物经常在独白中模糊地表达一种深刻的自省,分析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对个体被孤立却并不独立的困境发出喟叹。这可以举出哈姆莱特对“表象”与“真相”的考辨、麦克白夫人对自身性别限制的反抗、李尔王在多佛悬崖上对自己国王身份的质疑等经典段落。一个更为清晰的例子是卡利班对自身梦境与被莫名“噪音”唤醒的反思(《暴风雨》第三幕),它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阿尔都塞和拉康有关主体受意识形态力量“询唤”才得以形成的理论[25]。莎士比亚研究者汉森(Elizabeth Hanson)就曾指出,文艺复兴已经孕育了一种念头,那就是“内心可以让主体拥有抵抗外界的杠杆力”[26],体现出“内心”受到围困试图挣扎的状态。与之类似的反思声音也层出不穷[27]。
承上所述,我们无法否认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内心”观与18世纪的“内心”观具有连续性。不过,在看到这种连续性的同时,我们还是要返回格林布拉特的论点,考察18世纪小说“内心”观与众不同的语境和特征。经过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时刻,产生于古罗马的“公民社会”概念以新的面貌在欧洲重生。原来表示政治群体的“公民社会”逐渐分化为两种观念:一个是代表世俗政治权威的国家政体,即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一个是由家庭和物质生产、贸易、印刷业等流通体系构成的社会,与国家政体在权力上相抗衡。经过英国内战的洗礼,国家和社会共生并存又相互制约的趋势迅速发展,在18世纪催生了以商业繁荣和独特的公共文化、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为基础,并由国家权力背书的现代国家主义[28]。这个倾向在英国的表现最为明显,也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仍处于绝对君主制下的法、德等国。在这一历史语境下,个体的自主性和内在性逐渐树立,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用文字、戏剧等表达方式在公众视野下表现和塑造自我,同时,这种自主性越来越受到公共文化和国家机器的共同钳制。也就是说,从晚期中世纪到18世纪,西方现代主体逐渐浮现,而其核心悖论——即自主的“内心”与外部制约的冲突——也越发明显。启蒙之所以成为启蒙,在于试图跨越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已经浮现的“内心”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疏离和矛盾,提出在主体与外部环境间加以协调、消解主体日益鲜明的悖论、保证其完整性的设想。
启蒙的主体方案有很多悲剧性的缺陷,但仍有其历史价值。18世纪见证了对“内心”的首次系统阐释,见证了自主而能与他者协调的主体观念的生成。与18世纪哲学、美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一样,18世纪中叶的欧洲小说也反复构想现代性主体,在人物内心和人际关系的描写方面开创了一种动态平衡,使用许多新的叙事手段,让他们内心丰富而具有独立性,又不断被放置于他人的注视和判断下。一方面,文本内部设置了不少对话机制,让人物之间进行私密交流,也让叙事者不断教导读者,或对他们袒露心曲,延续蒙田开创的晓畅而私人化的散文传统;另一方面,这类作品又明显地制造各类“表演”场景,凸显“内心”面对公众并受到他们制约和阐释的维度。小说用新的叙事手段将叙事传统与戏剧表演传统相融合,体现并推动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观众导向的私人性”这个观念的兴起。
三、 现代小说的叙事渊源
西方现代小说与启蒙时代“真实”观和“内心”观有着密切的互文关系,不过两者的关联需要叙事文学史作为中介,西方现代小说是对整个西方叙事文学传统的延续和改造。因此,要了解西方现代小说如何生成,还需要对叙事文学史进行梳理,回顾现代小说如何整合西方叙事传统的许多元素和倾向,并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形式手段来寄寓对“内心”和人类社会的观察和揣测。
从叙事史角度来考察,现代小说从不同源头接收到“内心”书写的基因,罗曼司、短篇小说、来自东方的传奇故事[29]、自传体写作(生命写作)、书信、散文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囊括在现代小说中。概括来说,现代小说延续了罗曼司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又吸纳了短篇小说等早期现代发展起来的新体裁中许多试图折射社会现实和“内心”真相的元素。
先梳理现代(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关联。短篇小说(意大利语中的novela,即“新故事”)最早出现于15—16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这些叙事作品集中于情欲和婚姻主题,尤其关注女性的品德和脾性,成为1500年左右在法国发生的“女性问题”探讨和早期现代女性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30]。这些故事有很多取材自当时的现实生活,即便如薄伽丘《十日谈》改编自流传已久的欧洲或东方故事,也往往是对作者身处现实的回应。法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女性国度之书》(Livre de la cité des dames, 1405)截取西方历史上著名女性的生平片段,来反拨中世纪以来流行的红颜祸水之说,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女性国度之书》名为纪实,但可以说是后来反思女性生存现实的虚构短篇小说的先兆。16世纪晚期,玛格丽特·德·纳瓦勒(Marguerite de Navarre)对这个传统加以发展,借鉴《十日谈》的形式,在1549年左右创作了短篇故事集《七日谈》(Heptaméron),她原本计划写延续十日的故事序列,最后完成了差不多七日。玛格丽特不仅仿效薄伽丘的方式,用一个框架统率所有的小故事,还使框架中的人物就内嵌的女性故事展开辩论,让男性和女性人物围绕女性的美德和本性问题进行争论,揭示女性的情感需求和社会禁忌的冲突,显示不同视角之间的差异。薄伽丘的故事经常赋予女性角色以口才、智慧和强大的欲望,轻易地让男女之争缩减为个人智慧之争,相比之下,玛格丽特笔下展现男女情感纠葛的故事更贴近日常生活,女性也更明显地被赋予做出独立道德判断的能力。玛格丽特去世后,这些故事在1558年得以首次出版,第一版有严重残缺,第二版才恢复手稿中的大部分元素。
多纳文(J. D. Donovan)和麦卡锡(Bridget McCarthy)等英美学者对这段现代小说的前史有过全面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女性叙事写作在17世纪之前一般不以出版为目的,最初大多以手抄本的形式作为礼物传播,但随后通过翻译等方式对公开出版的虚构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31]。《七日谈》传播到西班牙,女作家玛利亚·德·萨亚斯-索托马约尔(María de Zayas y Sotomayor)在它的影响下创作了《爱情示范小说集》(Novelas amorosas y ejemplares, 1637)及其续书《爱的失落》(Desengaños amorosos, 1647)。1654年,英国出版了由科德灵顿(Robert Codrington)翻译的一个新的《七日谈》英文译本,使其影响扩大。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卡文迪许伯爵夫人(Margaret Lucas Cavendish, Duchess of Newcastle-upon-Tyne)的合集《自然写照》(Natures Pictures, 1656)用一系列虚构故事呈现现实生活的不同侧面,延续了《七日谈》代表的以情感世界为中心的短篇小说脉络。
早期现代欧洲的短篇小说将女性德性情境化,不仅回应了薄伽丘以降由男性书写女性情感欲望的传统,也对基督教中的“决疑法”(casuistry)这种叙事和修辞程式用故事的方式加以回应[32],对传统的女性观念和针对女性的道德束缚都发起挑战,也由此开启了现代欧洲长篇小说具有写实性的“内心”探求之旅。法国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的名作《克莱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 1678)和英国女作家曼莉(Delarivier Manley)的《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 1709)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先声,两部作品都受到短篇小说合集形式的影响,并各自做出创新。前者加强了内嵌故事与框架叙事间人物的互动,使之具有了长篇小说的雏形;后者揉进了宫廷丑闻这种同样来自法国、在17世纪尤为盛行的叙事体裁。对“内心”真相的探求不断延续,成为贯穿17世纪末女性作家的“情爱小说”(amatory fiction)、18世纪中叶以理查逊为代表的注重道德品味的情感小说,乃至18世纪晚期泛滥的感伤主义小说的核心线索。
当然,催生了现代小说“内心”写实的叙事传统还有很多,书信体小说[17世纪法国的《葡萄牙修女的来信》和英国詹姆斯·豪威尔(James Howell)的《家常信札》以降的传统],中世纪以来的自传体叙事传统(自传和日记等),还有由《旁观者》等期刊所推广的散文传统,都对现代小说的产生功不可没,催生了许多直接描摹人物“内心”的手法,如笛福的自述体、理查逊的内心剖白体、斯特恩的谈话体、从菲尔丁到伯尼再到奥斯丁的自由间接引语等。人物时而与“内心”交流,时而互相诉说或争辩,也时刻邀请读者的参与和品评。
不过,现代小说的“内心”描摹在写实之外,也受到来自罗曼司的影响。18世纪中叶至末期,罗曼司和新崛起的小说之间的界限一直不太分明,虽然novel一词在英语中已经很常用,但许多作家与批评家,如克拉拉·里弗(Clara Reeve)和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都随意将novel和romance这两个词混用,而法语、德语仍然以roman来表示长篇小说[33]。由此可见,现代小说与17世纪在法国、西班牙等地复兴的罗曼司传统有很大关系。此时,虽然中世纪骑士传奇被普遍摈弃,但古希腊开创的英雄罗曼司却开始盛行,与译介至西方的东方传奇故事的影响相交织,造就了许多用散文写就的、具有理想化倾向的英雄和史诗传奇,以曲折多变的叙事手法(包括倒叙、插叙等)称颂主人公的坚韧和信念。散文罗曼司与短篇故事的分野可以在叙事空间层面上考察,分别体现了欧洲航海探险与殖民扩张背景下全球文化的重构和私人领域的变迁;也可以从“内心”书写的角度来进行区分:罗曼司凸显对于道德和情感的浪漫想象,而短篇小说则注重在现实语境中考察“内心”的写实精神。
以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帕维尔(Thomas Pavel)为代表的一些当代学者曾论述过罗曼司与现代小说兴起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克拉拉·里弗、邓勒普(Johan Dunlop)等18世纪和19世纪批评家最早提出的小说来源于也有别于罗曼司的观点。具有标志性的早期现代罗曼司包括塞万提斯的《波西利斯和西吉斯蒙达》(Persiles and Sigismunda, 1617),贡布维尔(Gomberville)的《玻利山大》(Polexander, 1632—1637),玛德琳·德·斯库德里(Madeline de Scudéry)的十卷巨作《阿尔塔曼尼,或伟大的塞勒斯》(Artamene ou le Grand Cyrus, 1649—1653)在内的许多里程碑式作品,遍布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些作品基本放弃了中世纪骑士传奇中骑士追求功勋、名声的设定,但保留了骑士对未曾谋面或偶然遇见的女士的强烈情愫和比武竞技等元素,也延续了史诗和英雄传奇中主要人物栉风沐雨获得成功的情节模式。它们往往凸显人物的(被遮掩的)高贵出身与美好品质,主人公即使深陷困境,仍然因为勇力与美好品质获得新生:贡布维尔描写加那利群岛国王玻利山大为了追求画中见过的另一个岛国女王而历经考验,一度在非洲成为奴隶,而德·斯库德里笔下以波斯王塞勒斯为原型的男主人公被逐出家园,化名阿尔塔曼尼以兵士身份为自己的叔父效劳,随后又为了营救自己一见倾心的女子四处漂泊;但两人最后都重回高位,并与美人终成眷属。可见,早期现代小说不仅有对人的“内心”加以审视和剖析、以写实手法考察情感与道德规约张力的倾向,同时也具有将叙事情境极限化、对人物进行理想化呈现的倾向,后一种倾向对18世纪的新兴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世纪小说中不断出现约伯受难般的场景,让主人公历经艰险磨难,最后凭借坚韧的美德获得现实或精神上的胜利。这个特点不仅出现在理查逊的《克拉丽莎》(1748)和菲尔丁的《阿米莉亚》(1751),也常见于18世纪后期泛滥的感伤小说,如英国作家索菲亚·李(Sophia Lee)、海伦·玛利亚·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夏洛特·特纳·史密斯(Charlotte Turner Smith)的小说与法国作家李柯波尼夫人(Marie Jeanne Riccoboni)和让-弗朗索瓦·马蒙特(Jean-Francois Marmontel)的小说。
从写实性短篇小说和罗曼司发展而来的两个传统——即私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与英雄游历叙事——在18世纪的欧洲小说中紧密缠绕在一起,因而有很多作品难以简单归入某一类型,而是兼有书写内心“真实”的新颖形式与比较传统的理想化叙事套路,凸显我们之前提到的18世纪“真实”观的两个侧面,一方面尊重和观照开放、复杂的现实,另一方面乐观地赋予其体现某种时代需求的秩序。以情感或历险远行为主题的18世纪小说都同时具有这两个侧面。情感小说通过对私人领域和个体“内心”的描摹构建国家政体的隐喻,因而具备社会与政治批评的功能。用麦基恩的分析来说,18世纪小说中有很多“作为政体的家庭”[34]。但与此同时,它们又总是充满程式化的浪漫想象,将女性变成天然德性的化身和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石,将早期现代以来欧洲女性对性别束缚的批判和质询转化为对中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支撑[35]。以个人游历为主线,在空间上跨地域或跨国的18世纪小说也呈现出类似的双重性。它们经常沾染幻想色彩,把人物推向极限设定,背负沉重的困苦,但其实并不脱离现实,都以自己的方式切近资本主义信用经济、现代国家政体、欧洲殖民扩张等同时代政治议题。感伤小说、异域小说、弥漫惊悚和忧郁情绪的哥特小说等18世纪中后期非常普遍的叙事种类都有影射、批判现实的一面。
罗曼司与早期现代短篇小说这两个叙事传统的交叉融合也与18世纪“内心”观的内在张力相关。18世纪小说普遍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情感小说自不待言,即便是仿照罗曼司的结构原则,以人物纪行串连起各色见闻和小故事的长篇小说也同样注重人物描摹。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不只是串连故事的线索,他们在记录见闻的同时也如货币一样流通,被周遭人解读,曲折地获得自己的价值,同时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与读者直接交流,邀请读者的阐释和情感共鸣。法国勒萨日的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1715—1735)和英国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的《亨弗利·克林可》(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 1771)等作品都有这样的特征[36]。这说明18世纪小说试图协调个人主权与外在限制之间的冲突,与我们之前总结的启蒙时代的“内心”观具有互文关系。这些作品一方面强调私人内心和情感可以被描摹、概括,是由私人占有的财产,另一方面强调私人内心总是向公共流通和交往的领域敞开,不断表演的姿态和话语没有确定的真相,也无法被任何个体完全占有。西方现代小说在延续之前叙事文学的基础上做出重要创新,发展出了凸显人物多维度内心,体现人物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多种叙事和描写手法[37]。
结语
总而言之,西方现代小说的兴起是一个多源头事件,是诸多文化现象的合力所致,也是启蒙时代文化史和观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小说与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美学以及抒情诗传统共同缔造了一个急切探索、书写“内心”和情感“真相”的文化,使现代主体所依赖的“内心”观得以绽放。这个时期,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和社会理论纷纷聚焦“内心”与社会的关系,聚焦向环境敞开的身体感官和灵魂、头脑或主观意识之间的关联,寻找各种途径调和“内心”与他者的冲突。现代小说秉承悠久的西方叙事文学传统,在18世纪全球化语境中对这个传统的不同支流加以糅合和改造,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学体裁。到了18世纪中叶,小说数量众多,形式较为成熟,虽然它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断受到质疑,但已具备对个体意识与社会关系做出深入思考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功能。
不过,现代小说的历史功能和意义很难“一言以蔽之”。它折射的是一个宏大的启蒙梦想,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不论是现代小说,还是其对应的“虚构真实”观与“内心”观,都试图斡旋早期现代欧洲逐渐显现出来的个体与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然而,这个随着现代性萌生不断激化的冲突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启蒙的方案即使在18世纪也已经暴露出很多盲点和弊端,主体在理论层面的完美无瑕遮蔽了现实中不同社会群体被物化、原子化、无(污)名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到19世纪及之后更是展露无遗,引发了很多对于启蒙的批评。如何使不同人群都能有权定义何为主体,探索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成为主体的路径,进而在不同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对话中为人类找到更好的和谐共处的路径,是启蒙思想和18世纪小说无法解决的问题。18世纪的欧洲小说和欧洲文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从内部发出了许多质疑的声音。正如18世纪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在他不太著名的杂志文章《回答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中发出的警示:“一件事物在完美状态下越是杰出,那么当它堕落腐化之时就越为偏颇狭隘。”[38]19世纪,马克思在黑格尔将启蒙所构想的自主自为的个体历史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启蒙“内心”观和主体观的根本性批评,说明它们源于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所创造的“物质的生活关系”[39],也无法脱离其束缚。这个批评为包括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许多有关启蒙思想的研究和批评开拓了一条关键道路。
对现代小说及其写实观和“内心”观的批判自19世纪以来不绝如缕,而延续拓展这个批评的前提是充分了解其复杂的生发和形成机制。今天重提现代小说兴起的问题,就是要说明,西方叙事文学在18世纪发生了重要转折,现代小说与之前之后的叙事传统都有很强的连续性,但仍然拥有许多独特的形式特征和价值取向,标志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时刻。
注释
[1] Cf. J. Paul Hunter, Before Novel: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Fiction, New York: Norton, 1990. 亨特认为小说的起源应该在“一个广阔的文化史语境中”考察,这包括“新闻、流露各种宗教与意识形态方向的说教出版物,私人写作与私人历史等”(Before Novel: The Culture Contexts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slish Fiction, p. 5)。
[2] Catherine Gallagher, “The Rise of Fictionality”, in The Novel, ed. Franco Moretti, Vol. 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 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在2018年的一篇修正性文章《小说兴起论本身就是一种虚构》[“The Fiction of the Rise of Fiction”, Poetics Today, 39:1 (2018): 67-90]中提出另外几种“虚构性”理论,指出这些理论将人们对虚构性的认识往前推至古希腊时期,但弗鲁德尼克仍然基本认同盖勒格的论点。
[3] 盖勒格的这种看法也可以追溯至德国批评家卡勒(Erich Kahle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即18世纪的小说秉承《堂吉诃德》就已经发展出来的一种“象征性”(symbolic)思维,将具体的人物变成普遍人性的象征。这种象征思维与寓言写作不同,以“普遍人性”这个新兴的概念为前提。这种新的“虚构真实”观念也可以说是后现代以“虚拟”为核心的可能世界叙事理论的一种先兆。参见Erich Kahler, The Inward Turn of Narrative, trans. Richard Winston and Clara Wins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49。
[4] Nicholas Paige, “Examples, Samples, Signs: An Artifactual View of Fictionality in the French Novel, 1681-1830”, New Literary History, 48.3 (2017): 518.
[5] 用“相关性”交流理论来解释“虚构性”的做法借鉴自沃尔什(Richard Walsh),参见Richard Wals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ality,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沃尔什借用威尔逊(Wilson)和斯泊巴尔(Sperber)的“相关性”理论,说明交流中“命题性的真实标准”常让位于是否与说话人具有“相关性”的语用标准,因此虚构和非虚构文类的区分并不只是形式上的区分,而是语用层面基于“相关性”的区别。
[6]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页。
[7] Roger Chartier, Inscription and Erasure,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pp. 105-125.
[8] Lisa Zunshine, Why We Read Fictio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
[9] S. T. Coleridge, Literaria Biographia,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 1.
[10]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01.
[11] Christina Lupton, “Contingency, Codex,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 81, No. 3 (2014): 1173.
[12] 参见菲尔丁:《汤姆·琼斯》,刘苏周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297页。
[13] 比如海斯(Mary Hays)为小说《爱玛·考特尼回忆录》(Memoirs of Emma Courtney, 1796)书写的前言和司各特(Sarah Scott)为小说《乔治·艾利森爵士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Sir George Ellison, 1766)书写的前言。参见Christina Lupton, “Contingency, Codex,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 81, No. 3 (2014): 1173-1192。
[14] Richard Cumberland, Henry, Vol. 3, London: printed for C. Dilly, 1795, p. 202.
[15] 莱布尼兹:《神义论》,朱雁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94—496页。
[16] “使自己有机化”的说法取自康德《判断力批判》的李秋零译本(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页)。对19世纪生物学与哲学的关联已经多有研究,参见Daniela Heibig an Dalia Nassar, “The Metaphor of Epigenesis: Kant, Blumenbach and Herde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58 (2016): 98-107。刘小枫也曾根据特洛尔奇的观点,指出启蒙思想,尤其是18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重新给自然设置“精神目的”,但特洛尔奇过分强调了英法启蒙文化与德国启蒙文化的边界(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
[17] 参见Jonathan Sheehan and Dror Wahrman, Invisible Hands: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此书对18世纪的自我组织观念做了重要论述,认为上帝“意旨”(Providence)的概念在18世纪被重写,将随机性和秩序观调和在了一起。
[18] 这也就是麦基恩认为“私人”概念在17—18世纪间经历了“显性化”(explication)过程的论点。参见Mike McKe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Domestic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XIX。这个观点与他在《英国小说的起源》中有关真实和虚构在18世纪分野的观点是同构的。
[19] 哈贝马斯在《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回来:迈向去超验化》一文中的概述相当有用,参见Jürgen Habermas, “From Kant to Hegel and Back Again: The Move Towards Detranscendent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2 (1999): 129-157。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中也对18世纪“内心”观有相似的阐述。
[20] Charles Taylor, “Comment on Jürgen Habermas’ ‘From Kant to Hegel and Back Again’”,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2 (1999): 160. 这是泰勒对哈贝马斯《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回来:迈向去超验化》一文的回应,其中他基本同意哈贝马斯的论述,认为启蒙思想代表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规划,但着重指出不能将其绝对化。
[21]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p. 43. 中译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并未将这个术语完整翻译。
[22] Stephen Greenblatt, “Psychoanalysis and Renaissance Culture”, in Learning to Curse: Essays in Early Modern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16.
[23] 麦克奈马(Sarah McNamer)、萨莫塞特(Fiona Somerset)、罗森怀恩(Barbara Rosenwein)等学者都已经就此做出研究。对晚近中世纪文学情感研究的综述,参见Glenn D. Burger and Holly Crocker (eds.), Medieval Affect Feeling and Emo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24] Cf. William Reddy, Making of Romantic Love: Longing and Sexuality in Europe, South Asia, and Japan, 900-1200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瑞迪认为浪漫爱情与“内心”的萌生与中世纪诗歌传统紧密相连。C. S. 刘易斯早在《爱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Love, 1936)中就提出过类似论点,认为宫廷爱情成为一种信仰,与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产生隐形的对抗。
[25] Christopher Pye, The Vanishing: Shakespeare, the Subject,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
[26] Elizabeth Hanson, Discovering the Subject in Renaissance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
[27] Cf. Carolyn Brown, Shakespeare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New York: Bloomsbury 2015; Carla Mazzio and Douglas Trevor (eds.), Historicism, Psychoanalysis,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Elizabeth Jane Bellamy, “Psychoanalysis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Is it Time to Move Beyond Charges of Anachronism”, Literature Compass, Vol. 7, No. 5 (2010): 318-331.
[28] 英国历史学家T. C. 布朗宁对18世纪欧洲国家主义兴起有过专门论述,将这个过程与公共领域和公共文化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赋予其现代性,但他也同样强调国家主义与民族间的纷争脱不了干系,具有复古特性。他认为英国国家主义是由亨德尔等代表的公共文化与“新教、商业繁荣、权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T. C. Blanning, The cultural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06.
[29] 东方传统的影响可以追溯至罗曼司的鼎盛期。16世纪之前,已经有四大册拉丁文的东方故事,多来自印度和近东,犹太作家阿尔方斯(Petrus Alphonsi)已经从阿拉伯文翻译了33个东方故事,包括《天方夜谭》中的部分故事。
[30] 法国首次发表女性主义言论的女作家玛丽·德·古尔内(Marie de Gournay)深受女性短篇故事的影响,在散文罗曼司《与蒙田先生散步》(Le Proumenoir, 1594)中特意插入一段对于厌女故事的评论,后来又在自己著名的政论文《男女平等》(Egalité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1622)中将这个思想加以扩展。Cf. J. D. Donovan, Women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1405-172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34.
[31] Cf. Donovan, Women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1405-1726; Bridge McCarthy, The Female Pen: Women Writers and Novelists 1621-1818,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32] 所谓“决疑法”,是一种法律与宗教判定法或定罪法,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制定了年度忏悔的教条,由牧师将普遍教义运用于具体情境,裁定具体罪行。参见Edmund Leites (ed.), Conscience and Casuist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莱特斯对决疑法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发展做出过论述,多纳文著作的第五章也对此做出了详细论述。
[33] Clara Reeve, Progress of Romance,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W. Keymer, London, 1785; William Godwin, “Of History and Romance” (1796), in Maurice Hindle (ed.), Caleb William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8, pp. 358-373.
[34] Mike McKe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Domesticity, p. 120.
[35] 18—19世纪小说赋予女性道德权威的同时,又将她们逐渐封闭于私人领域的观点,最初由批评家阿姆斯特朗提出。参见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当代研究18世纪小说中女性地位的学者基本认同阿姆斯特朗的观点,虽然一般会强调女性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有重要影响。
[36] Cf. Deidre Lynch, The Economy of Character and Economy: Novels, Market Culture and the Business of Inner Mea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7] 国内学者中,黄梅最早将18世纪英国小说与“现代主体”相关联,影响很大。参见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页。本文试图将“现代主体”的问题精确到“内心”概念的生产,并与“虚构真实”概念相关联,对现代欧洲小说的兴起做出新的阐释。
[38] Moses Mendelssohn, “Ueber die Frage: was heißt aufklären?” (1784), https://de.wikisource.org/wiki/Ueber_die_ Frage:_was_hei%C3%9Ft_aufkl%C3%A4ren%3F. 这是门德尔松应《柏林月刊》杂志征文启事撰写的文章,康德为同一个征文撰写的文章更广为人知。
[3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关于马克思对启蒙思想的批判,参见刘同舫:《启蒙理性即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12期,责任编辑李松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