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 文化价值核心
歌德的《浮士德》是近代西方文学史上具有总结意义的经典之作。歌德用60年时间吐其心志凝成此作,既借浮士德抒写了个人的人生体验,又通过浮士德描述了欧洲近代人的心路历程和文化价值核心,因此,《浮士德》成了欧洲“近代人的圣经”。[1] 然而,欧洲“近代人”的文化价值核心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有待深入阐释的重要问题。
1
歌德:“渺小”的“庸人”?
“完全的人”?“世俗的人”?
以往我们在评论歌德时,往往引用恩格斯那段对歌德的著名论断:“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的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2] 恩格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指出了歌德身上的“鄙俗气”和妥协性同他的阶级出身之间的必然联系,也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指出了歌德在政治上的软弱性、矛盾性和局限性。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换一种角度,从文化史的眼光,从人摆脱宗教神性的束缚而追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角度看,歌德身上的这种多重性、矛盾性又恰恰是他为摆脱精神束缚,追求人生的多重体验,追求自我人格全面发展,追求人性自由的必然结果。歌德不是一个阶级论者,而只是一个人性论者。这种人性论观念从文化史的发展角度看,是文艺复兴式人的解放、个性自由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体现着十八世纪的理性启蒙精神,因此,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进步的和有积极意义的。笔者以为,恰恰是歌德对人性的这种多重理解,对自我人格之全面性的追求,显示了他在“人”的观念的理解上对但丁、莎士比亚与卢梭等前辈作家的超越。
歌德同时代诗人伟兰认为,歌德“是人性中之至人,”还说,“歌德之所以常被人误解,因为很少人能够有概念了解如此这么一个人。”[3] 那么,何以是“人性中之至人”呢?德国传记作家比学斯基解释说,伟兰的“人性中之至人”指的是歌德“人性之完全”;“歌德从一切的人性中皆禀赋得一分,是人类之最人性的……所以,曾经接近过他的人都说,从未见过这样完全的人。”[4] 拿破仑也称歌德是“一个真正的人”。[5] 笔者觉得歌德之所以能成为人性发展上的“完全的人”和“真正的人”,就是因为他能够独立地依据他所理解的“人”和人生题旨去生活,其间,既要挣脱宗教规范的约束,也要摆脱世俗生活本身的束缚,体验世俗生活的欢乐与悲苦,浸泡在庸俗乃至“鄙俗”之中,据此体味多姿多彩的新的人生体验:
歌德青年时期参与狂飙突进运动,狂热地追求情感自由与个性解放。1775年歌德脱离狂飙突进运动,在魏玛公国当上枢密院顾问和部长,主管公国的文化教育、财政经济、军事、林业,1782年又被任命为宰相。1786年,歌德化名为画家缪勒来到意大利。两年中,他遍游意大利名城,如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罗马等地,欣赏并钻研古代罗马和文艺复兴时的艺术。也是在1775—1786年这十年魏玛的官场生活中,歌德开始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对解剖学、矿物学、骨学、光学、色彩学、植物学、地球形成等都有广泛研究。根据这些研究,日后他出版过《植物变态学》、《色彩学》等自然科学著作。他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形成的进化论思想,曾使达尔文承认歌德是他的学说的先驱。

青年时期的歌德(G.O.梅作于1779年)
歌德一生的文学创作长达六十余年,涉及的艺术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传说、游记、文学与美学论文等多种形式,凡所能运用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手段,他都一一尝试,生活中所能表达的领域与内容,他几乎也都予以表现了。
歌德15岁(1764年)时爱上了友人的妹妹、比他年长的格莱卿;23岁(1772年)爱上了夏绿蒂·布甫,并差点儿因失恋而自杀;26岁(1775年)与法兰克福大银行家的女儿李丽订婚,旋即结婚;27岁(1776年)在魏玛公国与比他大七岁的宫中女官斯泰因夫人相爱,他们的感情保持了十多年之久;39岁(1788年)时与制花女工维尔乌斯同居(于1805年补行婚礼)。除了上述十分确定的情感生活之外,歌德还有多次时间长短不一的爱情经历,直至晚年,歌德仍在恋爱。
总之,歌德的一生,从外在的生活到内在的思想、情感、心理的体验都是十分丰富、复杂而完整的。歌德是按照自然原则而不是按阶级纷争、社会革命的原则去面对并投身生活的;他要让自然人性顺着生活的河流去观赏两岸的风光,进而体验人性的欢乐与悲苦,展示人性的方方面面。因此,歌德的人格展现就显得无限丰富而自然。正如比学斯基所说,歌德的人生“从容自然的像一朵花的展开,像种子成熟,树杆上升,绿叶成盖”。[6] 让人性如此自然地去展示,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的自由观?显然,歌德是要让自己,同时也是让人在一种既无宗教压抑、又无阶级纷争的“自然”氛围中自由地展示人性。因此,歌德在人生观上总是得不到恩格斯的肯定也是必然的。因此,尽管歌德像一个全能的文化巨人,恩格斯还是说:“歌德过于全能,他是过于积极的性格,而且是过于入世的,不能像席勒似的逃向康德的理想去避免鄙陋……他的气质,他的力量,他的整个精神倾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7]歌德很入世以至于媚俗,在此,恩格斯对歌德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问题是,歌德原来就没有想回避即便是“鄙陋”的现实,因为他要追寻的是人性完整、丰满而自由的人——一个世俗的人,而且他最终也成了这样一个人。
歌德像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思想文化“巨人”,不过,这个“巨人”除了在求知的胸怀与气度,在拥有的思想与知识深广度上与文艺复兴时的“巨人”相似之外,还拥有文艺复兴“巨人”所不具备的秉性:他更关注人的自然生命欲望的实现,更关注世俗生活并且直接去体验世俗生活。而推动他去永不满足地追求与体验的内在动力,就是他那不可遏止的自然情感与生命欲望。歌德追寻“完全的人”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追求自然,表现自然天性,实现自然生命欲望的过程。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生命欲望,才能获得对人生的最丰富多样的体验,才能成为“完全的人”和“真正的人”。所以他一生都全身心地游历于纷繁扰怀的世俗生活中,正如歌德少年时的友人雅各比所说:“歌德是个被神魔占有的人,他没有能够自由自主的行动。”[8] 这里的“神魔”即感性欲望,这里的“自由自主”即理性意志。雅各比的话证明歌德是一个顺随人的自然天性行事,向往个性自由的人。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歌德是一个欲望放纵者,而是指他是一个有强烈的自然欲望,并且不断去实现生命体验的人。在现实的环境中,他又常常有理性与感性欲望之矛盾;因而他追求生命欲望之幸福与欢乐的体验,始终伴随着绝望与痛苦。对此,传记作家比学斯基有十分深刻的分析:“只有像这样一个个性结构的人在老年时可以说:他命中注定连续地经历这样深刻的苦与乐,每一次皆几乎可以致他以死命。”[9] 另一位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也这样评析歌德的性格:“既感情丰富又十分理智,既疯狂又智慧超群,既凶恶阴险又幼稚天真,既过于自信又逆来顺受。在他身上有多么错综复杂而又不可遏止的情感!”[10]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无论歌德是“完全的人”、“世俗的人”、“渺小”的“庸人”抑或其他,都与他不可遏止的自然欲望分不开,因为正是这种自然欲求推动着歌德并造就了他完全而复杂的人格,正是那张扬人的生命意志和自然欲望的人文价值观念,使歌德创造出了浮士德这一充满自然欲望而又充满内在矛盾的欧洲“近代人”典型。因此,如果说,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借浮士德表达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知识欲望的时代精神”[11]的话,那么,歌德则借浮士德表达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充满扩张欲望的欧洲社会的时代精神,其内涵相对要丰富复杂得多。
2
浮士德与自然欲望
中世纪的夜,中世纪的书斋,年逾五十的饱学之士浮士德博士,在狭窄的书斋里长期研究中世纪的“四大学科”:哲学、医学、法律和神学,可到头来却丝毫不见聪明半点,产生了无尽的厌烦与苦闷,感觉到“这么活下去啊连狗也不啃!”[12] 长时期地闭门研究这种僵死的“学问”,不仅使研究者远离活生生的自然的世界,而且,这种生活似乎成了窒息自然生命的杀手。对此,浮士德不禁自问:
为什么一种难言的痛楚
会把你所有的生机扼杀?
上帝创造生气勃勃的自然,原本让人类生存其间;
可你却将它远离,来亲近烟雾、腐臭和死尸骨架。[13]
可见,浮士德在书斋生活中感受到的焦虑与苦闷,乃出自长期远离现实生活,出自生机勃勃的生命本原的被压抑和自然欲望的不能实现。早先,浮士德还以为自己是“神的化身”,“与永恒的真理近在咫尺”[14],现在,他明白了原来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卑微,生活是如此的无意义,从而顿觉生命欲望的无法满足。此时,他想到了用服毒自杀来结束这看似无意义的生活。浮士德之“渴望死”,不是因为他万念俱灰,无欲无求,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在意识到既有生活的无意义时生命欲望的骤然觉醒与萌动,因为他依然充满着对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好奇与渴望。继而他把死亡当作生命的新的旅程的开始,他要在新的世界里实现自己对生命的新的期盼:
我向往新岸,当新的一天来临。
一辆火焰车鼓着轾盈的羽翼,
朝我冉冉飞来!我已感到,
准备循着新的轨道冲入太空,
那儿的气氛清新,活动单纯。[15]
所以“渴望死”,是浮士德对新生活的企盼,是对生命存在的不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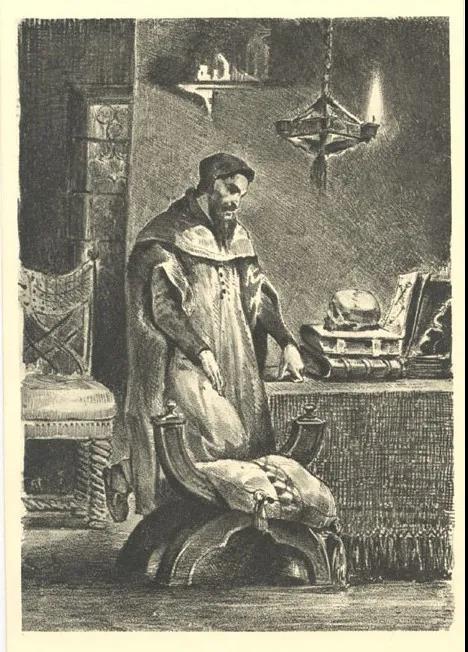
插图“浮士德在书斋”,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827年绘
然而,正当浮士德义无反顾地决定走向死亡、走向新的世界的时候,窗外传来了复活节的钟声和天使们的美妙歌声。从天使的歌声中带来的无疑是基督的旨意:只有历经尘世的磨难,人们才可以沐浴圣恩,进入永恒的彼岸世界。这当然只是基督教教义的一种劝人忍耐的说教。对浮士德来说,这种听起来像福音的说教并不能使他回心转意:“我纵听见福音,却缺少虔信。”[16] 让他放弃死亡,依然执着于现世的是天使的歌声勾起了他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在此,“童年的情感”让浮士德弃死恋生,是耐人寻味的。童年象征着人的原初阶段和生命的自然本真状态。在歌德这里,这种自然本真状态不是卢梭所说的“天赋良知”,“人性本善”,而是无拘无束的自然欲望。这种自然欲望是生命的本真状态,它驱动着人去不断地追求满足,在追求中体验人生,创造人生。所以,以“童年的情感”让浮士德放弃自杀,表现了歌德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原的思想,又意味着歌德肯定了人的感性世界的重要性。
浮士德从“城门前”熙熙攘攘的现实生活中回到书斋后,一方面他的心“豁然开朗”,“又开始渴望,渴望生命的溪流、源泉!”[17] 另一方面,他又“再无满足的快感涌出胸膛”,“重又忍受焦渴”[18],又产生了“渴望死,痛恨生”[19]的念头。此时,最终让浮士德放弃死亡念头的是靡非斯托,具体说,是靡非斯托许给了满足他自然欲望的承诺。靡非斯托知道浮士德胸中充满欲念便企图满足他的欲念从而使他沉湎于感性欲望的享受中,且以此为赌注赢得浮士德的灵魂。浮士德答应了靡非斯托的要求,并愿意跟随他去实现种种欲望:
让我们在感官的深渊里,
去解燃烧的情欲的饥渴![20]
当然,浮士德去实现自然欲望,并非仅仅为了满足感官的享乐,而是在实现自然欲望的过程中体验欢乐,同时也体验痛苦,在体验欢乐与痛苦的双重过程中,感受生命的自由、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实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浮士德说:
整个人类注定要承受的一切,
我都渴望在灵魂深处体验感觉,
用我的精神去攫取至高、至深,
在我的心上堆积全人类的苦乐,
把我的自我扩展成人类的自我,
哪怕最后也同样地失败、沦落。[21]
由此可见,在浮士德这里,感性世界是人的本真世界,自然欲望是生命的起点和动力,因此,人应该如儿童般从自然生命的起点开始,在自然欲望的推动下去感受与体验生命的痛苦与欢乐,去实现完整的人生。这就是浮士德既接纳儿童又接纳靡非斯托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让浮士德弃死恋生的真正内容是被基督教视为“原恶”的人的自然欲望。生命不息、欲望不止,承认自然欲望就是承认生命本身。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歌德的理解中,自然欲望不管是向善还是向恶,都是人之生命的本原,只有自然欲望的存在并不断地运动,才构成了生命的运动,才有人的存在与生命的意义。
3
浮士德与扩张的“自我”
既然自然原欲是人的生命本源,生命的运动凭着自然原欲的力量来推动,那么,实现自然原欲的过程,就是获得生命的欢乐与痛苦的过程,更是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外现与实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就成了目的;每一个人就成了自主自在的独立个体。这是《浮士德》中体现得相当分明的近代人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与斯宾诺莎和康德的理论有着密切联系。
海涅称歌德是“诗的斯宾诺莎”。歌德自己也说:“与我思维方法全体以绝大影响的思想家是斯宾诺莎……就我所知者之中,最与我之思想一致者,要数Spinozu(斯宾诺莎)之《伦理学》罢。”[22] 斯宾诺莎认为,自然界是一切事物统一的基础,从而否定了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否定了上帝的人格、天意天命、外在自由意志和意图对人的作用。“斯宾诺莎的基本思想是将自由和奴役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他的独特的自由概念包含着思维力量的积极运用: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一个积极的、自决的、思维着的人,自由的范式就是由内在决定的意志导出不言而喻的真理。”[23] 斯宾诺莎解释说,自由就在于“将(一个人的)所有欲望和反感整合成为一种协调的行为方式,一种发展他自身的理解力,一种发挥他的能动力量的行为方式”。[24] 所以,斯宾诺莎关于人的自由的观念中,突出的是人的自主、自在和能动性。
康德可谓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勇敢不懈地进行探索的“浮士德”。正是他对人的内心宇宙之复杂奥秘的倾心探索,深深地吸引着歌德。对此,康德从未加以理会,歌德则感言道:“康德从未注意到我,我却走着与康德相似的道路”。[25] 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他认为,“每个理性人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26];人的自由意志不是由外在规律决定的“他律”,而是由道德意志自己来决定的“自律”。在他看来,只是作为手段的人,是他人或自己内外自然的奴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与自由,也就不会具有根本意义上的主体能动性。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心甘情愿地作他人和自然的奴隶,这就证明人终究是以人本身作为目的的,他决不会放弃这一本质。自觉理解到这一点的人就有了自我意识,也才是按人的本性行动的人,才成其为人。受康德思想的影响,歌德自己就是一个按人的本性行动的人,他笔下的浮士德以自然欲望的意志为推动力,更是一个按本性行动的人。
对浮士德来说,他既不会按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意志行事,也不会一味听从靡非斯托的安排沉湎于感官享受,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一个充满自我意识的人。他只在乎现实的此岸世界,而无视超现实的彼岸世界;既不相信上帝的拯救,也不担心地狱的惩罚。他曾经说:
彼岸世界我不大在意,
先把这个世界砸烂,
随后才能有一个新的……
在将来,在另一个世界,
人们是不是也爱也恨;
是不是也分上下尊卑,
对此我一点也不再感兴趣。[27]
因此,就近代西方文学中的人神关系而言,浮士德身上表现了一种更充分的人的解放与自由。他既不像哈姆莱特那样犹如一个刚刚离开“上帝妈妈”的稚童,迷惘与恐惧地彷徨于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也不像卢梭笔下的圣普乐和朱莉,让充满神性的“美德”捆住双脚。而是像一只挣脱囚笼腾空而起的山鹰,俯瞰着世间的一切,贪婪地饱览着人世之盛宴。他说:
让我们投身时间的洪流!
让我们卷入事件的漩涡!
任痛苦和享乐相互交替,
任成功与厌烦彼此混合,
真正的男子汉只能是
不断活动,不断拼搏。[28]
浮士德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去体验、永不满足地去追逐生活的激流。他和魔鬼打赌与其说要的是满足,不如说是意志的自由。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才会是永不满足的人。
浮士德虽然是一个世俗主义者,然而,由于他是在自然欲望驱动下凭生命之自由意志去追求与体验现实生活,体验人类精神的,所以,他的追求和行动,主观动机上通常都无世俗功利意义上的远大目标,也无明确道德意义上的造恶与制善的选择——尽管靡非斯托帮助他总是为了引他造恶。因此,浮士德纯粹是一个自我主义者。浮士德与玛格莉特(又译甘泪卿)的爱情经历,完全是他在爱欲驱动下的情欲体验与满足,而在客观上却造成了无辜的玛格莉特的毁灭。他到宫廷为皇帝服务,并非出自什么政治变革、拯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是寻找一种人类精神的体验。他为一个摇摇欲坠、毫无正义可言的王朝服务,其行为本身亦无正义与邪恶可言,于是就竭尽曲意奉行之能事,尽量满足皇帝与大臣们的享乐欲望,沉湎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之中。这种宫廷生活的享乐没使浮士德感到满足,却实现了他又一种世俗欲望的体验。
移山填海,修造座座村落与片片良田的事业生活,他说出了“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的满足之语,因而浮士德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为民造福,建立理想社会,从“小我”走向“大我”乃至“无我”境界的“英雄”式人物。其实,浮士德移山填海的事业生活,依然是他从“小我”的角度去体验世俗生活,领略人类精神所作出的个人选择。如果在他心目中有什么“大我”,那也不过是他要体验的人类精神的方方面面而己。因此,他由“小我”走向了所谓的“大我”,那就是在永不满足的追求中体验了世俗生活的各种感受,成了一个“完全的人”和自由的人而已。所以,他的“智慧的最后结论”是:
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
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29]
这里的“自由”不是人在世俗权威面前的人身自由,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意志的自由,个体的人的精神独立与自主。拥有这种“自由”的人,能够每天不满足地去体验,同时也在永不满足地去开拓。显然,这“智慧的结论”展现的是浮士德那无限扩张着的自我意识。“自我”的扩张导致了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而这正体现了从传统文明中觉醒过来的欧洲近代人的一种人格侧面。
需要指出的是,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并不等于利己主义。近代西方社会以个体为本位,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范畴的概念,它与集体主义相对。道德范畴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在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中,个人主义或个体本位指每一个体都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同时每一个体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社会的利益建立在个体利益的基础之上(而非一味强调集体、国家而消融个人),且以个体利益为前提,是个体决定社会而非社会决定个体。个体本位是西方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亦为它的终点。因此,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与强调个人利益至上、自私自利并不相同。浮士德的“自我”扩张,是典型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而作为文学形象,如此狂放地张扬个体本位、放纵自我,在近代西方文学史上还是第一个。因此可以说,歌德通过永不满足的浮士德倾吐了欧洲近代人个性解放的心声,传达了初露端倪的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时代精神。这种个人主义以后又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发扬光大。
4
神性和魔性的永恒矛盾
众所周知,浮士德的故事在西方传说中由来己久。在中世纪后期最初的浮士德传说中,浮士德为了得到世俗的快乐和权力,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在文艺复兴剧作家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浮士德在魔鬼的引导下,享受了24年纵情声色的世俗生活,然后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可以说,歌德之前的浮士德,都是耽于享乐而坠入地狱的人物。说明人完全是受自然欲望支配的,只满足于低层次的感官享受。歌德对这一传说则反其意而用之。在他的笔下,浮士德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利用魔鬼的力量体验了人生的欢乐与悲伤,最后却被上帝拯救,灵魂归于上帝,从而说明人有永不满足的自然欲望,但人的本性决定了他最终不会满足于暂时的享乐。在“天上的序幕”中,上帝之所以敢于跟魔鬼打赌,是因为上帝相信他创造的人不会背离自己神圣的本源和目标;而魔鬼这“否定的精灵”则认为人会满足于纯粹而有限的世俗享乐,从而背离自己的本性。在诗剧的第二次赌赛中,浮士德敢于同靡非斯托打赌,是因为他坚信魔鬼永远不能使自己在理智上满足于暂时的快乐,魔鬼的任何魔法都不会改变人的本性和目标。浮士德最后的结局证明了他以及上帝的看法是正确的。这说明,浮士德虽然以自然欲望为动力不断去体验世俗生活和实现自我,但他并非盲目地和麻木地受导于自然本能,而是在受自然欲望之强力的推动的同时,又接受理智的牵引。也正是这种理性意识,使浮士德在每一次满足享乐后又沉浸于痛苦的自责之中,在经过灵魂的激烈搏斗之后,走出精神困境,进入新的境界。浮士德本人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他心灵深处的双重自我:
我的胸中,唉!藏着两个灵魂,
一个要与另一个各奔东西;
一个要沉溺于粗鄙的爱欲里,
用吸盘把尘世紧紧地抱住;
另一个却拼命地想挣脱凡尘,
飞升到崇高的净土。[30]
浮士德要纵身于“新生活”,就是既“把尘世紧紧地抱住”,又拼命地“挣脱凡尘”。强烈的自然欲望往往使他易于接受魔鬼的诱惑,不顾一切地追求尘世的享乐,甚至破坏、造恶也在所不惜,他身上就时而显露出魔性特征。但如上帝所说:“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31] 浮士德之所以是“善良人”,是因为他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在拥有魔性的同时又拥有神性,因而他总是在享受了凡尘的欢乐后飞升而向更高的境界。神性与魔性构成了浮士德心灵深处两股“各奔东西”的牵引力,也播下了他永难排解的心灵冲突的种子。
这更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智慧的结论”告诉我们,它就是“自由”。是既顺应自然欲望又不丧失理性约束,这两者的和谐统一,也即灵与肉、理性与原欲的统一,它体现了人性的和谐,因而符合人的生命原则,在终极意义上是对人的一种善。浮士德最终认可了这样一种人生的最高目标,在感到满足后灵魂归属于上帝。这说明上帝并不要求人们只生活在宗教式的精神沙漠中,放弃尘世去追寻彼岸世界,而是认可了灵肉统一、世俗与信仰统一的世俗人生。但这个“上帝”已不是原本基督教中的上帝了,而是歌德心目中富有人性、世俗化了的近代人的“上帝”。此外,剧中的“上帝”认可这样一种和谐统一的自由人生,而这种人生本身需要人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理智地把握好灵与肉、理性与原欲的关系,因而这又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正如康德所揭示的,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二者处于永恒的矛盾之中,道德的崇高永远是在扼制自然欲望中实现的,因而,灵与肉、理性与原欲的统一、人的完全而恒久的自由永远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所以,浮士德满足于这种自由的境界,实际上又意味着永远的不满足,或者说,他“满足于永不满足”。因为,从与魔鬼的赌赛来说,浮士德是一个胜利者,这是一个喜剧,他因此而满足;而从他的终极目标来看,浮士德依然处在永远无法满足之中,他又是一个失败者,这是一个悲剧,而这也就是人性的悖谬,人的永恒矛盾。
5
结语
浮士德是一个在自然欲望推动下不断追寻新的生活体验、不断追求生命价值、个体本位和原欲型的人物形象,他复活了古希腊、文艺复兴前期的世俗人本意识。[32] 他那永无止境的世俗化追求精神,体现了从信仰时代的宗教阴影中走出来的近代欧洲人的精神特质;他那扩张的自我和强烈的自由意志,预示了个体本位、个人主义的近代欧洲新价值观念的形成,预示了一个充满探索与创造欲、充满自由精神与个体意识的时代的来临。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浮士德》表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人文观,还预告了一种更为张扬个性、放纵自我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即将来临。
不过,浮士德身上虽然涌动着古希腊一罗马式的原欲型世俗人本意识,但他毕竟无法完全涤净其精神血液中的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基因。因之,浮士德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并不一味地在自然原欲的驱动下走向原欲放纵式的绝对“自由”,而是在理性意识的牵引与制约下不断地向“善”的境界提升。而在这个过程中,浮士德的内心深处也就始终存在着原欲与理性、善与恶、灵与肉、社会道德律令与自然欲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存在着“两个灵魂”的反向运动。他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种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自由的境界。因此,浮士德的个人追求始终散发着浓厚的道德意识和理性精神,这种道德意识与理性精神的文化血脉是与希伯来一基督教人本传统相联结的。浮士德心灵深处永难排解的善与恶的矛盾,正体现了欧洲近代人在强调张扬自我、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创造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人的道德理想与理性精神的追寻。而肯定并顺应人的自然欲望、追寻世俗生命价值的实现、个体本位、崇尚自我,同时又身陷理性与原欲、善与恶、灵与肉的永恒矛盾,构成了欧洲“近代人”文化性格和价值核心的基本框架。
[1]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56页。
[3][4][6][8][9]比学斯基《歌德论》,见《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7、67、71、71、70-71页。
[5]刘易士《歌德的生平与创作》,转引自《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71页。
[10]艾米尔·路德维希《歌德传》,甘木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
[11]Harry Levin , The Overreache: A Study of Christopher Marlowe, London: Faber and Faberd Limited,1954, p. 45.
[12][13][14][15][16][17][18][19][20][21][27][28][29][30][31]歌德《浮士德》,杨武能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21、33、36-37、40、62、62、81、90、90-91、85、90、670、56、18页。
[22]歌德《诗与真》,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第134页。
[23][26]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51页。
[24]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XLVI, 1960,p. 213.
[25]转引自徐葆根《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32]参阅蒋承勇《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对立与统一》,《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12期转载。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