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深受感动也是一种信心 ——访作家刘醒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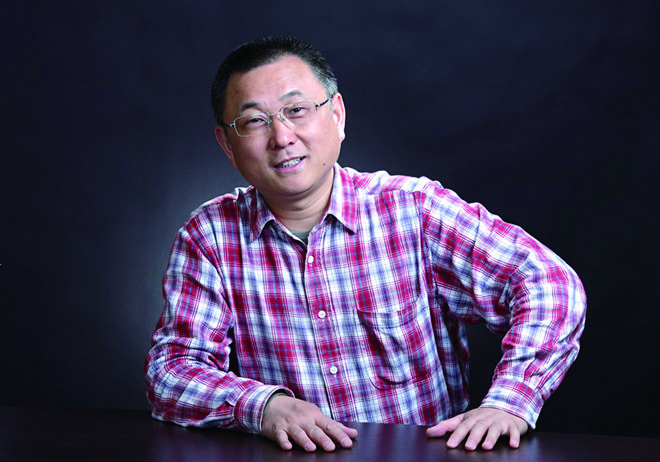
文 羽:我看到从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您就一直充满信心,从您在各个渠道的表达来看,似乎没有低落过。事实是这样的吗?您是否也有犹疑、情绪的低落?
刘醒龙:说自己情绪没有低落过是在硬充好汉,肯定不是心里话,只要人在武汉,遭遇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我一向睡眠很好,疫情期间却经常失眠。平常总想着减体重但总也减不下来,那时候吃饭没办法挑肥拣瘦,体重掉了三公斤。疫情开始时自己就患眼疾,后来变得日益严重,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人都是血肉做的,别人有的情绪我也都有,比起来我或许只略多一些自律和自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在家里我是爷爷,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是男人,这是与生俱来的,更是一个人从小到大所能领会的教养。
至于信心,人生本当如此。我理解的信心,无非是真诚面对眼前的生活,尊重努力劳作的自己与他人,不浮肿,不虚脱,为自己能够完成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而开心。我生性易受感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那么多人主动支援武汉,我深受感动。有时候,深受感动也是一种信心。
文 羽:我看到您当时在朋友圈里说,您的家人也有在抗疫前线战斗的,能说说他们的故事吗?
刘醒龙:有些事做了也就做了,没必要多唠叨。千家万户全都在一线抗疫,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不过有两件事还是值得一说。一是孩子在新闻单位上班,轮休时就在小区当志愿者。有一次孩子生气了,因为有人在自媒体上说,志愿者是假的,孩子便回了一句,今天我们几个女的卸了整整一车白菜,就因为没有送到你家门口,你就当没看见吗?另一件事,刚好相反,夫人当志愿者,送青菜和鱼去一户残疾人家,男主人伤残很严重,平时都不起床,却非要让家人搀扶着,走到他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们非常感激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支援,10月10日去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与很多专家学者见面时,我只开口说了一句,感谢山东人民对我家乡黄冈的支援,就泪流满面说不下去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自己因为眼疾当不了志愿者,但也做了些事情。武汉降为低风险地区后,有新冠肺炎患者家人给我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我借故没有见面,就放在湖北省文联办公室里,至今也不好意思打开看。有人建议送给抗疫博物馆,我也不想那样做,那会更加不好意思。人做一些分内之事,多半是为了求得心安。那时候,我听说有一个家庭四个人确诊,剩下一个小孩还在发烧,就试着帮一帮,没想到帮成了。做这种事,对自己也是一种鼓励。
文 羽:近年来,从《蟠虺》《上上长江》,到《黄冈秘卷》《文学回忆录》,您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堪称一位勤劳的创作者。现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刘醒龙:疫情之后,我开始时零散写了点文字,有访谈,有随笔。也写过一首歌词《如果来日方长》,被谱成曲后,反响还不错,自己索性将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重新构思写成一部18万字的长篇散文,篇名也叫《如果来日方长》。这之后,我最想做的事是先治好眼疾,虽然眼科专家表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好转概率,但自己还是挺乐观的。我也不允许自己不乐观,因为一直想动手的《青铜三部曲》之二正等着我去写。
文 羽:您作词的《如果来日方长》里面的“花不开、酒半杯”,背后有什么故事吗?您当时写这个歌词的创作情况是怎样的?
刘醒龙:夫人的一位朋友年年春节都会提前寄来水仙,正好在过年时节开花,水仙的清香特别淡雅,有天然的春天气息。今年春节收到水仙后,养了多时也不见开花。《如果来日方长》谱成曲唱开后,有几个朋友说,原以为只是自己家里的水仙不开花,没想到你家的水仙也不开花。有一个朋友,当医生的女儿要上一线了,他拿着酒杯说是给女儿壮行,只喝了一口就再也喝不下去,背过身去,落下的眼泪,反而比喝下去的酒还要多。疫情之下,花且有灵,何况是人。朋友一家后来全都安好,对于这两句歌词,我们从不触及。人心之敏感,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有很多。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将这首歌与战疫期间亲手拍下的各种图像一起做了一个短片,用于自己医疗团队的一个活动。她在微信里只说,同事们都觉得这歌真好听!我当然晓得这些话是不能说第二句的,便只回复了“谢谢”二字。因为再说下去,必然是泪如雨下。
文 羽: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知道您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停止写作,这一年来,关于文学,关于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您有没有一些新的思考?
刘醒龙:我曾说过,文学不是直接站在潮头上弄潮,而是从潮头上退后半个身位,不与即时报道的新闻争宠,用更加厚重的观察和更有体系的体验,重建这股大潮的艺术形象。前两年,在一个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上,莫言谈了一个观点,什么都可以快,唯独文学应当慢下来。那个活动由我来做会议结论,我强调了莫言的这话,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我曾感慨文学苍白无力。甚至现在,我也还是觉得最初那些铺天盖地的文字,只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元素,并不是文学本身,只有一次次对支援武汉的人们表示感激的句子,过后读来似乎还留得住。彼时的文学,找不到先贤留下来的现成经验,更不知能给后人提供哪些风范。在长篇散文《如果来日方长》中,我虽然写了几位在火线上“自我提拔”,以卑微的身份担起巨大职责的医护朋友,但我依然觉得,这不过是身陷火线的我们,用相对一手的文学元素,给未来的某种文学作些预备。所以,我尽可能完整地写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比如,我熟悉的一位护士长,55天没有与幼小的孩子见上一面,每天在电话里互诉相思。好不容易从隔离病区出来,走到家门口,孩子却躲在门后,用发自内心的声音,奶声奶气地不要妈妈进屋,说妈妈身上有病毒。母亲也不让她进家门,隔着老远递上几样她最爱的美食,她就在门外的楼梯间里蹲着吃完后,转身重回医院。这样的人性该怎样审美?这样的亲情该如何抒发?有一句话说,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即便文学有时不是朗月,也不是骄阳,但如果它能化为满天星光也是好的。
文 羽:经历过这样特殊而难忘的一年,您对文学的认识是否有改变呢?
刘醒龙:武汉战“疫”,国家在,政府在,人民在,文学也在,文学中的自己也在。对于新冠病毒我所知甚少,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我也知道得不多。实际上,在家里每每谈及这些带有专业性的话题,六口人中,我所了解、所能认知的,排名倒数第二,只超过8岁的小孙女。我只想说,经此一疫,世人更应当明白,文学不是以作家身份进行创作,必须是以人的身份进行再造。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现。
文 羽:在您看来,文学写作者在历史面前,应该担起怎样的责任呢?您与其他的同行朋友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刘醒龙:人在危难之际,首先想到的总是最熟悉的人。在文坛几十年,手机里保存下来的两千多个联系人,多半是与文学沾点边的。年初之时,总想着对有困难的朋友能帮就帮一下,竟然得到了那么多同行的支持,想来只有一句话才能解释:同舟共济,相互信任。文坛很小,其间三六九个人,大都耳熟能详。文学很大,大到高山仰止,海阔无边。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我深深信任这些全力做好每件小事的同行,就像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靠大话狠话就能写出来一样。做好力所能及的小事,写好身边的普通人,才是行稳致远的唯一正途。
文 羽:对您来说,武汉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刘醒龙:那还用说,就是生活与存在。
文 羽:4月8日武汉生活恢复正常,我看到您去江汉关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您的所思所想是怎样的?
刘醒龙:那天凌晨零点一到,我们全家人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夫人和孩子们有没有落泪,我顾不上看,松开手臂后,赶紧去卫生间,一边擦干净眼泪,一边剃去胡须。剃完胡须,家里人仍旧待在客厅里,一点睡意也没有。大约零点三十分时,才突然起了去江汉关看看的念头。我们到江汉关时,已是零点五十分,临江的街道旁有不少年轻人,在那里一次次腾空跳跃起来,让同伴用手机抓拍。那一刻,自己突然想起,1948年春节前,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对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的抓捕,在汉口一家布厂当工人的父亲正是从江汉关码头上了小火轮,逃回黄冈乡下。江汉关一带是我们经常来的,以往从来不曾如此联想过。我还想到1990年春节过后,自己在江汉关前与一位作家兄长握别,没过多久,那位兄长就病逝了。从古至今,江汉关一带由于是大码头,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别离。这么联系起来一想,2020年4月8日凌晨,大家都去江汉关,不就是送别那个时常跳出来对人类进行一场全方位大考的老对手?
文 羽:这一年您所目睹的、所经历的,会对您未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刘醒龙:加缪的《鼠疫》中有一段话:“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儿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反过来听,这话里有鼠疫将琐碎生活放大的意思。前阵子,也是感慨这一年过得太不容易,将自己十几年前的一段旧话写成书法:庚子去,辛丑来,春秋已经轮替,世界还在疫海沉浮。因为现在我们的平静,更要晓得文学的使命是描写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发生之时,人所展现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爱;文学的任务是表现这个世界的种种荣光来临之前,人所经历的疼痛、呻吟、羞耻与挣扎。
文 羽:如果在多年后回望2020年,这一年对您来说会是怎样的存在呢?
刘醒龙:用《如果来日方长》中的一句话说:疫情是一面很特殊的镜子,照出来的人间百态,没有一样是特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