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文学史的纵贯与学术精神的融合

杨义,1946年生,广东电白人。1965—1970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1978年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当工人、宣传干事。1978-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2000年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1年毕业后留文学研究所工作,1985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89年破格晋升研究员。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学位获得者荣誉。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文学年鉴》主编。2003年为英国剑桥大学客座教授。2004年出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2006年获评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2009年当选为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2010年任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座教授。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诸子还原”四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此后又出版《论语还原》多种。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文学地理学会通》等数十种。另有《杨义文存》(7卷10册)。
贺仲明:杨老师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畅谈您的学术经验和学术思想。或者先从您最近一些年的学术经历谈起?
杨义:社科院文学研究院所长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个所长我当了十一年,刚刚退下来,就被澳门大学特别聘请了讲座教授这个位置。澳门大学是一个做学问的很好的平台,它思想开放,中外思想在这里交融。另外,校长没有设置太多限制,我可以按照自己研究的观念、基础来设计题目。到澳门之后,我进入了自己学术上的黄金时代。我研究“先秦诸子还原”,包括“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后来还专门在北京开一个发布会,大家觉得这是研究先秦诸子的一个新思路。然后我进一步在做的是《论语还原》,引起广泛的注意,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著作的一等奖。之后做“兵家还原”,对春秋战国时期和兵学相关的文献做了梳理,还原了八个兵家,还原的是《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孙膑兵法》、《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张良素书》,写了一百七十多万字,共六卷,已经获得了国家后期资助。评审专家对这个研究的评价很高,因为它对建立中国军事科学的体系不但有历史价值,还有当代价值。我们过去的研究往往用是一些战例来说明兵法,这对普及兵法知识有很好的帮助,但这并不是一种还原的研究。在还原的研究中,我研究这些兵家是谁,他们的兵法是怎么产生的,含有哪些家族文化基因,汲取了哪些思潮推涌的因素,因此比以前的研究要更深入,更触及本质。
贺仲明:刚才您谈了近期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从现代文学延伸到古典文学,打通了文史哲,成就非常大。从现代到古代,从文学到历史、哲学,您在研究过程中肯定发现了其中的内在关联,可否分享一下您的经验或体会?
杨义:我要探索中国文化的精神,探索它的原本和它后来的血脉。你要做这种研究,若从现代文学开始的话,必须要续上古典文学。我在现代文学领域做了现代小说史研究,当时读了两千多种原始的书刊。接着想对小说内在的规律、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进行探讨,研究小说学。后来我到牛津大学访学,读了西方的叙事学,有许多启发。我做过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古典小说史论研究,这两个部分我大概读了三千多种中国古今的叙事文献。我再看西方的叙事学,觉得它不能涵盖中国叙事的精髓、核心,所以我形成了一个中西的对话。当时我的思路一是返回中国的原点,从战国、秦汉一直到唐宋的文献中看中国人如何看待叙事;二是参照西方理论,看西方人如何看叙事;通过贯通古今文史来融合创造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和学理体系。这就是我做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现在《中国叙事学》的国家外译工程已经下来,可能两年之后这本书就翻译到伦敦一个权威的出版社出版。
我研究了小说之后,觉得若要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只有小说是不够的。诗文在我国古代占据了更核心的位置,所以我又做了古代诗学的研究,包括《楚辞诗学》、《李杜诗学》。诗文研究之后,我当了社科院两个所的所长,当了十一年,跟大家一起深入学术脉络进行研究。接下来我对少数民族文学,例如对《蒙古秘史》、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问题。从空间的位置上来说,中国文学地图的绘制,如果只讲汉族文学是不够的,必须要把少数民族文学加进去。我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边缘的活力”。这是一种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在当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时候,我认为要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根本,不能离开先秦、经学和诸子学,所以我转而研究先秦、经学和诸子学,可以说我是逆着时间往上走的。不过后来我又重回鲁迅,研究鲁迅和金石学的关系。我的研究都是采取古今贯通的方法。中国文化精神的原本、血脉的状况如何,必须通过研究来梳理。
在研究过程中,还要着重解决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根本问题。我们过去从思潮的角度来看问题,现在我们用现代大国的文化建设这样一个宏大的视野和全球的思想文化进行对话。那么,用这样的视野应该怎样看待古代的问题?所以我在先秦诸子里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孔会,孔子向老子问礼,这是先秦诸子的开幕式。老孔会之后,老子的道、老子传授给孔子的礼、孔子以仁和孝改造过的礼,成为中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最基本的核心的问题。老孔会到底何时发生?经过我的考证,《史记·老子列传》基本上讲了老孔会和老子著道德五千言。《史记·孔子世家》里也有大段记录孔子去见老子的话。过去我们往往否定有老孔会,但实际上这在《史记》的《老子列传》和《孔子世家》中都有大段的描述。这是历史公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不能不解决。孔子向老子问礼,在《礼记·曾子问》里面,孔子反复说:“吾闻诸老聃云。”意思就是我听老聃是这样说的,对礼的问题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再根据《礼记·曾子问》里的一条史料,即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时候,他跟老子一起到洛阳出殡,途中遇到日食,老子告诉孔子,出殡遇到日食的时候应该停下来等日食过去再走。那么,根据日食发生时间的诸多考证,我们确定应该是在孔子41岁的时候,即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当时周历是十二月初一,公元新历是11月16日。而且根据现代天文学来重现那次日食,可以证明发生时间是上午9点56分。按照礼俗,周人上午出殡,把尸体埋下去之后,还要把灵魂迎回宗庙,日中而虞。所以那时是在上午遇日蚀之时,十点左右,不然赶不回来举行把灵魂迎回宗庙的虞礼。这是根据《周礼》,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来解经。经过这样的解读跟考证,我们可以得知孔子向老子问礼是在公元前511年冬。老子向孔子传授礼仪,孔子接过来之后又用仁和孝的基本观念来解释礼仪,这成为了春秋战国三百年诸子百家争鸣的源头。
诸子百家争鸣的闭幕式应该是荀子、韩非、李斯三个人的师徒会。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都知道荀子收了韩非、李斯两个徒弟,但是他什么时候收的徒弟,收徒弟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我就对这个进行研究。有一条材料,就是荀子到齐国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荀子观察天下,发现秦统一中国用的是一种法家的思想,缺乏儒家的东西。他去见应候,但是后来应侯被穰侯取代,所以荀子没有实现他的目的。他到秦国去见应侯,秦国跟齐国是敌国,所以他在稷下待不住了。后来春申君就把他招去当兰陵令。当兰陵令的时候荀子有个理论,就是商汤王、周文王有七十里地,如果他们整个思想正确的话,就会得到全国的政权。当时有人不认同这种理论,说荀子坏话。于是春申君把荀子解雇,荀子回到了赵国。后来有人在春申君面前为荀子说好话,说有才能的人还是得把他招回来,于是春申君重新招回荀子。荀子在回去的路上写了一篇文章,叫《疠怜王》,文章大意是说生麻风病的人都可怜国王,国王比生麻风病的人更不好受。同时我们发现在《韩非子》里面也有《疠怜王》这篇文章。过去的老先生在考察这件事情时,肯定《韩非子》的《疠怜王》是真的,而认为《战国策》的《疠怜王》安在荀子头上是错的。实际上,有三种可能。一 、二者一真一假。二、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他把老师的文章抄了作为自己的学习材料。三、荀子让韩非子给他起草,荀子修改之后寄出。我把这两个文本进行考察,提出了五条理由,认为《战国策》的《疠怜王》是荀子让韩非子起草,荀子加以修改之后记存的。它们都是真的,是过程中的真,不同层面上的真。实际上,在编《战国策》的一百多年前有一个《韩诗外传》。《韩诗外传》把这个专利权给了荀子。如果 “荀子让韩非子给他起草,荀子修改之后寄出”这个考证是对的话,那么韩非子回到赵国时,从韩国的首都经过,韩非子就在他的门下。
这是公元前231年,韩非四十多岁。他是韩国诸公子之一,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所以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不可能整天跟着他的老师,必须国家首都待着,谋求进入政权的中枢。李斯这时二十多岁,正好是学习的时候,他经常在荀子身边,在荀子的书中就有两段荀子和李斯的对话。李斯于公元前247年告别荀子入秦。荀子、韩非、李斯的师徒会,共有7年。这就是诸子百家争鸣的闭幕式。这时的荀子是儒家大师,但他的儒家和孟子的儒家不一样。荀子是赵国人,我们知道赵国的王霸思想很浓,所以他是黄老道的思想。韩非是法家,但黄老道的思想使韩非的法家思想更深邃。《史记》说韩非是法家,但是归本黄老。过去都问什么是归本黄老?其实我们把整个战国时期的思想史都贯通起来就可以知道,黄老思想就是老子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整合。法家思想后来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思想武器。
中国思想最后的奠定,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刘邦入关之后,萧何把秦国的地图、韩非子的著作搜罗起来。汉承秦制,它是带着法家思想进来的。同时它又是楚人北上,是楚国思想的北上。后来曹参入朝,以黄老治国。最后是儒学,董仲舒独尊儒术。所以到汉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变成了综合的意识形态,这使汉代国力大增,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国。我就是这样去追踪中国思想的源头。
贺仲明:您的思想研究已经超越了文学进入大文化的层面,非常恢弘、深刻,具有很大的价值意义。您年轻时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们当时都买来看了,觉得写得非常好。这套书在学界的影响也很大。不知您如何看待您当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了我做学问的方法和基本思路。方法就是从文献入手,阅读大量文献。我在社科院的图书馆读文献,发现郑振铎、何其芳把民国时期的小说搜集得很全,比国家图书馆还全。各个图书馆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做出中国现代小说史,和能利用社科院图书馆把现代小说都过一遍有关系。当时有个学者问我,说中国现代小说可读的不多,怎么你都要把它读一遍呢?我说,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两个人把它都读一遍,才能发现其中的精神脉络和奥秘。我深入文献,从文献中浮出思想。写小说史必须分章节,我按照读书时对问题的感受进行划分,出现了文学地理学的维度,比如京派和海派、东北流亡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华南作家群,这是用了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这些基本的思路,形成了学术研究的能力。我再去研究古代、先秦诸子的维度时,这些思路都在不断地发生作用。另外,我当了十一年文学研究院所长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学者晋级或学者著作评奖,都需要通过学术委员会讨论。学者在评奖时会把他研究中最精彩的思想和方法讲出来,让大家来投票。通过这个评奖过程,我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思想方法。所以,我现在处理文献的时候能够运用各种思想方法来进入它的脉络。还有就是自己积累下来的材料。到澳门后我进入了自己学术的黄金时代,因为这时的我具备了文献、材料、跨学科的视域和解决问题的各种思想方法。
贺仲明:这是因为您具备了非常好的学术视野,才可能广采博取,不断深化和强化自己。而且,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过程中付出了过人的努力,很让人敬佩。当您在今天回顾自己的治学经验,您觉得一个学者的成功,“智慧”“勤奋”“机遇”哪一个最重要?或者还有其他您觉得很重要的因素?
杨义:人文学术的创新,中国文化精神的锲而不舍的探寻,成为我的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里,有一个学者的历史担当,有一个学者的生命智慧的投入,也有现代大国学术文化的时代要求。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家学渊源,不会察言观色的人而言,无疑也是一种挑战。我在1998年—2009年由一个普通的研究员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两所所长11年,2006年以全票晋升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2010年应聘为澳门大学讲座教授,著述各类学术著作60多种,论文600多篇,著作量达到近2000万字,被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著名学者称为“治中国文学之第一人”,“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先人物”。我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不是我这个连研究室主任都没有当过的普通研究员有多么高明的管理和操作能力,而是胡绳、李铁映院长想通过一个学术造诣、学术成就较高的学者,来拉动和推升整个研究所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档次。当时流行一句话:“狮子引领着狗,狗就变成狮子;狗引领着狮子,狮子也就变成狗。”这说明选好领军人物的重要性。重要性蕴含着责任感。
在学术研究中,要开一代学术,不是前辈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而是要采取一个更高的更新的视角来进入。进去之后还要看你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研究角度和深度。你不是给前人的一百部著作增加了一部变成第一百零一部,而是你另开一个体系,成为第一部。
贺仲明:您提到做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方法,就是在大量的材料中发现、综合,形成自己新的见解。近年来您对古代文学关注更多,不知道您的现代文学研究对您的古代文学研究有没有什么帮助?您有什么心得跟体会?
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我重回鲁迅研究,研究鲁迅跟金石学的关系。民国初年的鲁迅是个独特的存在,如果没有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五四时期的鲁迅。我们讲鲁迅往往是说他接受西方思潮影响,但其实鲁迅的中国传统文化底子很深。通过对鲁迅的研究,我对古代文学的了解更丰富也更深入,也进一步增加了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初步形成了向古代文学研究转向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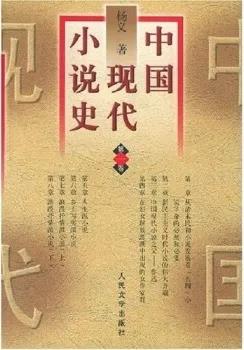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著
贺仲明:您是卓有成就的资深现代文学研究学者,能否谈谈您对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的期望?以及有什么经验?
杨义:肯下工夫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在基础文献的阅读方面。比如说你研究鲁迅,必须要对鲁迅的整个知识结构、鲁迅的素质有充分理解。鲁迅在研究小说史时从文献入手,下了很大的工夫,才写出《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通过对每个朝代思想文化的观察,尤其是民俗信仰的观察来证明特定的小说必然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例如志怪、传奇、明代四大奇书等。这些观察都是他深刻地研究了文献后用史实来点亮文献。没有文献的史实是空的,没有史实的文献是材料的堆积。鲁迅比当时很多研究小说戏曲的人要高明,因为其他人是在整理材料,而鲁迅是点亮了这些材料。我们要把文献、史实和各种思想方法融会贯通,研究者的这种素质和能力非常重要。有了这个能力后,再去开拓新的领域。运用这种方法,我在我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建立了和西方叙事学不同的体系,我认为西方叙事学的世界性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性,让东方的叙事学和它进行平等对话。

《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杨义著
贺仲明:您认为在一个学者成长中,导师的指导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一个好导师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如何做到?
杨义:我的许多研究都是立足中国文化的根本,参照西方现代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评价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在创造新的学理体系中,导师起的作用是告诉你文献功夫和创新能力应该从那里入手,导师引进门,创造在个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必须锲而不舍地迎难而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怎么走呢?还是要靠自己努力,自己的韧性和坚持。年轻学者不能过于依赖导师,要敢于超越自己的老师。学术是无止境,也没有绝对权威的。真正的学者要有不断突破的精神。
贺仲明:您的《中国叙事学》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有着与西方文学不一样的叙事传统,并进行了充分阐释。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杨义:文史哲是相互贯通的,不要画地为牢,不要顾虑自己是什么文学学者、文化学者的身份,而是不断地挑战自己的身份,追寻思想学术的新空间、新境界。治学,重要的是要“开窍”,创造性的孔窍开通了,选择好一个最有生长可能性的创新立足点、出发点,把学术逻辑与历史逻辑融通起来,打开一扇扇前人浅尝辄止、或未曾涉足的门户,在新的文化空间中尽情地施展你的十八般武艺。即使是面对西方新的学术人物、学术思潮,也要进行分析,看出他们大吹大擂的“世界性”,由于对东方文化的隔膜和空疏,依然是一种“有缺陷的世界性”,需要底气丰沛的中国学者与之进行平等的深度对话,才能引进源头活水,才能共构一个坚实而活泼的文化创新空间。中国学术应该具有中国的风度,中国的特质,中国的本原和血脉。如鲁迅所说:“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我们要用生命的血,染红我们的学术,这种学术才有沉甸甸的份量,才能震撼人心。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属于国家发展的软实力,文化自信的大厦全靠它来支撑,这应该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贺仲明:您刚刚讲的这些话让我很受启发。学者需要自信,中国文化也需要自信。这是学术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重要前提。另外,这么多年来,您带过很多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请问您在指导学生和教学方面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杨义: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给学生选题。比如说赵稀方,我给他选的题是做香港台湾文学,因为这个领域有很大的潜力,同时要用新的思想方法研究香港文学。再比如说李琳,一开始想做小说思想性、艺术性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般人都可以做的,就让他做地域文化研究,去研究一批流放云贵地区的作家。还有一个题目,是鲁迅的杂文和杂学。其实有些时候鲁迅看的野史透露出的社会实际情况比正史还要重要,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另外,研究的思想方法是可以贯通的。无论研究现代文学、古代文学,都有贯通的思想方法。能融会贯通才能做出大的成果。例如,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可以融入文学地理学,让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维度都参与进来。真正善于研究的学者,掌握了融会贯通的思想方法,在哪个领域都可以出新。
贺仲明:所以说带学生的时候也要让他们有这种融会贯通的意识。
杨义:对,在研究鲁迅杂学的时候就要把它研究透了。为什么鲁迅把眼光放在杂学上,而不是放在四书五经或正统的文献上?这是他文明批评、思想批评的维度。他认为在这个地方才能发现文明、思想和社会的真正意义。
贺仲明:所以您在指导学生方面很有成就。刚才您说先秦诸子的还原工作,又回溯了鲁迅的现代文学研究,请问您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是怎样的?
杨义:我曾经给7个博士生上课,上课时我提出理想的文学史的发生学应该怎么写、有什么原则的问题。比如说取材,你所选择的材料代表了你的眼光,哪些材料放在中心位置、哪些材料放在侧边位置,代表了你的文学史观。再者,还有文学和思想文化。文学史是由经典来构成,我们既要把握经典,又要打破经典。例如苏东坡最好的作品是他流放黄州时写的,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及《念奴娇·大江东去》。这些经典作品为什么在这时产生?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差点丧生,后来流放黄州。这时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受到了很大冲击。这时他用江水和明月来祭奠千古英雄,也祭奠自己。根据我的猜测,因为高太后说先帝给你留了一个宰相,所以流放黄州时的苏东坡还没有灭掉另一个心——他可能还想回去朝廷。到了儋州的时候他就接地气了,跟他在黄州时不一样了,把世间的事情看破了。另外,苏东坡的蜀学和王安石的新学、程颐的理学都是当时的显学。他的蜀学既有经学,又有纵横气。他的学术体系、思想不是很纯粹的理学思想,政论也带有纵横家那种指点江山的气息。
贺仲明:您的学术研究关注了从古到今的广阔时代,从研究空间来说,您也涉及到民族文学等多个领域。您是广东人,近年又主要在澳门生活,应该能够感受到正在兴起的大湾区文化建设获得。您对粤文化、广东文学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不知您如何看待粤文化和广东文学的发展问题?
杨义:岭南文化在上古时期,甚至唐宋以前都是边缘的文化。唐到北宋,流放到岭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到了南宋就不同了,南宋的经济、文化发展应该说是超越了北宋,同时开发了岭南。南宋以后,贬谪不贬到岭南,而是贬到云贵川那边去了。明清之后,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岭南的思想从边缘走向前沿。例如,万历年间利玛窦带来的天主教和科学技术跟中国古老文明发生了碰撞。在今天,香港仍然保留了和西方接触、交流的许多渠道。所以岭南的开放走了好几步,南宋是很关键的一步。
贺仲明:现在广东的商业文化比较发达。
杨义:当时中原还是重农抑商。现在广东打开了另一个东西——商业文化。司马迁那时觉得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是他的思想没有被正统王朝所接受。只有到南宋以后岭南文化才逐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贺仲明:杨老师,访谈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您也辛苦了。或者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听了您的访谈,收获很大,也相信它肯定能给更多的年轻学者以裨益,帮助他们在学术和人生上的成长。谢谢您!
杨义:今天通过跟你的对话,使我的思想也活跃起来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文学院
文章摘自:《新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