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西学东渐的逆行者?
全球的时代,中西文明以更为紧迫的姿态将相互间的理解提上议事日程,文明将因对话而更加精彩。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中西关系与文明对话”系列,邀请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又兼顾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共同探讨不同文明彼此沟通、相互体认的可能途径。以下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段怀清教授的文章,原题为《辜鸿铭:清末“西学东渐”的“逆行者”?》。
——编者按

辜鸿铭
一
1883年,辜鸿铭(1857-1928)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中国学》一文。这也是辜鸿铭第一次公开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是年他28岁,正近而立之年。
《中国学》一文的意义,并不完全在学术上或学术批评上,还有其他几点同样引人注目。其一是辜鸿铭以对西方汉学家尤其是19世纪欧洲汉学的批评,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写作生涯;其二是他在该文中提到了数量惊人的西方汉学家的名字,无论是否通读过这些汉学家的著述,仅从那些评论文字中的只言片语式的点评,已多少显示出辜鸿铭当时的知识结构和学术信息储备的别具一格、非同凡响;其三是《中国学》一文发表在英文报纸上,也就是说,辜鸿铭当时很清楚他文章的读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在华西人,甚至那些宽泛意义上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读者;其四是《中国学》一文是用西方语言而非汉语中文所撰写的。如果从接受教育的角度讲,英文倒更像是辜鸿铭的“母语”,而“中文”则是辜鸿铭差不多在而立之年后才真正开启学习并试图掌握的一门书写语言。
1885年,亦就是《中国学》发表一年后,辜鸿铭受招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出任督衙洋文案,“凡外交之事,资君赞画者居多”。后张之洞迁督湖广,辜鸿铭追随其后,并正式拉开了他协助前者推进洋务运动、自强救国的事业序幕。
如果统观辜鸿铭一生,会发现发表《中国学》和入幕张之洞督衙,分别开启亦各自代表着其一生事业的两条主线:西方批判和推动洋务——这本身看起来亦就生发出足够的内在张力。在这两条主线上,辜鸿铭的努力,又屡屡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非议或误解。有人认为辜鸿铭的西方批判就是为批判而批判,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在推动洋务方面,其实辜鸿铭不仅对张之洞推动洋务运动是有一定保留的,甚至对晚清整个“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他也一直保留有自己的立场及主张,这一点从他1920年在德国结集出版的《呐喊》一著中可见一斑。
换言之,尽管从1880年代一直到其暮年,辜鸿铭最主要的事业就是上述二途:著述与洋务,但他的著述并非是向中国输入并倡导“西学”;而在推动洋务方面,他又对洋务背后的西方世界,抱持着独树一帜的个人立场和观点主张。对于辜鸿铭的上述立场及言论主张,敬佩肯定者,多见其批评西方的一面,未见其自我矛盾的一面;而反感攻讦者,则多见其自我矛盾之处,而往往忽略了辜鸿铭试图超越中、西方在彼此认知方面的时代局限,在更高的文化及文明批判层面对于人类命运及文明未来的持续关注和深沉忧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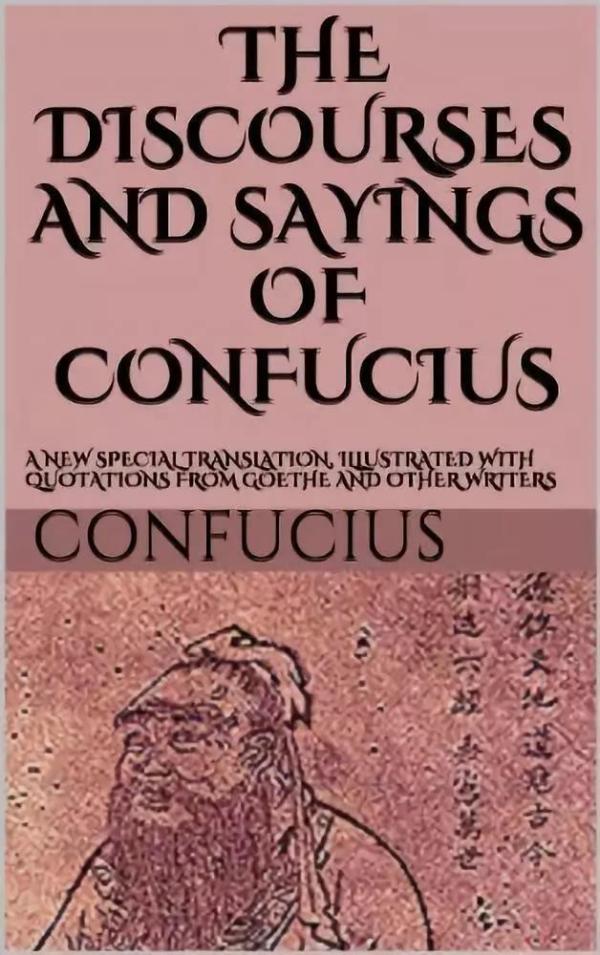
辜鸿铭翻译的《论语》
事实上,1911年辛亥革命、清室逊位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作为言说者、著述者的辜鸿铭均产生了极大触动,而作为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成就,就是他所翻译的《论语》、《大学》和《中庸》这三部儒家经典。有意思的是,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副标题,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
这一副标题,应该可以作为辜鸿铭向西方翻译传播儒家经典、阐发中国人的精神乃至中华文化核心要义的一个重要注解,但这一点又往往被辜鸿铭的中外读者甚至研究者所忽略。其实,辜鸿铭的西方观,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反西方,更不是所谓的为了批判而批判,也不是仅仅站在维护中国的立场上为中国及传统文化辩护。细读辜鸿铭的著述,就会发现他的阅读书单或文章著述中所提到的人名,并非只有被批判者这一系列,也有被他肯定、赞颂和阐释的这一系列,而且在后一系列中,并非只有中国传统儒家的圣贤哲人,也并非只有他所高度肯定的作为中华古典文化和文明代表体现的所谓“良治”与“良民”,还有从古希腊的哲学家一直到歌德、卡莱尔、阿诺德、爱默生等一长串西方人的名字。从这些名字中,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辜鸿铭的中西文化与文明批判的“超越性”,亦或者试图在中西文化与文明的更高层面,搭建起严肃认真对话与交流的思想努力。其实在这一方面,辜鸿铭无疑是晚清以来本土知识分子中最早意识到中西之间需要真诚而理性的文化与文明对话,而且也必须切实予以践行且中外闻名的批评家之一。
如果不仅将辜鸿铭置于晚清“西学东渐”与“洋务运动”这一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也不仅置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持续至今的时代语境来考察,还从中西文化与文明对话或者现代化与全球化这一更为宏阔的思想与实践语境来考察,辜鸿铭的文化身份及意义,应该就不只是一个晚清“西学东渐”的批评者或“逆行者”,一个中国立场与中华文化及文明精神的辩护者,还是甚至更是一个一直在试图超越中西文化与文明之人为藩篱界域、试图重建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与普世理想之宏大愿景的重要参与者,所不同的是,辜鸿铭将他所理解并认同的中华文化的经典与精髓,严肃庄重而且坚定积极地推介给了这一场注定不会一蹴而就的世界性的文化与文明对话。
二
1916年,亦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辜鸿铭60寿诞。当年曾同在张之洞幕府担任过文案的汪凤瀛(1854-1925),专门为此撰写《辜鸿铭先生六十寿序》一文,其中有一段文字,这样描述辜鸿铭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
君自髫龄即负笈重瀛,遍历英法德诸国,先后卒业于其国之大学,卓然为欧洲文学之冠。凡各国政治宗教得失之故,与夫名物象数之赜,旁及工程制造之事,莫不精研探讨,洞彻其始终原委而得其要领焉。学成归国,懼贻夫数典忘祖之讥,益动其好古敏求之念,于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深思力索,务求其义之所归,博考旁稽,必识其事之所系。于历代之朝章国故,靡不讨论研究,而知其兴衰治乱之由;于群经之大义微言,尤能融会贯通,而不涉破碎支离之病。它若诸子百家以及稗官野乘、道经释典之类,罔弗博涉多通,而尤于名儒语录先正格言,深嗜笃好,以为率循之准。
这是一个在1870-190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极为罕见的知识、学术与思想个案。众所周知,晚清中国于1860年代先后在北京、上海及广州创办了旨在向中国学子教授外国语言的新式学堂,即同文馆与广方言馆,而此时科举考试制度依然是作为评估教育水准及人才选拔标准的国家制度及仕途正道。尽管这些外国语学校的创办,只是为了尽快养成并解决在翻译及制造方面所亟需的洋务人才,却也推动了晚清“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改革。而汪凤瀛的兄长汪凤藻,就曾在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外国语言,而当时主持上海广方言馆的西方总教习,就是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
1870年代,清政府又先后分四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由此拉开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出国留学大潮的序幕。不过,如果就知识结构以及思想格局而言,当时留学生中鲜有可与辜鸿铭比肩者——辜鸿铭不仅在1870年代即获得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对于西方古典学包括古典语言与古典文学,有着他的那个时代中国本土士子学人绝对鲜能企及比肩的知识与学术修养,同时他还曾游学法德,对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亦曾深有涉及。而回国之后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与文明的“好古敏求”及“博涉多通”,不仅让辜鸿铭在古典与现代、人文与科技、西方与中国之间,均有了非同凡响的知识训练与学术体验,再加上长期在张之洞幕府的高层历练,使得辜鸿铭在认识视野及思想境界方面,事实上成为了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最有可能在中西之间展开文化与文明对话的不二人选。
对此,辜鸿铭的同时代人中,即有对他在这方面的所学所为以及学术及思想操守给予过肯定评价:
吾国自前清同治中年,政府始有选派生徒出洋游学之举,至光绪季而其风极盛。卒业而归者,就中不乏通才硕彦,知名于时而求其持正不阿、不为利禄所诱,则皆视君有愧色焉。
自有清末造,西学盛行,出洋游学一途,争视为终南捷径,有官至尚书侍郎者。民国初建,留学生尤见重于时。上自内阁总理各长官,下逮群司百职,咸得当以效其用。以君之学之才而终不一遇,虽寂寂憔悴、穷居困顿,而曾不少悔焉。
这似乎是在为辜鸿铭不见用于时而抱屈,但更多则是对于辜鸿铭作为一个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思想气节的认同敬佩。而对于辜鸿铭在向西方世界乃至全球推介阐释儒家思想以及中华文化方面的积极贡献甚至不二事功——“君又欲以孔子之道推行西国,因以英文译《论语》《庸》《学》诸篇,遍布海外各国之学者,几于家置一篇、人手一册。则君之志虽不伸于中国而吾道精微,得渐被于泰西,君亦可以少慰已”——评论者因限于所学,只能作上述夸张之描述,未能真正深入其中并作详尽阐述发明。
其实,早在辜鸿铭之前,曾襄佐林则徐幕府的岭南士人梁廷枏(1796-1861),在其《海国四说》一著中,就曾提出西学既然可以入华,儒家学说何不能“西渐”的设想。时人对此亦多见其为中华文化辩护的一面,而鲜见他们对于中、西方文化与文明能够展开真正平等、理性对话交流的期待,以及为此所曾经付诸的探索努力。
而随着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扩大深入,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并成为时代之主流,辜鸿铭当年所发出的思想声音,一方面近乎被完全淹没,另一方面,似乎又不时地浮泛起一些隔代的回响余音。
三
红红白白的野李花
在寒空中开放,
阳光照射下的丛林
一片美丽的橙黄。
珍珠般的河水清澈透亮,
静静地流向大海。
那灵魂的骚动纯粹只是为了
自己能够自由自在。
这是辜鸿铭在他的《总督衙门论文集》开篇扉页上所附的一首诗的一、二小节,整首诗凡十节。这首悼亡之诗作,几乎将辜鸿铭自己的人生及人格理想全部隐喻其中。“阳光照射下的丛林”,或可隐喻辜鸿铭自己的思想与精神世界,或可隐喻他所致力于弘扬的中华古典文化与道德文明,亦或可隐喻他所尝试努力的引泉成流、终归大海的跨文化、跨文明的对话交流这一理想事业。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辜鸿铭的读者,应该也都可以从这首诗中,读到一个世纪之前的那个思想生命的精神世界里最高贵亦最温暖明亮的那一部分。
1866年,英国思想家、批评家卡莱尔(1795-1881)在爱丁堡大学发表其受聘该校校长后的“就职演讲”。7年之后,辜鸿铭注册入学爱丁堡大学。尽管校长和学生显然并没有在校园中相遇,但校长对于这位来自于千万里之外的东方学子,却产生了终其一生的影响。
卡莱尔的就职演讲中,提到了这些对于一个知识生命来说绝对不容回避的核心价值:责任、工作、艺术、英雄、历史、忠诚、宗教、终生不倦地从书籍和生活中学习。而这些价值中的绝大部分,在辜鸿铭后来的人生中,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回应。
1928年,辜鸿铭病逝。
在此前后,还有严复(1854-1921)、林纾(1852-1924)、王国维(1877-1927)、梁启超(1873-1929)亦先后离开这个世界。清末民初积极参与并分别引导过“西学东渐”的一代学人,退出他们的历史舞台,鲁迅、胡适等新一代学人,迅速取代或填补了因为他们的离去所留下的空白,并创造性地开拓出属于一代新人的全新事业。而晚清所开启的“西学东渐”这一历史潮流,亦由此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无论这是辜鸿铭曾经倡导过的,亦或者是他曾经忧虑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