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图内斯《审查官手记》:以患病形式“沾染”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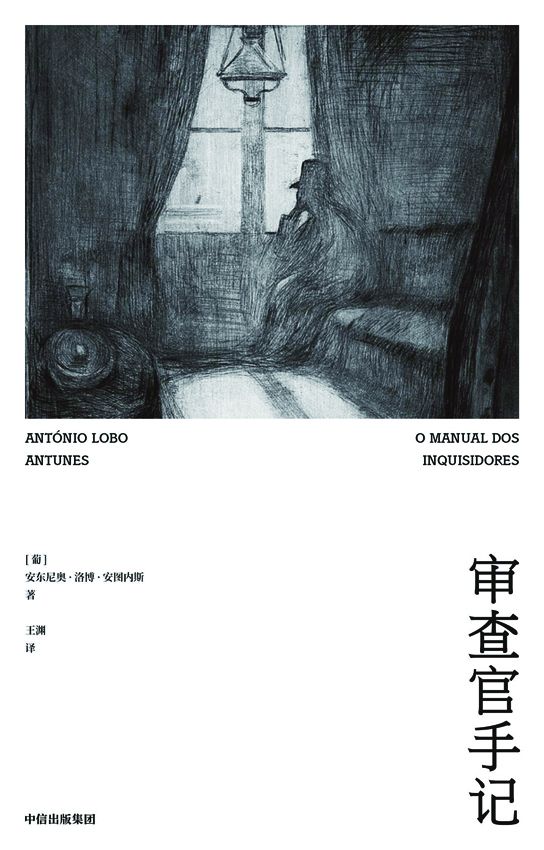
《审查官手记》是一部奇异晦涩,“挑衅”读者的“怪杰之作”。作者安图内斯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一样,堪称当代葡萄牙语文学的“双子星”。从某种角度看,安图内斯属于跨界写作,作为长期研究心理学的医师,他对人性异化与社会病态抱有抑制不住的诊断激情。可以说,他让小说变得更像“病例报告”。《审查官手记》里的回忆与叙述充满反常的扭曲变异,偏离与混乱,正是对叙事可能性的极端实验。在作家看来,清晰可辨的意象、叙事节奏的稳定、人物和情节的秩序,不过是经过理性压抑、自我审查的结果。
安图内斯正是想提供一种“原生文本”:充满矛盾狐疑、闪回跳接,沉默躁郁反复交替的叙述,就像梦、醉与病的三位一体。《审查官手记》被称为作家最黑暗的作品,直抵人类无意识的幽暗之地。不正常的文本,需要非常态看待。叙述者的“失控”,意味不再受作家“审查”,而是向所有读者敞开的虚空。这或许是“审查官”(召唤读者批评)之谓的真实意图。小说的“述评体”颇为独特,“共分为五个报告,每一篇分为六小节,一位主要人物分三次叙述,另外三人各有一次评论的机会”。(《译后记》)这让我想起循环赛制,结构与程序的均衡之美,与叙事的繁杂迷乱,造成几近怪异的反差。
其潜在意图很明显:即使人物的身份地位有云泥之别,但在叙事话语上却显露平等制衡。部长弗朗西斯科与儿子若昂、女管家蒂蒂娜、私生女保拉、情妇米拉这5个叙述者,和外围14个评论者,完全超越了复调小说的多声部合奏。因为安图内斯的诸多叙事者,并非声音的简单叠加聚合。相反,众声喧哗的“离散型”与“非和谐”压过了惯常的和声。而纷乱嘈杂,或许是作家意欲呈现的叙述生态。
尽管作家反感原型批评和历史分析,但评论家们依然发现了某种现实映射。作品文本风格与作家批判的现实生态,恰好是协调互生的。他用小镇帕尔梅拉上的一个庄园,衍射整个葡萄牙社会的历史图景。历史上,经济学教授出身的萨拉查,统治葡萄牙近半个世纪,他将对外殖民与国内农业传统结合起来。小说里的庄园就是沟通农业社会和政治时局的空间隐喻。部长弗朗西斯科和少数寡头在这里关起门来,玩弄社会政治。这种家国宗法的高度同构,移植并扩散成一种关系,即部长弗朗西斯科对雇工仆人的任意处置,与父权制的独裁政府之间本质相同。
有意味的是,安图内斯强调小说的催眠、致幻功能。这是很多作家都未曾重视的接受心理。“你们需要陷入这些作品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暂停和冗长的省略,沉溺在阴影覆盖的波浪摇摆之中,一点一点地,文本就会把你们带去和致命的黑暗相见,这对精神的再生与革新至关重要。”“我提议的真正冒险,需要叙述者和读者一同在无意识的黑暗和人性的根基处进行。”作为早年就研究医学、成为作家后仍旧从事精神分析医师工作的安图内斯,把“职业后遗症”也带入到创作里。你甚至有种直觉:小说是把葡萄牙社会当作病院环境,将一群人物当成需要治疗的“病例”。
近于精神分析一样的文本召引,相信自然而然能诱引读者进入无意识层,探查人性的基底。从而,我们理解了作家所谓放弃“讨论主题”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让读者脱离“意识层”的控制,进入不加设防的无意识。作家将这种接受过程称为“以患病的方式沾染书”,而非阅读。只有经历“感染”,才会在康复时(合上书,回归自身时)满载而归。若昂少爷的自白就说明了叙事的虚空。“无我”是行为的条件,人物的透明性得到突显。“婚后他们请我去银行上班,条件是在月末的工资单上签字,条件是我不许异想天开,不许搞什么项目,不许在会议上发言,也不许去工作,事实上,条件就是我不再存在,对我的岳母来说不存在,对我的妻子来说不存在,对我的孩子们来说不存在。”
小说如同精神错乱的呓语,是一堆不同时空生活场景的“混剪”,强制拼贴。博士老爷在庄园的堕落淫乱,法庭打离婚官司的若昂少爷,岳母打桥牌时的轻蔑……这些印象成了倒带循环,不断重现,就像坏掉的光碟,总跳不过故障影像。如老爷说:“她们要怎样,我都会做,但我从不摘下帽子,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岳母对女婿的蔑视,“你是真蠢还是装傻”。这些口头禅似的句子,被作家循环插播,指认出人物最难抹除的无意识印痕。
管事女儿只有在黑夜的长明灯里才能看到幸福宁静,白日却是死亡重来的时刻。黑白颠倒,恶魔就在白日(现实里)伸出魔爪。老爷欺辱一切可被奴役的女性,看待她们如同圈养母畜。女人与奶牛的描写拼接,正有如此用意。这暗示我们一种罪恶逻辑:暴力已超出阶级压迫的奴役性,转变为人对“牲畜”的凌辱。若昂少爷是见证父亲不堪兽欲的叙事者。“我从没有母亲,没有兄弟姐妹,我是独生子。”在我看来,“猜母亲”或许是小说的游戏,听上去像荒谬恶作剧,却是罪恶的果实。“而这张照片里的女人很像那位女管家,她会开着灯在我身边‘小若昂、小若昂’,直到我入睡。‘会是女管家吗’?”
如果我们按作家提示,用“符号”、“私语”或“幻觉”来看待故事,就会发现更多寓言象征。如部长造访时,不仅对人下达高压禁令,甚至对乱叫的乌鸦也大肆射杀。那只阿尔萨斯狼犬的狂吠,也是犬牙帮凶的符号表达。排除异己和噪声,追求绝对的死亡寂静,是葡萄牙独裁时期的精神写照。甚至暴力也渗透于日常,如管事女儿的受迫害狂,持续出现的幻听幻视,意味暴力的后遗症更为恒久。“害怕厨娘会抓住我的脖子,拿刀把我的喉咙割断,害怕厨娘像博士老爷在畜棚里那样扼住我的脖子。”“博士老爷的皮带松开,背心敞着,大腿夹住我的腰,一边笑一边将小雪茄的烟雾吹到我的颈背,别动,小姑娘。”
博士老爷的威权是与统治阶层联结,“合体”实现的。他与枢机主教大人、海军上将、萨拉查教授、教皇的合影照片,说明是利益勾结的同盟。安图内斯实现了文本的复仇,他让老爷从一个施暴者、强权者彻底蜕化成被人摆布的失能者。女护工把老爷当成“垂老的婴儿”、稻草人、一个旧玩偶。“她们解开父亲睡衣的布袋,打开襟门的拉链,在他极度消瘦、除了毛就是骨头的双腿间摆上便盆”,“我的父亲下巴下垂,屁股绵软,正尝试用颤抖的袖子擤鼻涕”,“我的父亲一言不发,百依百顺,一无是处,没有小雪茄,没有假牙,没有嘴唇,没有帽子,他像稻草人一样躺在床垫上。”一个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之人,曾肆意发泄兽欲,蹂躏女人。这种近乎报应的“审判”,有种天然快感,它达到了小说内在叙事伦理的制衡。沉默、顺从、又无用,一切独裁暴力都有衰落颓败的残局。
“博士老爷”的形象是暴戾腐坏的象征,他的中风代表贵族独裁的坍塌,庄园毁弃就是隐喻。“博士老爷在如今的大厅里,没有帷幔,没有沙发,没有壁画,没有棋桌,没有吊灯,没有家具,露台朝着荒废的庄园倾倒,花坛近乎枯萎,鸽棚只剩残垣,车库里没有轮胎的汽车慢慢腐朽。”虚构的部长老爷和现实独裁者萨拉查都充满对权力的迷恋。即使中了风,还忘不了恐怖统治的威权。“猎枪完了,威胁结束了,子弹没了。”是否暗指那场没怎么流血的“康乃馨革命”?事实上,安图内斯对革命的态度依旧是怀疑。他并不认为存在历史进步。资本家佩德罗夺取庄园,成为新贵,取代老旧政治势力。但本质上,这并未改变社会的病态、异化与强权,前景依然混乱迷茫。
安图内斯成为福克纳风格的承袭传人,无论是风格、主题还是技法形式。《审查官手记》与《喧哗与骚动》的亲缘关系,如同直系血亲。小说采用的述—评模式,可以视为一种内在性“交互对话”,它在每个叙事小单元里都能实现小说动力上的“内循环”。这种经营设置,把不同人物的情感、判断和视角高度压缩,形成“沉积岩”一般的断面。它们或相互补述,参差互见;或相互阐释,相反相成;或在自我独白和事件评价中,彰显故事本身的多维分裂与意义褶皱。福克纳多重人物叙事、罪恶与不幸的代系轮回,以及如河网稠密的意识流动,都在安图内斯的文本里得到“复刻”。他与塞利纳的相似,则更多如姻亲般“合体”。癔症般的长句,不加标点,就像哮喘患者的呼吸困难,病态、肮脏和颓丧的气氛杂糅,如同冷血动物的肤质,黏腻且潮湿。
作家反感那套社会学式的外部评论,它把小说直接“降维”成一堆问题的佐证注脚。这恰恰是全书最零散、最不重要的方面:“国家、男女关系、身份问题和对其的搜寻、非洲和殖民剥削的残忍等等,也许在政治、社会或者人类学角度上,这些主题十分重要,但它们和我的作品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或许是对动辄大谈后殖民、种族、性别、身份等“学院批评”的嘲讽。评论家们甚至会惶惑,如果不谈这些主题,该怎么“下嘴”去谈作品。安图内斯给出的答案是放弃自己的钥匙,放弃每个人都有的万能钥匙,“只使用文本提供的钥匙”。
这意味着不要滥用外部理论阐释,要用文本批评保证一种内在性、自足性和纯粹性。不要把小说当成历史背景简单的回声返照。安图内斯把作品视为“虚构幻想的实体化象征”,小说沦为虚像,“话语只不过是私密情感的符号,而人物、场景和情节只不过是表面的托词,我只是引领走向灵魂背面的深处。”换言之,作家在意历史幻象里的“意识界真实”。如果耽溺考证和比对,从小说里找寻“历史批评”,显然舍本逐末,并不明智。鲜有作家会在小说前大谈“读法”,但这看似自负的提醒却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