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弋舟《庚子故事集》:文学介入现实,需要诚实
今年疫情爆发时,弋舟待在西安。他整日宅家,几近封门。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或许不算太过难熬,但铺天盖地的消息也足以叫他坐立难安。
就在那段非常时期,他总听见窗外有钟声响起。这钟声来得古怪,声源不明,每天只在午后两点和傍晚六点这两个时刻准时现身。
“你开始怀疑,没准儿,许多时刻,你那所谓的理性,也只不过是自以为是。”
“腿真的是被关住了。耳朵貌似依旧自由。但你早就明白,这人间,从来都有着对于耳朵的囚禁。更多的时刻,人还会充耳不闻,自我拘囿在听觉的牢笼里。”
“往日,你并不觉得有一座大钟在你生活中的存在,就像你并不察觉这世界是在如钟表一般地运行着,无数个你无视的人,人构成的组织,齿轮一般的咬合转动,才支撑起了你轻慢的生活。”
……
他将自己内心的波澜写进一篇《钟声响起》。而钟声究竟来自哪里,它为何不响够二十四下,是弋舟至今想要解开的谜底。
9月,弋舟“献给这个本命年”的小说集《庚子故事集》由中信·大方推出,这篇《钟声响起》作为代自序也被收录其中。《庚子故事集》主要由五个故事组成,有人说,这是一本2020庚子年的记忆保留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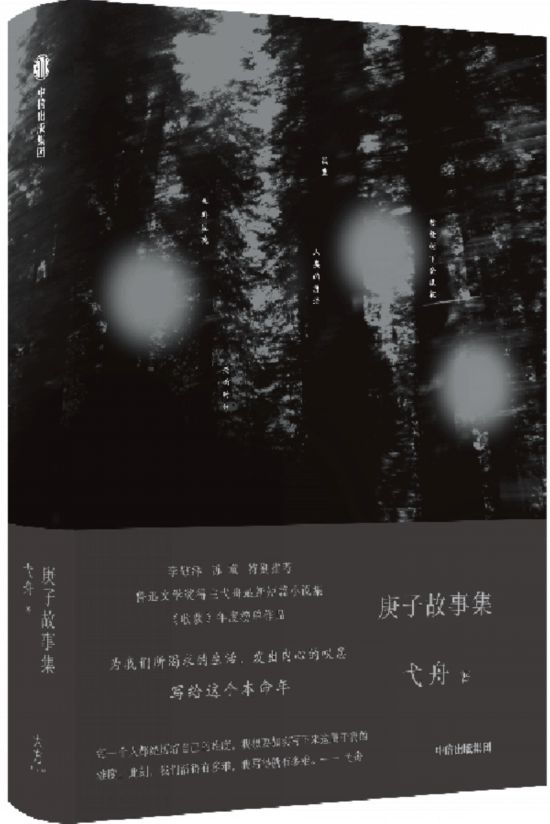
但它并不是一份简单的记录。对弋舟而言,“怀疑”或许最能形容他在这段日子里的个人状态。他怀疑自己,也怀疑写作,“语言,字词,是我工作的基本材料。那段时间,这些基本材料被动摇了。那些既往被我们用来描述世界、说明自身的语言,突然间变得不那么准确和好用了。我甚至对‘隐喻’这个曾经津津乐道的词都怀有生理性的厌恶。就像一个面包师突然不再信任面粉和奶油,这很要命。”
在这样的怀疑之下,《庚子故事集》“非常难写”。按弋舟的话说,“此刻,我们活得有多难,我写得就有多难。”
尽管新作不到十万字,但它依然为今年的现实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固化的场景与正反分明的人物之外为我们了解与想象这个庚子年提供了更多微光。它起码提醒我们,人类的痛苦并非只来自健康,人类的孤独并非只源于隔离;它也提醒我们,在医护之外还有很多人正默默维持着这个世界的生活秩序,在口罩之下还有很多隐忍不发或难以言说的心事与秘密,在疫情之外人类还有很多“轰轰烈烈的平庸的困境”,以及孤独与爱。
近日,弋舟就新作《庚子故事集》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澎湃新闻:因为疫情,你的生活与写作节奏有了哪些改变?到今天为止,你觉得自己的节奏恢复了吗?
弋舟:显著的事实是,上半年的节奏的确是被打乱了,也真的是让我领教了何为失措。时间似乎倒也充裕了,但仅仅充裕的时间,原来并不足以令我们活得从容与写得从容。除了物理的时间,原来,我们更加受制于内心的时间。这种“内心的时间”,兼有空间的性质,它是立体的,时而一望无垠,时而空前逼仄,我们因之空茫或者窒息。
时至今日,一切似乎是有所“恢复”了,但我知道,这种“恢复”感,更有可能源自我们渐渐“习惯”了。时光之下,有些事物,大约是再也无法恢复了。
澎湃新闻:疫情发生以来,你因为什么有过最难受的时刻?在那些艰难的时刻,你想起过你的小说人物吗?
弋舟:写完《掩面时分》的那个晚上,手机上看到一组剪辑的视频,镜头里是流浪在高速公路上的长途车司机,阳台上鼓盆的女子,追着殡仪车哭喊亲人的女儿……那一刻真的是痛苦万分,积压已久的情绪几难自控,我哭得满脸泪水。我想,这应该是人类普遍的情绪,在一场整体性的灾难面前,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切己”的由头,人类本身的苦难,就足以令我们痛彻心扉。这组视频配有音乐,是那首《只要平凡》。于是,我把这句歌词也加进了小说里: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这样的情绪,不过短短半年时间,现在都已觉得有些遥远。我们是多么容易遗忘。回答你这个问题,令我重温了这样的情绪,我发现,它是如此的宝贵。
那些日子里,一个人关在家,是有自己小说中曾经写过的人物在脑子里浮现,但我很难一一指认他们,只觉得他们也在这尘世,一同受罪。
澎湃新闻:《庚子故事集》的《代自序》给了我很多触动。它定稿在今年的2月10日——国内“抗疫”依然十分艰难的时候。“午后2点的钟声”在你的生活中真的存在吗?按你的说法,它完全是“现在进行时”中的情绪。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想到它会是新集子的“代自序”吗?于你而言,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弋舟:它真的存在。我自己一度都怀疑是否有了幻听。为了佐证,我专门在那个时刻站在窗前录了音,连续录了几天,让它确凿地成为了一个“真”的存在。然而如今它却没有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重新沸腾的市声湮没了它?是自己再度粗糙的内心屏蔽了它?还是真的有那么一个人间的机构,只在特定的日子里敲响钟声?这是一个重大的谜面,我一定会专门去寻找一下答案。
这篇文章也是应刊物的约稿而写的,彼时,文学似乎也仅仅能做到这些。当时完全没有计划让它成为一本集子的“代自序”,我没有这样的习惯,出版的书从未有过序言。但是,当《庚子故事集》决定结集时,我发现用这篇文章来做序言真的是恰切。它就是“现在进行时”的,与这本集子的“现在进行时”高度吻合,甚至也和小说一样,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构成某种我需要的混淆。而且,更重要的也许是,不把它收进来,我害怕自己无可救药的遗忘,害怕它也像那准点鸣响的钟声一样,消失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恢复”之后。
澎湃新闻:从《核桃树下金银花》里的那个下午,到《代自序》里的“钟声响起”,再到你和贺嘉钰对谈时说:“我们不属于空间,我们属于时间”……我的感觉是,“时间”在这个新集子里无处不在。
你曾说小说家是时间的捕手,“时间观”约等于一个小说家的“文学性”。我想问,疫情对你的“时间观”造成了哪些影响?
弋舟:这些对于“时间”的指认,我现在依然毫不动摇。如果说,现在我的“时间观”有了怎样的改变,那只能是——我更加地顺服在了它的脚下。最初,我们信任一个“十四天的周期”,屈指一天天地数算,就这样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数算了下来,直至“恢复”,直至麻木,直至生命中失去一个又一个“十四天”,直至坚固的成为涣散,有过的化为乌有……可是,有几个人清晰地觉察到了,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一个春天,失去了一个夏天,失去了一个庚子年。失去了时间,我们就是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
澎湃新闻:说到时间,比起阿拉伯数字,以中国的天干地支来纪年更有一种周而复始的意味。你在2016年写下《丙申故事集》,又在2017年写下《丁酉故事集》。很多作家对“写当下”会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对你来说,坚持写“故事集”系列,难在哪里?你会接着写《辛丑故事集》《壬寅故事集》吗?
弋舟:“当下”与“即时性”,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象。我们也习惯于认为,自己更好的表现,更佳的创作状态,都悬挂在不久之后的他日。于是,今日留给“感受”,他日留给“加工”,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但是你看,那“今日”的钟声瞬息便被湮没,被外部世界湮没,也被我们的善忘所湮没,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及时地提起笔来?
提起笔来,结果当然有粗糙的风险,有被证伪的可能,但至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愿意忠诚于自己的局限,我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就暴露出怎样的状态,我没有必要“装得像托尔斯泰一般优秀”。就像这本集子说到的:我活得有多难,我写得就有多难。
至于继续写《辛丑故事集》《壬寅故事集》,目前来看,应该是会的。我不敢确定,但我期望我能够写下去。
澎湃新闻:《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其实写于2019年,你为什么想到也把它们放进《庚子故事集》?
弋舟:这的确是一个改变。依例,《庚子故事集》要放在明年结集出版的,并且,也只应该收录庚子年写下的故事,但这一年改变的岂止是一本小书的出版节奏?一切都被打乱了,那么,为什么就不跟随着整个时代的步伐一起颠簸?这也是这本集子“现代进行时”的一个体现,我就是想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留下属于自己的特殊痕迹。
集子里破例的事儿多了,我破例给自己的书加了篇“代自序”,甚至,还有一篇没写,就破例和嘉钰做了整体性的对话用来做“代后记”。前面的两篇收进来,也正好是一个时光的接续吧,从中你会发现,原来,尽管天翻地覆,但人的内心却并未断崖式地被改造,我们依然在那些“基础性”的困惑之中打滚。于是,在庚子年出版,也就可以叫《庚子故事集》了。
澎湃新闻:我想这本新集子和刘晓东系列一样,依然在写“时代中的人”,只是因为2020的非常事件,让这个“时代”尤其具体,意有所指,但它的落脚点还是人。
你在集子里有一句话——“我终于看到了我。”它让人想到了认识核桃树的“我”、因为旧物翻检过去的“我”,走到天台边缘往下一望的“我”……这里的“我”似乎可以是弋舟,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人,这里既有普世的况味,也有温暖的力量。如果要你自己用三个词去形容《庚子故事集》,你会用什么?
弋舟:露底。等待。熬着。
“露底”在于这本集子我完全没有想要“表现”的冲动,也没有“再上一个台阶”之类的妄想,不过是如实地兑现出此刻我既有的能力,喏,我活得有多难,我写得就有多难。“等待”的意思在和嘉钰的对话中有过阐释了,《等光来》,一如篇名,这是温柔的盼望,也是一个人应有的自尊。“熬着”就不用多说了,小说中的人们都在熬着,你我都在熬着。但这“熬着”,我视之为力量,是一场生命的盛宴。
澎湃新闻:无论是《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还是写于2020年春节之后的《人类的算法》、《掩面时分》、《羊群过境》,它们都有关“人的困境”。这个主题也是从《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一以贯之下来的。
疫情当然也是人类的困境,但只是“之一”。在没有隔离的日子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依然有隔阂;在能够自由出入的日子里,人依然会懒惰、懈怠、难以专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掩面时分》里写到一句:“世界何曾太平过。不戴口罩的日子里,每个人不是照样深陷在各自轰轰烈烈的平庸的困境里。”我觉得这个表达很真实——“各自轰轰烈烈的平庸的困境”。面对这样的人类困境,你认为文学有哪些能与不能?
弋舟:对此你已经描述得很充分了,文学“所能”,也无外乎忠实的、准确的、富有艺术性地将其捕捉下来,这些“能”,在我看来也许恰恰是文学的“不能”。那些自以为文学无所不能的人,就让他们奔放地去“能”好了,那些自称“从未对文学绝望过”的人,恭喜他们,他们从未理解过,文学之“无能”与绝望,亦是人的根本性困境。他们感受不到人的困境,欢天喜地地追名逐利也好。
澎湃新闻:有关“疫情时期的文学”,线上线下、纸媒网媒都有很多对谈、讨论,也有很多打着现实主义名号的写作,但似乎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并不多见,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有效性也在下降。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在你看来,文学应该如何与现实生活重建关联?
弋舟:这样的难题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也开不出什么药方,只能说:如果文学真的能够有效地介入现实生活,我所认为的唯一前提便是——诚实。你不能一面赞美英雄,一面对于自己的自私毫无羞耻,不能一面天花乱坠地表达着文学理想,一面提笔就是表演。自私其实没那么不堪,是你得直面自己的私欲,表演也可被理解,但是你一边表演要一边懂得害羞。弋舟,当代小说家,历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刘晓东》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我们的踟蹰》等,长篇非虚构作品《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等。

弋舟,当代小说家,历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刘晓东》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我们的踟蹰》等,长篇非虚构作品《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