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中幸存者张静淑君的后半生
原标题:心灵的债务——缅怀张静淑老人
我虽并非宗教徒,但却有忏悔意识。特别到了暮年,常反思此前做过什么错事,荒唐事,不周到的事;能弥补则抓紧弥补,实在弥补不了那就只能今生抱憾,留待来生了。
本文所想偿还的,是我对张静淑老人的心灵债务。
这应该是六十余年之前的事情了。我在湖南长沙雅礼中学就读期间,语文老师声情并茂地在课堂上讲授鲁迅的杂文《记念刘和珍君》。文中有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实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骨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根据鲁迅此文叙述,发生于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烈士在段祺瑞执政府前中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从此,张静淑“沉勇而友爱”的形象就镌刻在我的心版上。对于她传奇式的经历,我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三·一八”遇难烈士纪念碑
58年前,由于命运的安排,我出乎意料之外地被分配到了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学任教,而这所学校的校址恰巧是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这“三个女子”母校的原址。又是由于命运的安排,46年前我居然萌发了撰写一本《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的念头。这是一本史料性的读物,资料来源之一是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历史档案,之二是当事人的口述历史。经过多方打听,我终于得到了静淑老人的通信地址,于是就开始了约3年的通信联系。
回忆起来,我最初给静淑老人写信是1975年底,询问了六个问题。1976年元旦她即给我写了回信。当时她还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市建政街24号,是租赁的一处民房,条件极差。后来才搬迁到长沙南区幸福街32号一处公房,条件稍有改善。静淑老人在回信中说:“从你信中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看,使我感觉到你这位五七届高中毕业生比我这个五十年前女师大毕业的学生对女师大的情况都熟悉些。我不知道为何能如此熟悉?资料出自于何处?”
我当然最想了解老人当年受伤的情况。据旧报刊报道,在“三·一八”惨案中张静淑受伤,被抬回女师大,惨叫了一夜,第二天才住医院,身体倍受摧残。我跟老人核实这一情况。她复信说:
我受伤后苏醒过来一看,我正倒在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院内,左边大铁栅门口。刘和珍、杨德群两位也都倒在那里呻吟。我使劲地抬起双手来,抱着刘和珍,叫她快起来!她指着胸前子弹眼说:起不来……当时,这院内大铁栅门口人堆人,极难爬过去。有一位北大戴眼镜的男同学把我向缝隙里一推,我跌倒在地上。他扶起我问:“哪里的人?”我说:“女师大的。”他叫了一辆人力车,扶我上车,放下车篷,嘱咐拉车的:“由小胡同走!”我到校时已是傍晚,同学们正集聚门口等候我们三人。同学把我抬到寝室床上后,发现枪弹从我背后尾脊等处射入。当时学校成立了救伤委员会。注册课的职员伍斌,湖南衡山人,戴眼镜,用电话请德国籍校医克礼来诊,当即送往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几天后将弹头一一从大腿等处取出。这时鲁迅先生也住这家医院,是临时避难的,他吃得很少,我常将我吃的东西分送给他吃。(1976年1月13日来函)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旧址
同时,我当然会向她了解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的事迹。她函告我,刘和珍烈士是她的好友,1923年一同考入女高师。刘读英文系,她读教育系。烈士是江西南昌人,1920年毕业于江西女子师范。1921年秋在该校组织进步团体“觉社”,出版《时代之花》半月刊。“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她的遗体是从段祺瑞政府手中几经交涉才夺回的。烈士的老母亲1960年去世,活到83岁,无疾而终,一直享有烈属待遇。刘和珍之弟刘和理,解放后在江西师范学院化学系任教。
静淑老人还函告了杨德群烈士的情况,说杨德群是湖南湘阴县人,牺牲时24岁。杨德群牺牲后,她父亲过继了一个儿子,叫杨建民,在长沙冶金工业学校任教。杨德群的父亲曾为女儿编过一本《杨德群烈士纪念册》,内有烈士部分日记及散文,原始资料由湖南汩罗县弼时公社弼时中学杨宪章老师保存。
经静淑老人介绍,我跟刘和理老师取得了联系。他曾将刘和珍生前照片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向来办事周到,又翻拍洗印了三十张(每张复印三份)回赠捐赠人。刘先生自留一份,送给静淑老人一份。另外十张,刘先生写信跟静淑老人商量。信中说:“我意,可赠与北京市158中学语文教师陈漱渝同志,由先生(指张静淑)直接寄去,或由我转寄均可。并请先生反面注明影中人姓名及关系。关于陈老师,在我给先生的信中已经做过介绍。陈老师对于先生及烈士是极为敬仰的。”不久,我就收到了静淑老人转赠的这十张珍贵照片。喜出望外,立即转交了鲁迅博物馆资料部,作为文物收藏。杨宪章老师那里,我一直没有主动联系。
我还向静淑老人了解了一些有关女师大风潮的其他情况。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开头写道,敦促他撰写此文的是一位“程君”。她前来问鲁迅道:“先生可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爱看先生的文章。”由此可见,这位“程君”就是这篇经典之作的催生者,就跟孙伏园是《阿Q正传》的催生者一样。我开始臆测,这位“程君”可能是郑德音,因为她是女师大风潮骨干,又是笔杆子,而且“程”“郑”音近。静淑老人函告我:
程君名字叫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她继承祖母遗产,在校时经济状况最好,穿着讲究,人也漂亮,是刘和珍、我的好友之一,不知现在是否健在?(1976年2月20来函)
在女师大“偕行社”的合影上,能看到程毅志其人,印证了静淑老人的说法。
上文提到的“偕行社”合影,是静淑老人跟刘和理老师向我提供的最为珍贵的史料,因为合影上端的题辞是一篇重要的鲁迅佚文!

“偕行社”合影(这张珍贵历史照片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提供给中华读书报社使用。谨致谢忱!)
1925年12月1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后的第二天,刘和珍、许广平、刘亚雄、郑德音、赵世兰、张静淑等二十四名学潮中的骨干在校园合影留念。照片上端有一段题辞:“……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蒙从来未有之难。同人等敌忾同仇,外御其侮。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此之谓也。既复校,因摄影,以资纪念。十二月一日。”我听说这段题辞系鲁迅代为拟稿,因为它既符合鲁迅的立场,又符合鲁迅的文风。此前,鲁迅也有为女师大进步学生起草宣言的先例。我函询静淑老人。静淑老人肯定说,这题辞确系鲁迅拟稿,鲁迅就是在场人,校友吴瑛也可以证实。为什么照片上的题辞不是鲁迅手迹呢?静淑老人解释说:
在女师大复校斗争中,鲁迅先生被称为“学潮鼓动者”,因此既不参加摄影,也不手书题辞。然而“偕行”一照鲁迅先生是完全知道的,许广平先生参加了合影,就是极为有力的证明。(1976年3月3日来函)
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一重要史实,静淑老人又函询了她的学友陆晶清,得到的回复是:
女师大并没有偕行社这一组织,只是鲁迅先生为我们24人拍的照片题辞时用了“偕行”这词。那题辞确是鲁迅题的,是老许(许广平)和我去求他题的。字可不是他写的,可能是照相馆人代写的。(1976年6月3日来函)
陆晶清也是女师大风潮的积极参与者,著名女作家。她是鲁迅为合影题辞的邀请者,这进一步证明这一题辞的确是一篇重要的鲁迅佚文。
关于静淑老人本人的经历,她向我提供了一份传略,还有一篇回忆《我在吉隆坡》。从中得知,1902年6月,她在江西赣江逆流而上的一艘船上诞生。因为其时在江西太和县工作的父亲被革职,只好冒酷暑返回故乡长沙。六岁时父亲病逝,江西贫家出生的母亲只好携张静淑寄居长沙南门外白马庙的一个尼姑庵,以刺绣为生,抚孤成人。后得表叔资助入学。小学毕业后,张静淑考入了长沙古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是徐特立先生,学校不仅提供食宿,而且每年发给灰布制服一件,青布长裙一条。1922年毕业后曾在长沙幼幼小学及北京平民半日学校任教。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升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三·一八惨案”后,张静淑辍学去吉隆坡任教,介绍人是她的同乡、同学任培道。任培道也是杨德群烈士的好友,杨烈士传略的撰写者。1908年,吴雪华女士跟她的邻居钟卓京先生在马来西亚的首府吉隆坡创办了一所坤成学校。这是一所华文学校,重视女子教育。学校预支了张静淑200元路费。1926年底,张静淑乘坐一艘“斯劳斯”号法国邮轮抵达了吉隆坡,迎接她的是十余名从国内聘请的教员。到校后,同事、学生、家长以及当地华侨对她都很好,唯独跟校长格格不入。校长张纯士女士毕业于长沙艺芳女中,观念陈旧,主张复古、读经。张静淑虽是国文教师,但极力反对八股文,坚持讲授白话文。当时,作家许杰在南洋编辑了一份《益群报》,曾把张校长错解《论语》的一些话编成《新语录》披露。张校长怀疑是张静淑所为,于是派来一位叫陈君保的督学来监听张静淑讲课。当时一些进步学生对张静淑表示支持,校方便以“言行越轨”为由开除了四名学生,其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张静淑。
在吉隆坡,张静淑经学生何慕兰介绍,结识了一位共产党员莫华。莫华瘦而高,说一口广东式普通话,居无定所。在他那里,张静淑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此后,莫华都是主动联系张静淑,让她秘密散发一些传单,主要是宣传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北伐战争的胜利,并动员华侨捐资支援北伐。张静淑在吉隆坡呆了两年,休学期已满,在坤成中学又难以再呆下去,便于1928年回国复学,直至女师大毕业。
毕业以后张静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北京女师大附中、长沙私立幼幼学校、纯德职业学校、含光女子中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长沙沦陷,她辗转流离于益阳、沅陵、桂林等处,长达七八年之久。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张静淑与友人创办大同小学及新民、光明两所托儿所,致力于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
晚年的张静淑境遇不好。1976年3月,我写信给她问候起居。她同月15日复信说:
当前我的健康情况很不好,一些老年人的病:血压高,白内障,失眠,动脉硬化我几乎全有,再加上左腿骨跌倒骨折,须扶杖行。五十年前中四弹的伤疤,至今仍隐隐作祟……这些使我处于不安的状态,心脏的活动是随时会停止的。(1977年3月15日来函)
1976年11月至1977年1月15日,静淑老人“病得严重,几乎死去。经诊断是肥大性脊髓炎,致使白血球增加,影响到血压、神志和便秘。”(1977年1月15日来函)
1977年春,我拜托在长沙定居的表弟王平探望老人。同年5月1日,她复信说:
承关怀,托令表弟王平同志来看我,非常感谢。我因年老体衰,血压高,经常失眠,通宵不能成寐,加之最近有时夜晚忽然失去知觉,不认识人,据医生说系梦游,由于年老,神经衰弱,用脑过度所致,因此不但没有和人来信,连书报都极少阅读。(1977年5月1日来函)
1977年5月2日,我又写信问及静淑老人的经济状况。她函复说:
我晚年的生活境况不好,其原因是:我一生毫无积蓄,年老多病不能工作,仅有一子,他已成家,其工资收入极微,时感入不敷出,更无力顾我。(1977年6月22日来函)
她很希望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以求得到党和政府在经济上的援助。
我收信后,即将她的情况及联系方式告诉了有关单位和个人。上海鲁迅纪念馆派虞积华先生专程赴长沙向她征集文物,并支付了一点征集费。静淑老人很高兴,说为数不多,但不无小补。她撰写的《忆刘和珍烈士》一文,我也转寄给了《读点鲁迅丛刊》的负责人王世家,王世家回复说可在1977年11月在该刊发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向老人寄赠了《鲁迅手册》。女作家陆晶清也答应1978年春天由昆明返回上海市时,到长沙小住,探望这位半世纪之前的同窗。这些都丰富了静淑老人晚年的生活。为此,她于1977年12月31日来函向我表达谢意。
最有意思的是,静淑老人在一封信中还跟我以“战友”相称。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我以“关山”为笔名,在《南开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文革时期上海市委写作组“石一歌”写的《鲁迅传》,引起了静淑老人的强烈共鸣。她说“石一歌”写作班子也曾经联系过她,幸亏她没有搭理,否则她就有可能被视为“‘四人帮’伸向长沙的黑手了。好险!”(1977年1月14日来函)
令我感动的是,1977年6月22日,静淑老人还签名盖章,专门给我单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自从认识陈漱渝同志并与之通信后,使我重新得到战斗的鼓舞,我似乎年轻了许多,这是我得感激党和政府,感谢你们,感谢陈老师的。”“战斗的鼓舞”这类语汇,今天读来似乎有隔世之感。她当时提到的“战斗”,主要是指揭批“四人帮”并肃清其流毒。信中虽然对我过誉,但我跟她联系,唤起了她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使她在病贫交加之时有了一些情感的慰藉,倒确是一个事实。
1978年初,静淑老人病逝,终年76岁。当年2月6日,我接到她儿子的讣告:“家母生前,承蒙关怀,家母死后,顷接惠书。字里行间,情谊深厚,深表谢意。”当时,我的第一本小册子《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我立即给老人寄赠了一本,没想到老人遽然仙逝,未能亲自对拙作进行指正。同年5月22日,静淑老人的儿子收到书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首先肯定拙作“作为资料性读物,的确是一本很好的书,尤其是能将有关此一专题的零散的珍贵资料,以史实为依据,进行整理收编,确实难得”,接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未能编入静淑老人的照片和资料。他说,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赞誉的是“三个女子”,怎么能仅突出刘和珍、杨德群而撇开张静淑呢?对于薛绥之先生主编的《鲁迅杂文中的人物》未能收入张静淑传,他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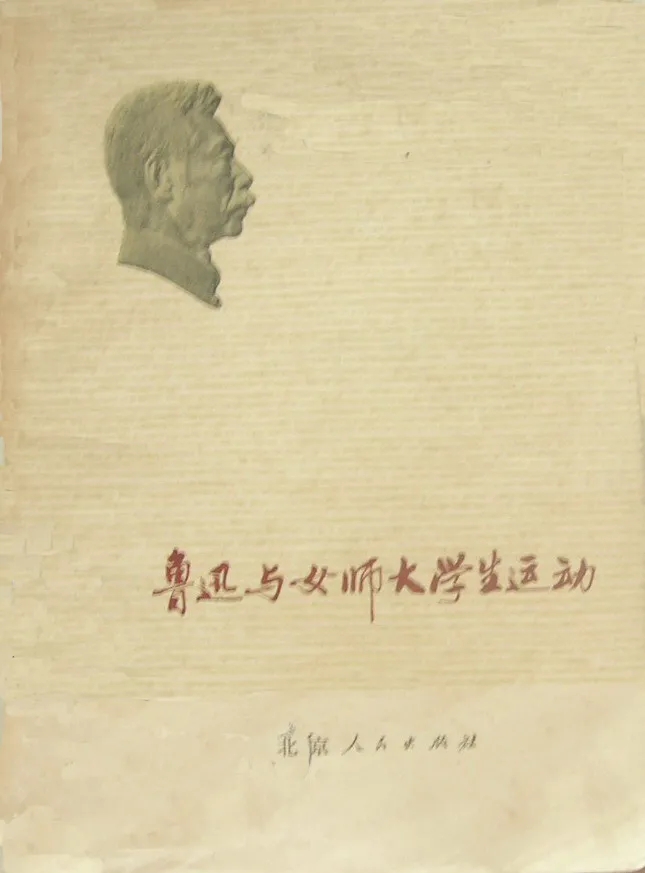
本文作者著《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
今天反思,老人儿子的严正批评并不是全无道理的。不过,《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完稿于1974年,那时我尚未跟静淑老人取得联系。北京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清佑首先肯定了这本书的出版价值,但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邓清佑要我将这部“齐清定”的书稿先压在出版社,没想到这一压就是三年多!如临时增补章节,会导致重排、倒版等一系列问题,出书心切的我便知难而退了。再说,那时公开发表文章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但要审查作者的政治状况,而且也要审查文章或著作中所涉及人物的政治情况。静淑老人是一个隐姓埋名几十年的人物,当年被我发现可以比喻为“出土文物”。虽然谁都知道她的历史贡献,但对她1926年之后近四十年的状况却都不清楚,我也不可能以个人名义去“内查外调”,所以,在报刊和公开出版物上广为宣传,还存在疑虑和顾虑。而且,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国还是一种“乍暖还寒”季节。张静淑老人写的《忆刘和珍烈士》一文,我转寄王世家先生主编的《读点鲁迅丛刊》。这是黑龙江省黑河市教师进修学校的内部刊物,无上级主管单位,所以很痛快地发表了,并在鲁迅研究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全国研究鲁迅的专门刊物似乎只有两种,所以北国边陲城市的这个内刊在鲁迅研究圈子里,可以说是无人不晓。静淑老人《我在吉隆坡》一文涉及到作家许杰,当时他正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将这篇文章寄他审阅。他说已经记忆模糊,未予置评。至于张静淑先生的传略,我也转寄给了编撰《民国人物小传》的有关单位,他们处理的结果我已渺无记忆。
我个人的不当之处,是未能在拙作《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一书中增写有关静淑老人的章节。此后我的研究重点发生了转移,又没有在静淑老人仙逝之后专门撰写缅怀悼念她的文章,因此一直心存愧疚。当下正值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半年基本处于禁足状态。暇时翻阅幸存的师友旧笺,唤起了四十余年前的许多温馨回忆。如今我也成为八十岁的老人,庆生贺寿的朋友微信中提醒了我的真实年龄。有些心灵的债务如不赶快偿还,那就真会造成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在垂暮之年握笔,勉力写了这篇未能尽表心意的文章,希望能减轻我内心的负累,因为心灵的负债是要用情感的利息偿还的。同时我也想提供给研读鲁迅的同好参考;让这些珍稀史料据为己有,肯定会违背静淑老人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