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纽约:《雨王亨德森》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六周 第四天
纽约 索尔·贝娄 《雨王亨德森》
跟巴黎一样,纽约也一直是移民心目中的圣地,尤其是那些满怀抱负的作家们。很多作家来到纽约追寻文学梦,这里云集了众多美国出版社。甚至很多外地作家会定期造访。1969年,就是在他的一次定期造访时,我认识了索尔·贝娄(Saul Bellow),彼时距离他获诺贝尔奖还有七年。他那次来和出版作品或推广活动有关,但还有个浪漫的目的,他当时和玛格丽特·斯达茨(Margaret Staats)在一起,他正想娶她做第四任贝娄夫人(最终有五任)。他们曾订婚过一段时间,后来玛格丽特改变了主意。她给贝娄看了一篇我的日志,然后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约我去跟贝娄见面。见我对十八世纪文学感兴趣,贝娄建议我更广泛阅读当时的作品。正因为他,还有我哥哥,同为文学学者的李奥(Leo),我才读到了菲尔丁、笛福、理查逊和斯摩莱特。他还慷慨地为我的日志写了一些夸赞的评语,“警告”说我可能成为一名作家。
贝娄被形容成那种“把书当氧气”的人,他是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等十九世纪伟大作家的作品长大的。他不仅被源于现代西班牙早期的流浪汉小说传统所吸引,还喜爱十八世纪的书信体小说和讽刺作品。所以他让我去读理查逊和斯摩莱特并非巧合,不是每个人书单里都有斯摩莱特,但他的《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Expedition of Humphrey Clinker)是复调书信体创作的伟大试验之一。就在我与他见面的数年前,贝娄已经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赫索格》(Herzog,1964)还上了热卖图书榜,这本书的大部分都以杂乱无章的书信形式呈现,全是贝娄笔下无休无止的,牢骚满腹又糊里糊涂的主人公写给各色想象中的收信人的信。说是想象的收信人是因为赫索格从来没真的把这些长信发给老朋友、老情人和前妻们,而那些写给类似于像尼采、上帝的信,他想发也发不出去。
贝娄上一本小说《雨王亨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1959)最有可能的模本是十八世纪的作品《老实人》,在《雨王亨德森》里,非洲取代了伏尔泰想象中的巴西,在这里,主人公遭遇一个全然非西方的文明,和当地哲学家一样的国王进行讨论,并逐渐理解自己的世界。如同对伏尔泰笔下埃尔多拉多(El Dorado传说中的黄金国)的再现,瓦瑞瑞(Wariri)的首都就藏在群山中,与世隔绝,而国王达福(Dahfu)甚至有一支“亚马逊女武士”组成的侍卫队。和伏尔泰一样,贝娄从未踏足过他笔下的异域世界,但他的知识却不止是来自那些旅行者的故事。他在西北大学获得人类学学士,又去威斯康辛大学继续攻读硕士,所以不同于《老实人》,他的小说有扎实详细的人类学背景。《雨王亨德森》中很多部落习俗,以及其中一些段落,都直接取自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的《东非的牛情结》(The Cattle Complex in East Africa,1926),这本书出版十年后,贝娄就在作者的指导下,在西北大学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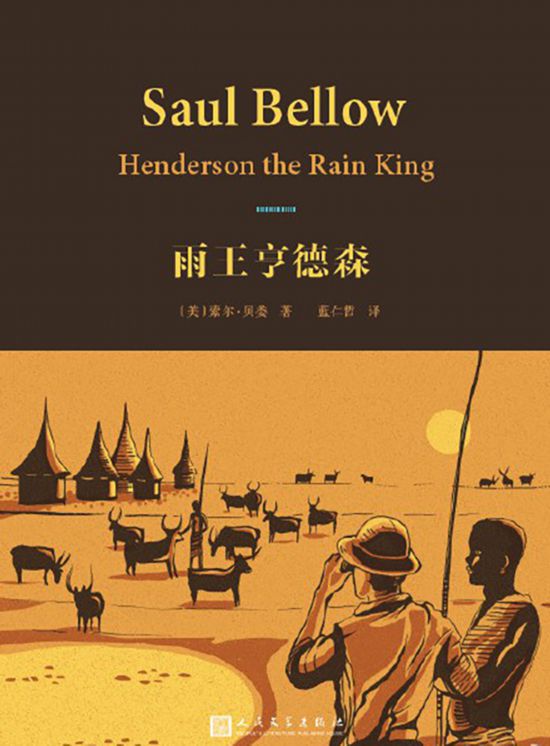
一般认为,贝娄是个典型的芝加哥小说家,但创作《雨王亨德森》时,他住在纽约。他的主人公尤金·亨德森(Eugene Henderson)是小提琴家,也是一个养猪场主,他莫名其妙地在他康涅狄格州的庄园里开了养猪场。养猪场离纽约不远,他还去纽约市57街找一个“叫哈珀以的匈牙利老头”去修小提琴。贝娄笔下的纽约满是像他一样的移民。亨德森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比做纽约地图:“我的脸就像是个终点站,就像中央车站,我是说——高高的鼻子张大的嘴,可以直达鼻腔,而眼睛就像隧道。”当他跑到非洲去寻找自我时,仍然用纽约的参照物来给自己定位。所以当听到国王达福的声音里带有一点低沉的嗡嗡声时,“让我想起了闷热夜晚纽约十六街发电站的声音。”
对自己的突然出走,亨德森最好的解释就是:“我心里有种骚动,一个声音总在那儿喊,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这个声音每天下午都会响起。”在非洲,亨德森在两个部落生活过,分别是和平的阿诺维和好战的瓦瑞瑞。这样两个对立的部落精神正是亨利·莫顿·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那套帝国话语的必备内容。亨利的任务是平抚或消灭那些战士,以及掠夺和平的部落。但令人吃惊的是,亨德森在两种社会中都没有建立起帝国式的掌控。
有一些章节讲述了亨德森在阿诺维村寨里的时光,小说在此转向我们八十天旅程中最后一次瘟疫叙事。因为缺水,牛纷纷渴死,漫长的干旱还在继续,而非同寻常的是,因为来了一群青蛙,村寨为干旱准备的蓄水塘却被废弃了。正如亨德森跟他们说的:“我相信自己非常明白遭受一场瘟疫是怎样的痛苦,也很同情他们。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只能把眼泪当面包来度日,我希望我不会给他们麻烦。”
出于同情,亨德森无法抗拒作为白种人的使命,挺身而出去帮忙解决当地人的问题。他做了一个愚蠢而惊人的方案,他制作了一个小炸弹,扔到蓄水塘里,想炸死那些青蛙。结果是蓄水塘被炸破,水都流光了。尴尬的亨德森就此离开了。他迟疑缺少决断,建立帝国式掌控的那些尝试都失败了,然后他来到了瓦瑞瑞的地盘,在这里他搬动了一个沉重的雕像,之前部落里从未有人能举起来过,以至他短暂地成为圣戈(Songo),或者叫“雨王”。当他搬起雕像之后,雨神奇地落下来。其实他这个胜利是被国王达福的敌人安排好的,他们想除掉国王,还需要一个继位的人。谁能比一个无知的,他们能控制的外人更合适呢。
国王达福交游广泛、熟习药理,英语也很流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亨德森已经很依赖于他。就像休·洛夫廷笔下的棒破王子一样,达福说着一口过于详尽的英语(“我估计你非常强壮。噢,太强壮”)。但贝娄不是在取笑达福,他将国王的话作为神谕,富于广泛阅读后获得的哲理。(“詹姆士的《心理学》是本非常吸引人的书”,他顺道对亨德森评价说)。达福对整个人类,以及对亨德森这个人,都有非常深入的见解。
“你阐释了很多东西”,他说:“对我来说,你是一个阐释道理的宝藏。我不会责备你的外貌。我只是从你的体格中看到了世界。在我对医学的学习里,这是对我来说最具魅力的部分,我曾独自对各种体型做过透彻的研究,形成了整套分类系统,比如有,痛苦型、贪食型、固执型……狂笑型、书呆子型、好斗反击者型,啊,亨德森-松戈,多少种类型啊,数也数不清!”
渐渐地,达福听着越来越像贝娄在纽约的精神科医生:“想象在你身上起了作用,它虽然闭塞,却是强力而原初的……你是各种暴烈力量的非凡融合。”在他养狮子的地窖里,达福给亨德森安排了一系列费力而危险的任务,迫使亨德森脱光了去触碰自己内心的野兽。这听起来像是个诡异的东方主义幻想,但实际上,贝娄曾接受过莱克学派医生的心理辅导,有两年时间,医生都要求他在心理辅导中全身赤裸,而小说正是对这段经历的戏仿和强化。
尽管这些心理辅导让人恼火,但和贝娄一样,亨德森也开始对自己,对美国有了新的感知,并能在回到家后让生活重回正轨。不再无止境地去“成长”了,他决定:“且看当下!打破灵魂的沉睡。醒来吧,美国!让专家们瞠目结舌。”贝娄的非洲是从纽约化身而出的,是纽约的倒影——一个也许能将美国惊醒的翻转镜像。
贝娄把《雨王亨德森》称作他最爱的作品,还说相较于笔下的其他角色,他在亨德森身上倾注了最多的自我。这样的判断似乎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像莫斯·赫索格和萨姆勒先生那样的角色更直白地表现出跟作者的相似。但就像笔下的非洲,贝娄用反转来创造了他的主人公:他自己是个穷犹太移民,而亨德森是个美国白人新教徒,还是个百万富翁,住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康涅狄格农场;贝娄虽然瘦小,但灵活英俊,而亨德森是个高大丑陋,力量惊人的摔跤手。通过将纽约、康涅狄格转换为非洲,将自己转化成形体、文化的对立面,贝娄找到了能把自己和国家看得更清楚的距离。他在巴黎待了几年之后回到美国,在巴黎,他和詹姆斯·鲍德温成了朋友,那时他已经准备好探索世界了。正如他心目中的达福,“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竟能遇上这样一个人物。是啊,旅行是值得推荐的。相信我吧,世界就是一个意识。旅行是思维上的游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