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尔丘克:在“怪诞”的文学罐头里想象未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新书《怪诞故事集》云首发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新作《怪诞故事集》的中译本,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十篇风格各异的短篇小说组成。这十个故事打破人与自然,人与物质世界的界限,超越时间和空间,以宏大的文学视野,带读者进入既怪诞又温柔,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其中每一个故事,都潜藏着对加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的隐喻和对未来的某种想象。

活动现场
8月3日晚7点,《怪诞故事集》云首发活动在单向LIVE直播间举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李洱,《世界文学》主编、翻译家高兴,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学院院长、教授、翻译家赵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教研室主任、《怪诞故事集》译者李怡楠,在直播间与读者一同分享托卡尔丘克的新作,以及她怎样以文学的形式提出关于当下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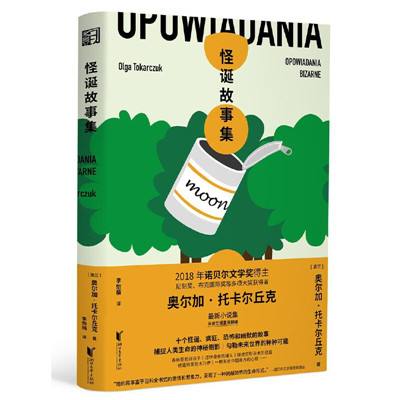
《怪诞故事集》书影
“怪诞”非荒诞,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延伸
托卡尔丘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波兰文坛,作品形式多变,善于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科幻等元素来观照波兰的历史与人类生活。曾凭借《云游》和《雅各布之书》两次荣获波兰权威文学大奖尼刻奖,六次获得尼刻奖提名;2018年《云游》获布克国际奖;2019年《雅各布之书》荣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奖,同年《犁过亡者的尸骨》入围布克国际奖短名单,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糜骨之壤》曾获201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怪诞故事集》是托卡尔丘克出版于2018年的新作,中文版由李怡楠从波兰语直接翻译。

李怡楠
李怡楠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翻译《怪诞故事集》的经历。她回忆到,自2016年起每年都会关注波兰文学的年度动态。2018年,她在整理当年波兰文学的年度动态时,关注到《怪诞故事集》。当时因为时间有限,没有读完全书,但看了不少书评。后来她在院长赵刚的办公室又看到《怪诞故事集》,表达了想翻译的意愿。李怡楠介绍说,“怪诞”(bizarne)这个词在标准波兰语中找不到,是托卡尔丘克结合法语词根自己创造出来的。法语词汇“怪诞”(bizarre)意思是“奇怪的、多变的、可笑的、超乎寻常的”。除了“怪诞”,《怪诞故事集》里还出现了不少托卡尔丘克自己生造的词,像《变形中心》里的“变形中心”、《拜访》里的“爱工”、《人类的节日年历》里的“雷控”等。

李洱
结合阅读经验,李洱认为,“怪诞”并非我们平时所说的奇幻或魔幻,而是指这个时代不断增加的各类信息超出日常认知后导致的一种不可控制的、不断分裂的感觉。托卡尔丘克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蘑菇”这一意象,在访谈中,她也提到过蘑菇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而是一种菌类。李洱把“蘑菇”看成解读托卡尔丘克小说的关键词,“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她(托卡尔丘克)的小说看作一种蘑菇,一种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介于神话思维和日常思维、介于人物传记和童话之间的故事类型。”
李怡楠在阅读和翻译《怪诞故事集》时,经常一身冷汗,译完好多天都不敢校对译稿,得先缓一缓。但她也提醒读者注意,托卡尔丘克小说中的情节虽然荒诞、不可思议,但都是现实中会发生的事情。“托卡尔丘克真正想表现,或者表现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东西。”
碎片化时代,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书写
《怪诞故事集》由十篇围绕“怪诞”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短篇故事组成:《旅客》讲述“我”在长途旅行中遇到的男子述说他幼年经常在床边看到的 “鬼魂”竟是老年时的自己;《绿孩子》发生在1656年的波兰,身为国王御医的“我”遇到两个和自然浑然一体的“绿孩子”,仿佛获得了治愈的解药;《接缝》里的主人公在衰老时突然发现世界的一切都变了;《变形中心》里的姐姐选择变成一匹狼,回归森林;在《拜访》里,世界仿佛沿着时间的轨迹在蜗牛壳里爬行,智能“爱工”的存在使世界变得精密、完美却也乏味;《万圣山》里的神秘心理研究揭开了关于修道院里木乃伊的一段阴暗历史……这些故事涵盖科幻、童话、史诗等多种文体类型,除了内容的丰富和杂糅之外,写作风格和手法也多种多样。

高兴
“托卡尔丘克的开放性和丰富性让人惊讶。”高兴称托卡尔丘克为一位博闻强识的作家,能在各个领域顺畅地腾跃、跨界,几乎每部作品都构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托卡尔丘克厉害就厉害在,她似乎掌握着十八般武艺,而且她的作品中,涉及到的学科领域太多了:人类学、心理学、植物学、医学……真的是需要一颗百科全书式的头脑才能创作出这么多奇妙的作品。”高兴将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归纳为“合成的文学”,并提到,托卡尔丘克小说中呈现的碎片化,绝对是一种精心安排的结果,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她实际上教会我们用怎样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她特别强调视角的转换,视角变化可能让读者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托卡尔丘克的很多长篇如同纸牌那样,可以不断组合,然后在这种不断组合的基础上获得新的意义。”
“托卡尔丘克的小说,用一个词形容的话,就是强烈的综合性。”综合性也是李洱观察到的小说在世界范围内近20年来发展的一种潮流。“从文体上看,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杂糅了游记、日记、童话、神话等多种形式,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特征。思维方式上,托卡尔丘克认为神话故事从未发生过,但神话思维一直留存于人间,她的小说带有强烈的溢出日常生活经验的思维方式。”李洱尤其注意到,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彼此之间有镶嵌作用的故事片段,通过相互“挤压”产生了化学反应。“这有点类似于互联网时代流行的一种碎片化,甚至可以说用原始思维写成的故事。看上去虚构的故事,却带有某种非虚构的色彩,这可以看成是托卡尔丘克对这个时代的写作做出的一种调整。”
李洱将当下形容为一种信息纷乱、不断向我们提供一些负面的恶的时代,他认为托卡尔丘克的碎片化写作与互联网时代大众传媒的发达密切相关,“现在所有作家都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如何面对网络、手机等现代通讯手段对人的冲击和挤压,以及传统的叙事方式在不断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如何做出调整。”李洱觉得,托卡尔丘克既迎合了这个碎片化时代,又通过写作对时代提出了质疑,表现出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本能。“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如何把握这个时代,如何用小说的方式应对这个时代,托卡尔丘克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我们来认识她,从而来审视自己。”
李怡楠提到,托卡尔丘克本人非常推崇短篇小说,她在波兰专门倡导短故事文学集。接受采访时,托卡尔丘克曾谈过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区别:长篇小说让读者进入一种缥缈的状态,融入到整个长篇中;短篇小说对作家要求更高,作家要有能够创造所谓“妙语金句”的能力。“托卡尔丘克还是很热衷于进行碎片化的短篇小说的创造,她在当今时代的文学丛林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她不一定用这种方式迎合碎片化的时代和碎片化的阅读方式,但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她的标签之一,她的短故事背后其实蕴藏着许多深刻的思考。”
正如托卡尔丘克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温柔的讲述者》中所说,“也许我们应该相信碎片,因为碎片创造了能够在许多维度上以更复杂的方式描述更多事物的星群。我们的故事可以以无限的方式相互参照,故事里的主人公们会进入彼此的故事之中,建立联系。” 这或许就是托卡尔丘克所提出的“第四人称讲述者”的要义:搭建某种新的语法结构,而且有能力使作品涵盖每个角色的视角,并且超越每个角色的视野,看到更多、看得更广,以至于能够忽略时间的存在。
既有波兰性,又具有非波兰性
托卡尔丘克是波兰历史上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此前已有显克维奇(1905年)、莱蒙特(1924年)、米沃什(1980年)、辛波丝卡(1996年)等四位作家获奖(此处不包括从波兰移居美国的艾萨克·辛格)。为什么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波兰走出了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现场作家、评论家对此做了一番交流。赵刚认为这与波兰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有关。像许多中东欧国家一样,波兰也是传统的欧洲价值观和现代文明的挤压的一块土地。在过去几百年,甚至是一两千年,波兰以及很多中东欧国家一直在欧洲文明圈的边缘,政治上的腥风血雨时常在此发生,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和交融。“他们内心一方面非常珍惜和怀恋所生长的乡村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卷入或带入现代文明的轨道上。包括米沃什等作家都曾深刻地反思这个问题。有挤压才会迸发,在重重重压的内心纠结的状态下,他们的文化达到了一种高度。”

赵刚
赵刚将波兰文学分成两种流派。其中一个流派以密茨凯维奇、显克微支、莱蒙特等正统作家为代表,特点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作品来表现民族精神,为国家代言。另一个流派是像贡布罗维奇、布鲁诺·舒尔茨、辛波斯卡等现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对波兰的民族性格和特点、波兰的历史和文化有客观而冷静的反思和批判。“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潮流存在的话,波兰文学很难走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恰恰有多元共存的现象存在,给波兰文学创造了一方肥沃的土壤。” 在赵刚看来,托卡尔丘克便诞生在这方沃土之上,同时在诸多方面突破了波兰文学的传统框架。“在托卡尔丘克的视野里,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也说不上人的世界和非人世界的区别,它是一个逐渐过渡、逐渐变化的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融合的世界。”
高兴表示,波兰出现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杰出作家,完全在情理之中。他将赵刚提到的波兰文学两条不同的创作思路简单地称为“波兰性”和“非波兰性”,并认为托卡尔丘克综合了两者。“托卡尔丘克既有波兰性,又具有非波兰性。“显克维支那种具有震撼的历史细节描写能力——她有,贡布罗维奇怪诞的那种想象力——她有,舒尔茨那种变形——她有,以及那种巧妙的暗喻——她也有。”在高兴看来,托卡尔丘克与波兰其他当代作家相比更具文学性,是当今中东欧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温柔地邀请读者进入她的文学世界
作为一位带有先锋性质的当代作家,托卡尔丘克并不拒绝讲故事。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她特别强调了讲故事对解构现实经验的重要作用。“文学是为数不多的使我们关注世界具体情形的领域之一,因为从本质上讲它始终是心理的,我觉得这里的心理其实关乎灵魂的意思,它重视人物的内在关系和动机,揭示其他人以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获得的经历,激发读者对行为的心理学解读,只有文学才能使我们深入一个人的生活,理解他的观点、分享他的感受、体验他的命运。”
高兴认为托卡尔丘克是一个建构者,而不是一个解构者。她的很多作品故事中有新的故事,讲述故事的方式是中断旧故事、然后再讲新故事。高兴说,世界和生活的真相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断地被打断,我们不可能完整去听一个故事,讲述一个故事。如果仔细阅读的话,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可以拼成很多完整的故事,这个需要读者的互动。“进入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世界,可能比较容易。但是要真正地深入领略她的文学世界,则需要读者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艺术境界、人生阅历,以及对世界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准确看法。”

托卡尔丘克
高兴表示,托卡尔丘克是一个具有灵魂意识的作家,这种意识使她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写作者。“托卡尔丘克是强调意义的,强调每部作品、每本小说起码都要围绕着一定的意义,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种迷人的、贴心的光泽。托卡尔丘克是一个绝对有魅力、有个性的作家,始终以一种温柔的、亲切的方式邀请我们进入她的文学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应她亲切温柔的邀请,走进她的世界的话,肯定会发现一个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的文学天地,同时又能让我们多多少少捕捉到世界和人生的真正意义。”
“托卡尔丘克是一个特别值得去细读的作者。”李怡楠补充道,“可能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读者,都可以通过阅读她的文字或者她的作品,找到自己的故事,找到自己对于托卡尔丘克写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词的一种对应的理解。”
《怪诞故事集》里,便有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十种生命经验。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泛滥、碎片化的时代,托卡尔丘克继续用她瑰奇的想象力,提醒着我们“文学”和“讲故事”的重要性。在托卡尔丘克看来,文学是“为数不多的使我们关注世界具体情形的领域之一”,文学还保留着怪诞、幻想、挑衅、滑稽和疯狂的权利。可以说,文学赋予了碎片以意义和存在感,重构了我们的生命经验,并成为我们对抗日益肤浅化和仪式化的现实生活的一剂解药。
据悉,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将推出的托卡尔丘克作品全系列(共九部),包括长篇小说《犁过亡者的尸骨》(即《糜骨之壤》)《最后的故事》《雅各布之书》等,以及小说集《衣柜》《鼓声齐鸣》等。该系列作品均从波兰语直接翻译,译者包括著名波兰语文学翻译家、学者张振辉、乌兰、茅银辉、李怡楠、林歆等。除《怪诞故事集》外,8月下旬还将出版小说集《衣柜》,长篇小说《犁过亡者的尸骨》和散文《玩偶与珍珠》也计划于年内与读者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