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创伤与男子气概 ——读海明威《我们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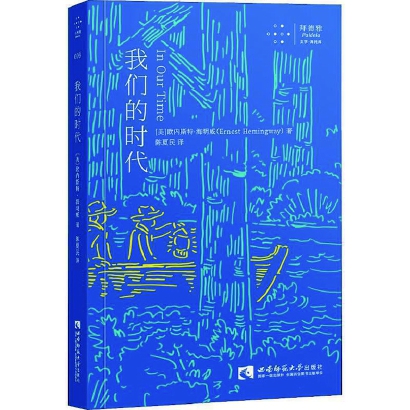
作为海明威的早期作品,《我们的时代》探讨的是战争以及战后社会的暴力、创伤和身份问题,其实验性的叙述结构既呈现了新颖的主题,也打破了陈旧的形式,而两者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主义运动密切相关,即大屠杀导致的幻灭感促使人们寻找新的艺术模式来拯救危机中的文明。海明威、伍尔夫以及乔伊斯等作家,都试图通过小说重新思考那些战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来尝试这种拯救。虽然每个短篇都以传统小说常见的“章节”形式呈现,但《我们的时代》却不是一本具有统一线性时空的小说集,而是一部在单一空间中将彼此对立却又相互关联的现实同时展示出来的作品,一如D.H.劳伦斯所说的“断片式长篇小说”。
《我们的时代》通过不同的叙事声音与模式呈现了战争与日常生活语境下的两面性。其中的故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新闻风格的小片断,一类是篇幅较长、更加小说化的短篇。前者的特点是令人困惑的匿名性、短暂的暴力爆发以及创伤性的内容与淡漠的叙述语气。与漂浮在叙事边界上的片断相比,短篇有着更大的叙事结构,更多的情节、背景和人物塑造。如果说短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从现实生活中截取的故事,那么片断则试图捕捉地狱般的梦境。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得读者很难将这本书作为一部具备统一特征的作品来理解。
这本小说集的另一个颠覆性元素是缺乏清晰的线性结构。收录的故事在时间和地理上并不一致,叙述者要么不为人知,要么经常变化,这使得读者很难厘清故事之间的联系。这种实验性的叙事风格导致了一种与现实脱节的效果,即战争的暴力与日常生活是分开的。然而,一旦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貌似分离的人物和场景实则交集在一个文本中,而通过强化战争与日常之间的联系,战争的恐怖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创伤性影响也就愈发明显。如此架构还意味着它鼓励社会在个人和公共层面就暴力和创伤展开更加开放的对话。
豹变式的成长历程
在貌似混乱的叙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和人物不仅将战争和平民生活联系起来,而且传达了暴力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作为贯穿小说集的一个人物,尼克第一次出现时还是小男孩,其身处的环境与时代也都与战争无关。与此相应的是,连接全书的战争情节,最初都被晦涩难明的小片段所取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叙事与尼克一起被推到了“一战”中间。与此同时,读者也逐渐明了战争期间平民生活和军人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人和集体所经历的创伤。如,在《印第安人营地》《斗士》和《军人之家》等篇中,我们看到个人的命运是如何被各种形式的暴力所塑造,而早期遭遇暴力、无法交流带来的创伤以及寻找权威,又是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那样的权威往往由理想化的男子气概来体现。
传统上,小说叙事的进展遵循一个特定人物的成长轨迹,而作为海明威人物谱系中的至爱,贯穿全书的尼克·亚当斯不仅帮助我们熟悉了书中陌生的结构,进而也让我们认识了更加陌生的战争和暴力。依据尼克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解读“沉默”中的暴力、男子气概和创伤主题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童年和自我的形成、青春期和对自我与权威人物的疑惑,以及成年和对世界的质疑。如此线性分析不但突显了贯穿全书的种种连接,而且还让我们领会到《我们的时代》是一本有内在凝聚力和统一主题的小说集,而不只是一些短篇故事和叙述片段的汇集。
含蓄简约的叙事艺术
作为小说集的第三个故事,《印第安人营地》标志着全书回顾过去的结束和故事线性发展的开始,叙述背景从欧战回到战前的美国,叙述声音也转为第三人称,而其将读者置于“他者”的地位却与前两个故事如出一辙。区别在于,前两个故事《士麦那码头上》和《所有人都醉了》,因其超然的叙述允许读者将叙述者视为受到创伤的他者,而在《印第安人营地》中,我们不能将创伤归到一个并非故事人物的叙述者身上。这样一来,读者不但成了被迫从远处目睹暴力事件发生的他者,而且还改变了小说的利害关系。这一转变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对所有人都有创伤经历的普遍性的理解,不管他们与战争有无关系。
当印第安妇女持续两天难产时,男人们躲得远远的,不想听到那“噪音”。无从揣测的叙述者看到的是“她躺在下铺,大肚子盖着棉被。她的头歪向一边”,而懵懂无知的少年尼克则天真地问:“爸爸,难道不能给她点什么,让她别再喊叫吗?”例行公事般实施手术的父亲回答说:“但她的叫声不重要。不重要,所以我听不到。”男人们对暴力的否认或忽视最终导致了更大的暴力:难产女人的丈夫令人费解和残忍的死亡。而难以捉摸的叙述者如法医勘探现场般记录下刚才还因脚伤待在上铺的男人的死状,“他的喉咙被切开,开口从左耳延伸到右耳”。“女人生孩子都会这么惨吗?”“爸爸,为什么他要自杀?”尼克是唯一直面这对夫妇命运的人物,而他淳朴的疑问隐含着质疑权威与暴力的种子。
尼克走向光明的隐喻和他的身体走向光明的时刻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巧合。海明威通过叙述的转变、尼克面对血腥场景时的行为变化,以及即将到来的日光细节,向我们展示了尼克在故事结尾的变化。故事以一个天真男孩的视角开始,幸福的他无视世界上的暴力、死亡和差异性。而在故事的结尾,这样的看法已悄然改变,它更接近尼克父亲冷漠而务实的世界观,但还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无情,因为“太阳正从山上升起……”与这美好的景色相对应的是他坚定的心态,“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死”。尽管尼克刚刚经历了死亡,但他年轻的视角一如既往,固执的他者立场根深蒂固。就像创伤和“他性”一样,这种否认死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潜意识,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经历。而这一切背后的人性真相是:正是他者视角导致了人际之间的隔阂、冷漠甚至暴力。
暴力与死亡的美学表现
尼克对死亡的拒斥是他对父亲拒斥暴力的别一种诠释。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立即改变他的观点,而是花时间去考虑他父亲的想法。在后来的故事中,随着尼克的成长和成熟,他向周围的权威人物以及他们为他构建的暴力和男子气概的传统概念发起了挑战。《三日大风》中的尼克和比尔,一边偷喝父亲的威士忌,一边炫耀他们关于酒的“知识”,在如此突显“男子气概”的反讽场景中,尼克对比尔观点的轻易认可与《印第安营地》中他未获承认的紧张相呼应:一方面他想要遵从父亲的观点,一方面又不愿盲目接受自己并不理解的东西;一方面他不想冒犯比尔,一方面却又在寻求父亲的指导。
两人之间有所显露的紧张气氛因各自父亲的更大差异继续加剧。比尔承认他的父亲“偶尔会大闹一场”,而尼克自豪地宣称他的父亲“这辈子从来没喝过一滴酒”。前者辩护道:“呃,他是医生。我老子是画家。本来就不一样。”画家用画笔描绘生命,而医生与死亡搏斗。如果酒精是应对创伤的一种方式,人们会认为离死亡更近的医生会有更多的创伤。然而,也许在海明威看来,对生死的审美表现比现实生活中的对抗更令人痛苦。正如《印第安人营地》所呈现的那样,对死亡采取务实态度的医生,无法与孕妇产生情感上的联系,也就无法体会那种伤痛。而面对暴力与死亡,如果有与医学方式相反的艺术方式,那它必然是感性且富有同情心的,因而给艺术家和观察者带来的创伤也就更大。
我们不妨将叙述者理解为尼克父亲的反面。与医生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和泰然自若的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叙述者巨细无靡的客观描述。前者的视而不见才是真正的冷漠,后者的尽收眼底却是深受创伤的表现。如果说不动声色或许是医生必需的素养,那么若无其事却是叙述者应对创伤的一种方式。因此,无论是在情节层面,还是在叙述层面,医生临床的无人情味与艺术家的感同身受之间的张力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身为艺术家的海明威在对待暴力的态度上却处于一个有趣的中间地带。他的小说是对生命与死亡的美学表现,但他的叙事方式却为艺术带来一种临床的方法。而他对这两种方式的融合又反映在男孩们对父亲暴力方式的融合上。
虽然语言最初是人类为了表达物质生活而创造的,但一个作家想要用它来呈现从未见过或经历过的战争仍是一件难以描述或无法言说的事情。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中如一个创伤深重的士兵,以不谈论的方式谈论暴力或创伤环境中,记忆的创造力与语言的可用性之间的冲突。我们必须在文字蕴含的“沉默”中来领会其间的微言大义。因为他很少给读者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能够对他的写作做出具体的结论。我们能得出的或许仅仅是一个有充分依据的推测。因此,海明威鼓励读者进行多种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阐释。读者在叙事建构中往往扮演着与作者同样重要的角色。许多晦涩的文本和开放的结尾,一如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明确答案的故事,抑或“一战”后很多人生活中那种令人心碎、违背逻辑的模糊不清与左右不定。
《我们的时代》作为海明威写作生涯的序章,其大师风范已显露无疑。行文简练而意蕴丰富,朴素的外表之下是内在的单纯与明净,简单的对话如高手过招般尽是机锋,尤其是叙事节奏的控制与叙事氛围的营造,整体结构的布局与具体层次的分布,以及黑洞般的空白与沉默,无一例外地显示海明威在短篇小说艺术上的精深造诣与杰出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