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译者姜乙:我如何翻译茨威格和黑塞
姜乙是一位“从幕后走到台前”的译者。姜乙并非德语专业出身,她本科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后留学德国。她的代表译作包括《悉达多》《人类群星闪耀时》《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黑塞《悉达多》因其充满哲学和宗教隐喻,是其作品中最晦涩难解的,姜乙翻译的首部作品即选中了《悉达多》,而她的译本在豆瓣评分中以9.4分成为评分最高的译作。在豆瓣短评中,姜乙的名字被不断提及,很多读者称其翻译“如歌如诗”“流光溢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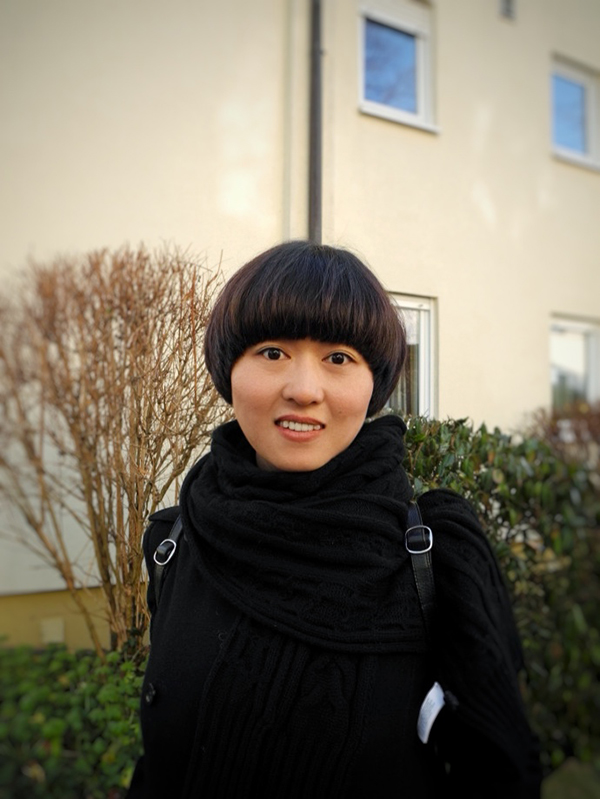
姜乙
最近,姜乙翻译的黑塞另外一部代表作品《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出版,澎湃新闻就此书和姜乙去年翻译出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及关于德语翻译的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访谈。
《人类群星闪耀时》:茨威格提供一种视野让我们感受历史
澎湃新闻:《人类群星闪耀时》包含了十四篇“人物特写”,但没有拘泥于一个人物,很多故事都是铺陈开很宏大的历史场面,虽然是历史中实有其人,但茨威格加入诸多想象,比如在托尔斯泰那部分,用了三幕剧的形式还原了他在人生末端决定离家出走的前后场景,还有《亨德尔的复活》中许许多多对于亨德尔怎样得到神示一般拥有了灵感,有些内容是很私密和个人化的,您怎样看待有很多“脑补”成分的历史写作?
姜乙:我记得我在译后记里表达了对这本书的看法:首先我试着解释了“特写”这个概念的意思。我先从把握概念谈起,他为什么称它为“特写”。我写了一些我在词典上发现的解释,当然是德文词典上针对这个德文词的解释。我的理解是它是茨威格——他像一位艺术家完成一幅画作一样——描摹历史的瞬间和片段,他在一幅画面上凝固了历史。他以不同的体裁描写了十四幅画面。所以我并没把它理解为一部地道历史书。
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既是他对历史的描述,又是对历史的想象。它是一部艺术作品。读者不仅能从他的文字中了解了历史,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历史,感受历史,欣赏历史,并在阅读中有自己的想象和思考。这是一种美好的体验。他提供了一种选择:假如我们愿意承认,历史的原态并不真正存在,或只是相对存在。让我们思考:我们如何/是否能求得历史的绝对真相?历史的叙述者是否总是时代的产物?他或她是否能完全摆脱所处时代,摆脱个人的烙印、角度、经验和意图?它流传至今,是否具有可以吸收和借鉴的价值?可能我们会在阅读时获得更多的享受和启示。
澎湃新闻:你的专业是音乐,一些读者在阅读时都谈到你的语言的节奏和韵律感。音乐怎样影响到翻译?
姜乙:我大学本科念的是音乐学院,专业是歌剧演唱。今天我只是一个听众或音乐爱好者,我喜欢古典音乐和爵士乐。音乐和翻译好像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但怎么说呢?音乐对人的影响或者说音乐与人的关系,似乎是个宏大的命题:石器时代人类就雕刻笛子,格陵兰岛人通过说唱比拼来解决纷争,足球迷们会迅速化身合唱团团员,歌唱提高人的免疫力,演奏钢琴可以提高数学成绩,莫扎特的音乐被证实可以缓解病人的压力……音乐可能隐藏在每个人的基因里,印刻在每一种文化形象中,影响我们的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我们天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翻译,我想,应该对书里的每个人物感同身受。作为一个热爱巴洛克音乐或者说亨德尔音乐,和对他这个人略知一二的译者,可能对这一章更有好感,更亲切。如果说影响:某些时候,我试图做个勇敢的人,在翻译时试着打破某种母语中人们习惯的节奏或说话方式,打破我自己习惯的节奏和说话方式。这非常难。比如完全直译,一对一,试图造成某种让人心动的陌生效果……但这些不过是给人自大印象的泛泛而谈。
澎湃新闻:关于《人类群星闪耀时》,很多读者都论述到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作者澎湃的激情,回看历史时会让人心旌摇荡的那些瞬间,书中很多内容都具有鼓动性的断言,比如“人生中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在富于创造力的壮年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命运渴望强者和暴君。多年来对这几个人: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奴颜卑膝地百依百顺。因为命运无以抗拒地热爱着这些和它相像的不可捉摸的生灵。”在翻译中怎样去有效传达这种文字中的激情,是否需要译者对于语言的力度和文化语境等比较强的感受力?
姜乙:我认为要彻底理解茨威格是不容易的。我的体会是,他在这本书中,借用描绘一些历史画面,历史特写,反思了人性,反思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举动和作为。但他并没有下给论。他不是历史学家,他选择这些事件,一方面,他倾尽笔墨,表现主人公的创造力,表现人的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他又表现了这种创造力,这种智慧和力量的有限性。
在他的笔下,人一面伟大,一面渺小,一面崇高,一面卑劣;时而像神一样,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时而又非常脆弱,一个小小的外力,一个突发事件、偶然事件,就能轻易把人打败。也可以说这是他对命运,人生和人性的认识。他借用了这些历史画面,故事,通过他细腻的刻画,反省了人类自身。他对时代的变迁保持着一个艺术家,作家的敏锐和警醒。
同时,茨威格也提出了问题:我们人类的智慧、灵性和力量,究竟要用在哪里,是为我们自身带来福祉和和平,还是为我们带来灾祸和战争。对不可阻挡的、不可逆转的现代性和物质主义,对古老传统价值受到的冲击和撼动,对和平的企盼和无视,他在赞叹的同时,表现出一种无力感。他只能用细腻的笔触,去一笔笔勾画历史,一边勾画着,一边唉声叹气。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似乎能感受着他在历史面前的各种忧思。
澎湃新闻:《人类群星闪耀时》也被认为将历史的局面太归咎于一个偶发事件和一个偶然的人,过分强调宿命,作者也有很多评述是不断强化这个历史瞬间的巧合、用各种角度去促成这个瞬间。您怎样看这种叙述方式?
姜乙:按照我在一本叫《凯若斯》的书里学到的说法,我不妨抄几句,或许有点启示:据希腊人的古老传说,“时机”为众女神之一,其角色有点像罗马人传说中的命运女神。从希腊诸神的谱图中可以看到,“时机”身上有展开的翅膀,手持天平,一副在世间主持公道的样子。奇怪的是,她前额有密发,后脑勺却光秃秃——据说意思是,谁不会把握时机,就只会拽不住命运的后脑勺(等于拽不住命运),另一个解释说,谁如果不把握时机,谁的脑袋就会被剃光(倒霉)。按哲人的说法,时机是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后来圣保罗用这个词来描绘耶稣基督悄然来临的时刻。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把握住决定性时刻至关重要。
那么与其说“茨威格把历史的局面归咎于一个偶发事件或一个偶然的人”,不如说他提醒我们留意一些“时机”,一些悄然来临的时刻?
《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黑塞完成有说服力的自我释放
澎湃新闻:你翻译了黑塞的两部作品,《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在黑塞的作品序列中是怎样的位置?
姜乙:黑塞于1919年以辛克莱为笔名发表了《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时年42岁。之前他曾出版处女诗集《浪漫诗集》(1899)《乡愁》(诗集,1904)《彼得·卡门青》(1904)《在轮下》(1906)《此岸》(短篇小说集,1907)《盖特露德》(1910)《温泉疗养院》《印度纪行》(1911)和《孤独者的音乐》(诗集,1914)《艺术家的命运》(1914)等等。曾经历少年退学,做钟表工厂学徒,书店店员;经历结婚,生子,亚洲旅行(新加坡,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和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过战俘慰问工作),认识了罗曼·罗兰;经历了父亲去世,妻子患精神病,个人精神危机。44岁他出版了《悉达多》。
澎湃新闻:《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也被认为影响并催生了垮掉的一代,您可否介绍,此外《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还影响了哪些作品?
姜乙:美国读者从1950年代开始熟悉黑塞的作品。之前几乎没人读过。起初是少数所谓社会边缘人,诸如垮掉一代的追随者对《悉达多》《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荒原狼》和《东方之旅》感兴趣。1960年代初,他的作品又在超验主义者中,在即将兴起的迷幻运动中广泛传播。1965年,美国掀起黑塞热。他作品中的动机和主题引起反传统文化的年轻读者的强烈共鸣:避世,远东的精神性,反叛庸众和呼唤个性。当然,这种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建立在对其作品广泛的解读上,尽管这些解读并非完全符合作者的意图,却反映了时代的基调和气氛。推动黑塞热潮的主要人群是嬉皮士、大学生、美国中产阶级和日益增多的反越战人士。黑塞被塑造成流行文化的大师和英雄。美军从越南撤军后,美国民众的情绪有所平复,随着黑塞热高潮退去以及新青年运动的建立,读者对黑塞的兴致降至“正常”程度。黑塞作为德语作家在美国独一无二的成功故事,是典型的时代现象,并将黑塞坚定地植根于美国文化中。
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注意到,在 1950年代的德国,《明镜》周刊曾称黑塞为不合时宜的作家。著名德国文学评论家马瑟尔·莱希·拉尼奇认为黑塞在美国掀起的热潮不可思议。他无法接受将黑塞和托马斯·曼相提并论(尽管托马斯·曼本人十分推崇黑塞)。黑塞不过是个三流作家——拉尼奇的这番话甚至今天还毁灭性地影响着德国媒体和大学对黑塞的评价和接受。尽管马瑟尔·莱希·拉尼奇随后继续宣称,至少黑塞在有生之年是位博览群书的作家。另外还有一位叫卡尔海因茨·德士纳的德国批评家,在他1957年发表的批评文章《媚俗,习俗和艺术》 中称黑塞为具有破坏力的拙劣作家。德国评论界认为黑塞是个有点儿守旧的小说家,是位19世纪的内向性诗人,一个不错的青年读物作家。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在美国被反越战人士和拒绝服兵役者吹捧,不过是嗜酒成性的美国人的奇想。
这是读者和文学评论家之间的黑塞,也是评论界的轻视无法影响迄今世界各地读者喜爱的黑塞。
澎湃新闻:《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和《悉达多》都被认为是受到荣格心理学理论的影响,你可以分别谈谈吗?
姜乙:黑塞于1916年38岁时进了鲁塞恩的一家疗养院,认识了精神病医生、荣格的学生朗格。离开疗养院时,黑塞虽然感觉自己并未痊愈,但他意识到,他走上了通往“伟大自我”的道路。之后黑塞和朗格继续约定治疗,期间也有通信来往,他还写了一些借助心理分析的带有自传特性的童话。他记录了《精神分析梦境日记》。这些梦境反映了他的恐惧不安和自卑情结——或许和他年少时接受的虔信教育中的自我审查有关。父亲的形象在他的梦中是上帝的形象,是威权和掌控。上帝不停地注视着他。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让黑塞认识到,他曾塑造了一个错误的自我,一个美好和谐却虚假空洞的世界。黑塞认识到,他拥有了重新阐释他生命中宗教基础的机会。对荣格来说同样,神圣事物就是“自我”。这些让黑塞对“自我”的认识更完善,更清晰,更系统。荣格心理学作为女性灵魂形象的阿尼玛原型,在黑塞的作品中意味着人类的天然本性,是神。而在最后在野战医院,辛克莱和德米安的再次相遇似乎意味着内在和外在,梦境和现实的一致性。
《悉达多》除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外,我们知道,黑塞的精神世界里还有《奥义书》《薄迦梵歌》《道德经》和《论语》以及对这些思想的洞见和分析。在这部书中,佛陀的慈悲,耶稣的爱,道家的无为不争与欧洲的自我实现融为一体。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新高度。
澎湃新闻:《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和前两年比较火的《我的天才女友》有同质化的内容,比如都有引领者,《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中第一个、且一直挥之不去的引领者就是德米安,德米安的任务是引导“我”去克服自己的懦弱,并以截然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完成成长的蜕变。而中国的作品中好像这个引导者的形象则常常是长辈、教师,就您的理解和观察,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姜乙:德米安是黑塞梦中的人物。黑塞和荣格见面后做了个噩梦。这在他1919年9月的记录中可以获悉。梦中他和德米安在两次角斗中失败,之后德米安没有离开他。德米安是个拥有双重形象的造物主,也可以说是阿布拉克萨斯神。从开始就是一个将有意识和无意识完美结合的强大个体。他将可朽事物和精神上的自我意识结合为一种牢固的力量。可以说这个梦启发黑塞创作了《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是他的灵魂自传。在《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中,黑塞所完成的是一次有说服力的自我释放,以及在对荣格的精神分析的认识中,艰难寻找自我的过程。正如德布林所说,“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确定性,触及了最根本的精髓。呈现了原出的非道德性。”
如果我们复杂地认为《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只是披着成长小说的外衣,或简单地认为《我的天才女友》只是两个女孩的友谊,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就是我们,都不得不寻找“自我”,都不可避免地在亲情友情爱情中成长。所有扑面而来的人和事都让我们发现和思考,都是我们的领路者。
“比较重要的是我在夜晚独自坐在灯下的书桌旁的那些时刻”
澎湃新闻:《人类群星闪耀时》《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都是之前有很多译本,前者有十几位译者先后翻译过,再翻译时是否要借鉴他们或者规避掉他们的问题,在翻译界是否存在类似“影响的焦虑”这样的情况,即被第一个译本的风格、形式等影响?
姜乙:在翻译这些书时,我恐怕没有权利和资格去借鉴或规避别人的问题。翻译对我来说是件个人的事。类似于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搭积木,一个人做数独。我还相对是个新手,还对翻译充满好奇和冲动,还没有幸成为“翻译界”的一员,至少我自己认为我没什么资格,所以对这种“焦虑”不是特别熟悉。坦白说,我没有这种焦虑。
澎湃新闻:你可以描述一下在德文原本中看到的茨威格和黑塞的写作风格吗?比如他们各自爱用的句式和关注点之类?
姜乙:黑塞的“诗意”“诗”或许可以换个说法:一种直接、有力和表现力的结合。茨威格给我的印象是准确和优雅。
澎湃新闻:您的翻译策略,是尽可能地接近中国的阅读欣赏习惯还是某种程度上保留德语的意味?
姜乙:翻译时,可能需要采取比较综合的方式。有时直译,有时意译,有时断句,有时保持长句的张力和紧张度。
澎湃新闻:你翻译了《人类群星闪耀时》《悉达多》和《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选择一本书来翻译时的标准是怎样的?翻译一本已经译介了很多次的名作,是否也要面对来自原作者本身的名气的焦虑。
姜乙:这些书是出版公司的建议,我自己又很喜欢,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的合作很愉快。我想,我没有翻译过这些书,对我来说是新书,不是吗?喜欢应该算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谓“功劳”和“发现者”对我的翻译工作而言是陌生思路,陌生词汇。我没有这方面的愿望。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我在夜晚独自坐在灯下的书桌旁的那些时刻,其他的我不会特别在意和考虑。
澎湃新闻:你目前选择的书都是名气比较大、做过很多译介尝试的作品,这是否和你个人的偏好有关,还是背后有出版社的诉求的影响?
姜乙:谈不上偏好,只有三本书和一些短篇小说。过去翻译过的一些短篇小说收在《德语文学和文学批评》里,是我自己的选择,完全不会被注意。但我很喜欢。这三本,编辑问我这本行吗?我说看看,首先我得能行,觉得合适,不会是个痛苦的翻译过程。之后我说好吧,开始吧。好像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