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小说更像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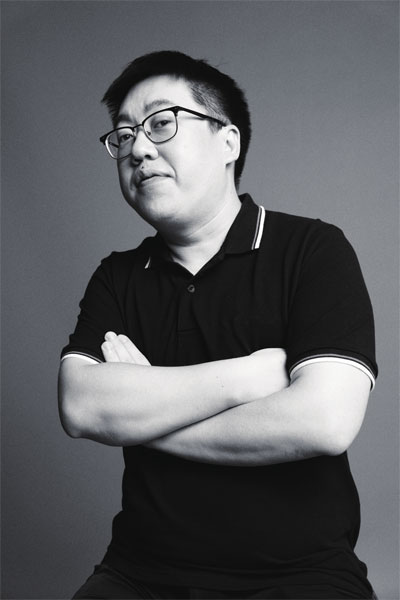
班宇,1986年生,沈阳人,代表作《冬泳》。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
很多00后认识班宇,是从易烊千玺的Instagram上发的《冬泳》书封,这直接导致了《冬泳》一书的多次加印。易烊千玺说,《冬泳》的阅读体验很奇妙,“里面的人很不一样”。有媒体甚至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易烊千玺拯救了严肃文学”。
其实,作为一个跨越了“纯文学”和新媒体边界的作家,班宇的受众群体非常广泛,其中不乏90后00后。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喜欢阅读班宇的作品?
班宇承认,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很多读者确实没有经历过,他们对这本书产生兴趣,可能是对那个时代人的命运感兴趣。对于班宇自己来说,他有印象的时候也已经是一个相对中后期的阶段了,变革应该从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情感结构一定是共通的。”
班宇说,在读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时,对于他们所描述的那个时候的国家的状态、人们的状态,也很感兴趣。因此,无论时代背景是如何,科技发展是如何,人们心中的那些景观,人们心中的那些念头和想法,可能是同一种“噪音”所驱动的。
从乐评人到文学创作者
在成为作家之前,班宇做了将近十年的乐评人。从2006、2007年起,他开始为一些音乐杂志撰写乐评。他说,那时候的自己是个普通的文艺青年,平时喜欢看电影、读书,也尝试过写小说。只是写得比较少,也从来没有拿出来过。对于那时候的班宇来说,他喜欢音乐,乐评也是他愿意接受的表达方式。
2015年前后,新媒体兴起,很多媒体都面临着转型和创新的问题,一些综合类杂志也砍掉了音乐板块。那段时间,班宇没有什么稿子可写。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乐评虽然也是一种独特的创见和表达,却始终受制于音乐作品本身。班宇说,一方面,觉得能承载乐评的媒体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自己也遇到了比较大的困境,不知道怎么能够写得再好一点。因为已经写了将近十年,可能会形成一些固定的范式,写乐评这个事儿好像变成了一种空转。这是他不想看到的状况。
正在这时,班宇的一个在豆瓣做编辑的朋友问他,“你要不要过来写个小说试试?”班宇的回答是愿意。因为对他来说,相比于乐评,“小说更像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容器,它可以是各种形态,相对自由一点。”
在豆瓣的征文大赛,班宇写了关于铁西区的四个小短篇,后来又加了一篇,一起收录在《冬泳》里,叫做《工人村》。这组作品在豆瓣上拿了奖之后,班宇觉得,这份事业好像是可以继续的,于是又写了几篇,就有了《冬泳》中的《梯形夕阳》和《盘锦豹子》。后来,《小说月报》、《上海文学》和《收获》等期刊,陆续刊发了班宇的作品,班宇从此开始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班宇坦言,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权衡新写的故事的走向和脉络,跟以前的相比,哪一个是自己更想要的,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也只能在一步一步的写作和修改里边,慢慢磨出来,碰出来。这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但在这种痛苦里有很大的愉悦。
班宇认为,自己的写作并不是完全顺畅的,写每一篇的时候,都遇到过大大小小的麻烦。他回忆道,“写《肃杀》的时候,我的改动特别大。稿子写完之后,我觉得整个的叙述和感觉都不对。我之前是讲了一个故事。三分之一之后,我就讲了一个其他的故事,但是后来我觉得,我不想那么做。因为至少在这一篇小说里面,故事性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是把大家带回到一个场景的氛围当中。因为如果真正把氛围写好,把整个时代的状态写进去的话,人的困境和人在困境下的种种行为,并不是不可解释的。读者也许会从这儿得到更多的东西。”于是,班宇删掉了原稿的三分之二,几乎是将这篇小说推倒重来,才有了今天的《冬泳》中的这篇《肃杀》。
作家要信任自己的写作
班宇指出,所谓信任自己的写作,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写自己经历过的场景,或者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再从这种感受出发,倒推出整个时代的景观。这也是班宇在文学生活上的一个根源。
班宇说,“我的小说除了某几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原型之外,大部分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虚构的故事情节,而不是虚构的情感经历。对于在小说里面投入的情感,我从来没有想过虚构。我不会去太想写那些自己不太信任的文字。我只是把那种真实的情感和经历,在小说里面,做一个虚构的处理。”
班宇非常认同博尔赫斯的一个说法,所有的文学都是心理文学。也就是说,现实完全等同于想象,小说里面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同等真实。在班宇的理解里,真实是作家试图忠于自己的一个原则。想象并不是一种空穴来风,而是跟我们能触及到的所有的现实一样,也是真实的一部分。
在自己的写作中,班宇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姿态。他说:“在写作的时候,某一阶段是重新梳理自己的记忆和感受,然后是重新梳理自我的秩序。这样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虚构化的表达,但在文本下面隐含着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等,又是真实可触的。我可能一定要嗅到某种味道,或者说,感受到某个让我觉得真实可信的细节,才能去踏实地进行虚构的处理。”
在《冬泳》这个短篇里,主人公“我”杀死“东哥”这个情节,引发读者广泛的争议。对此,班宇表示,“我的写作没有把东哥杀死,大家是不是对这个人的生命力有一点误解,这只是揍一顿,这个人没那么容易死。至少是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没有要写这个人的死亡。这个故事里面,包括最后那些东西,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是,很多人会遭受到一种不公的结果或者不公的命运。”
班宇想表达的是,很多事情看似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可能在某个人的某个节点上,我们也做出了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决定,也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他说,“我只是想讲,人在某一时刻所遭遇的这种困境。在这个困境里边,如果选择死亡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解决方式,也不是一个有效的抵抗方式。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把它落实来讲,其实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死亡。”
班宇笔下的人物,始终生活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当中。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在一代人或者说那个时代的所有人身上都有体现,无论他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甚至是已经在家养老,这种时代的变化,会映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说,“我只是讲,这种映射的强度和力度,因为大家面对艰难,最终会找到自己的应对方式,或者积极,或者消极。就算是消极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去选择一种死亡,更多的可能是,大家终究会挺过来,或者是找到一种自己舒服的方式来把这段时期度过去,只是这样而已。”
产生共情并不困难
《冬泳》里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下岗”“买断工龄”,这一背景关乎1990年代,也关乎东北。作为东北人的班宇,对近两年来的“东北热”也有自己的看法。班宇认为,“我觉得一方面是追忆,另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的某些现象,在今天也能找到一种映射,这个东西是要超过我们所描绘那些时代的元素。”
班宇以东北音乐人董宝石的《野狼disco》为例,他说:“这首歌讲的是2000年前后,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歌厅里面的东西。但是今天,大家依然会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和共振。他唱的不仅仅是上游的时代,也有对于今天的一种诠释。”在班宇看来,大众对东北文化的关注并不完全是一种猎奇的心态。也许最开始有这样的意味,很多人不了解东北,不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再加上通过之前的小品或别的,大家会把东北人卡通化。
班宇认为,在认知东北的过程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复杂性在里面,没有办法用几个词语,或者是几个标签,就把东北和东北人概括了。”班宇这样概括东北在整个中国的位置,“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地域里,所有人的命运都可能相似。只不过有的时候你走到前面一点,有的时候你又走到后面一点,所以可能给大家的感受更多一些。这种感受是真也是假,有的时候你觉得它跟你的记忆是完全相吻合的,有时候你又觉得它好像离你很远,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受。”
在班宇看来,某一个地域的变迁,整个文化结构上的变迁,并不是一个一直向上走的过程。他指的并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一定是一个像波浪似的、有高潮有低谷的循环的状态。在谷底的两个时期的人们,一定会感受到一个相同的状态。同样,对于站在峰顶上的人们来说,也会看见曾经的低谷是什么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