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野蛮”到“神人合一”:周作人的浪漫主义冲动
“你不明白吗,”我说,“我们先从给儿童讲寓言(mythos)开始,寓言从整体看是假的,但是其中也有真实”
——柏拉图《城邦》
与一切活的合一,在蒙福的自我遗忘中重返自然的宇宙,这是思想和喜乐的巅峰
——荷尔德林《旭裴里昂》

周作人(1885年-1967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就兴趣的广博和思想历程的漫长与曲折而言,无人能出周作人其右。1920年前后是周作人成为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之一的关键期。我们只需把目光投向这个短暂的时期,周的文学观和哲学观,就已经显示出微妙的、不容忽视的变化和修正。这些变化和修正之所以引入瞩目,尤其在于周作人作出它们时,有明显的挣扎和痛苦的痕迹; 而它们之所以重要,乃缘于它们是理解周作人未来发展的一把钥匙。尽管它们显得零散、不成形也不系统,但在1918年末至1921年底,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变化,明白无误地昭示出一种趋向,而这种趋向所指,我称之为浪漫主义。认这一趋向为浪漫主义,对我们理解周作人此时和此后的思想世界有工具之效,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也有很重大的辐射意义和连锁后果。
我对浪漫主义或浪漫派这个词的使用,是遵循了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确立的批评传统。这个传统把在主要是世俗的处境中,在内心里对于拯救的寻求,看作是“浪漫派的崇高主旨”。 从1918年末以降的三年里,周作人的文学观和哲学观,与浪漫主义的某些最核心的方面均相吻合。目前迅速扩大着的周作人研究,迄今尚未把周作人的思想纳入浪漫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框架中来考察。但是倘若不把它纳入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语境里,就将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解决属于他后来生活的许多问题,同时也会让我们很难获得对“五四”时期更深刻周密的理解。在本文中,我将通过考察周作人的白话诗和在1920年前后的那些重要的批评文章——特别要集中考察和儿童文学、文学中的超自然主义、超验主义和社会乌托邦等有关的问题——来证明和阐发周作人的浪漫主义倾向。通过识别他所接受的资源、追踪他的某些文学和哲学构思的形成过程,并通过阐明它们在跨国的、历史的、思想的和文学的背景中的意义,我将试图实现历史和理论的融合。我的目标是要提出一种清晰的理论和历史模式,这个模式将展示为同浪漫主义完全吻合。
从前,有个寓言:《小河》
今天,周作人最长的白话诗《小河》 曾经引起轰动、以及它被称为白话诗的“第一首杰作”这一事实,可能会让中国普通的诗歌读者感到惊讶。但是周作人的弟子、批评家和诗人废名(1901-1967) 193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讲新诗时,就这样褒奖过这首诗。在这个讲座中,废名还解释了,这首诗在白话诗歌史上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在1919年前后带来一种“新鲜感” ,而这种新鲜感建立在“其所表现的东西,完全在旧诗范围以外了”。另一位同时代的批评家朱自清(1898-1948),在树立新文学经典的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卷导言中,对这一评价表示赞同。 两位批评家都暗示,这首诗除了与传统诗歌形成鲜明的对比外,就是与当时所发表的其他白话诗相比,也具有创新性。废名特别指出,是周作人的这首《小河》,而不是胡适(1891-1962)那些被认为是打响了反传统诗歌战役第一枪的早期白话诗,让一种全新的诗学破土而出,并因此标志着白话诗与传统之间根本的决裂。这就是为什么这首诗,用废名的话来说,被看作“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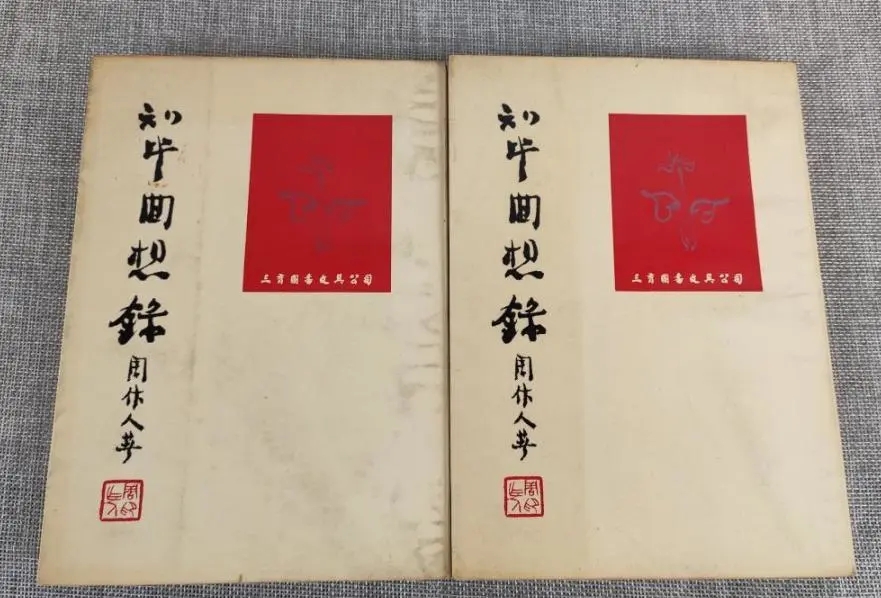
《知堂回想录》1971年版,周作人著
周作人自己也很看重《小河》,他晚年写成的自传《知堂回想录》,就用了两章(131和132)的篇幅来记叙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因而可以说,这首诗受到的关注是独一无二的,超过了他所有其他白话诗。在关于《小河》的这两章中的第二章里,周作人用大量篇幅引了他在1944年所写的一段关于《小河》的札记。 这则札记含有对这首诗的形式的论述,宣称这首诗的形式可以归为“譬喻”。如今,“譬喻”一般理解为“明喻(simile)”或者“比喻(metaphor)”。然而,在周作人那里,这个词所指的,必是某种类似于“寓言”的东西。在现代汉语中,“寓言”这个词常被视作对应于英语的“fable”,而fable在英文中本义是虚构的故事,其中虚构是这个词的核心意义,同事实或纪实相对立。 “譬喻”应被理解为“fable”(寓言),尤其因为周作人曾在别处提出,形象化的譬喻表现(figurative representation),或者说象征手法(symbolism)——周作人将它等同于中国传统诗学中三个基本概念之一的“兴”——应该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要表达方式。
照他看来,在传统诗学的三个基本概念中,“兴”较“赋”和“比”更为根本。按照这种对中国古典诗学的主要概念所进行的重新阐释,周作人自己的这首诗就必须放在“兴”——即形象化的譬喻表现——的范畴内来考察。
《小河》所讲述的,是一条流动的小河被一个农夫的堤堰所截的故事。这首诗包含会说话的稻苗、能表情活动的桑树和小动物等形象。它们都能用语言来表达对受阻遏的小河的同情和对它们自己状况的担忧。显然,这首诗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比”。它与“赋”——这个词往往和它在古典模式中可见的那种铺张、甚至浮夸的文风是同义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从风格上说,它是那样的朴实。作为一个明白无误地用非现实主义的模式(会说话的水稻和动物)写成的故事,《小河》所讲的故事,是靠“象征手法”,即靠“形象化譬喻”,来传达其含义的。出于这个原因,按照周作人的术语定义,这首诗应该属于“兴”的范畴。“譬喻”,作为“兴”的一种形式,可以被翻译为“fable”,因为一个“fable”就是“一个虚构的、与超自然的或者非凡的人物和事件有关的故事”,而且往往含有某种实用的教训。 由于《小河》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利用了被赋予生命和智能的物体作为故事中的人物,以此来传达,据作者自己的说法,某种伦理的和政治的信息,因此,《小河》符合“fable”(寓言)这个词的所有定义。

1923年4月,鲁迅与周作人、爱罗先珂合影
如果我们把前面两位批评家对这首诗的评价,同作者自己对它的形式的评价结合起来,那么把这首诗看成是一个突破,就很有理由了。因为和当时的其他白话诗相比,《小河》中那个详尽的虚构故事是很独特的。比如,它与胡适早期的白话诗相比,就有明显的不同。尽管胡适率先试验写作白话诗,但他对抒情诗的理解是诗主要还是由景物的瞬间构成的,要么就是为诗人的情绪或转瞬即逝的情感状态所引导支配的。 在风格和语言方面,《小河》与沈尹默(1883-1971)的白话诗相比,也很突出。沈尹默在新诗运动之初发表的那几首白话诗中还保留着明显的传统诗歌的痕迹,读起来很像乐府和词。 与那时产生的大多数白话诗不同,《小河》并不是一幅风景素描, 而是包含着一个完整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寓言性的,或者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是用了“象征”手法的。同时,与同时代的很多白话诗不同,《小河》的语言是平实的、不做作。特别是在废名那里,诗歌构思的整体性和完全,以及句法的整体性,是现代诗的两个决定性特征, 因此,正是这个用平实流畅的语言叙述出来的虚构故事的完整性,使得这首诗在废名眼里,成为白话诗的第一首“杰作”。
一个更理论化的解释,可以进一步揭示周作人的叙事诗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中国传统诗学,在其形成阶段,摇摆于表现说和教化说之间。 其中表现的倾向,是这两者中更为根本的,这在郑玄的《诗谱序》中,表述为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诗言志”。 当“志”受到了道德原则的规范时,诗的表现说,就变成教化说。这种表现理论,和西方诗学的根本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将诗歌看作摹仿。 通过语言的中介来摹仿人类的行动,就必然导致叙事或者讲述故事,有时候还要加以戏剧化,在近代以前,就是竖琴式诗歌也有很强的故事甚至戏剧化成分;与此相反,表现观的诗歌理论不利于编造或者讲述故事。 实际上,它更有利于那种直接的主观感叹的泛滥,这在早期白话诗中经常能见到。同这样的表现论相对立,诗人的角色——他个人的天赋、感情或者欲望——在西方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才得到很大重视。 对诗歌本质的表现论看法,在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后果就是,虚构性故事并没有占据突出的地位,相比之下,西方诗学从一开始就在故事和诗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密切的联系。比如,在《城邦》中,柏拉图就用“mythos” 这个词——在英文中,或译为寓言(fable),或译为故事(story), 或译为志异(tale)——来指像荷马那样的诗人所讲述的虚构的故事。 后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篇首,将mythos(故事情节)的组织,列为一首好诗所必需的几个根本特征之一。
还没有证据表明,作为首个或者首批学习古希腊语的中国人,以及第一个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系统了解的中国人,周作人是在研究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写下这首诗的。然而,《小河》在根本上背离了本质上是表现派的中国诗学的基本原则,采用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的欧洲诗学的最基本的宗旨:作诗就是作故事(poesis is mythopoesis)。 然而如果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是其直接来源,那么周作人在《小河》中是如何抵达西方诗学的这一根本原则的呢?
……这寓言是儿童一样的
《小河》是一个採用了万物有灵论(animism)的寓言。其中的角色是会说话的植物和能表情的物体。就万物有灵论而言,它在本质上与主角是一只会说话的猴子的《西游记》没什么不同,也与几篇其他没有《西游记》那么有名的中国传统小说或者传说并无不同。这类小说或寓言包括十五或十六世纪的《中山狼传》,周作人曾把它同自己这首诗相比较。
然而,这样的类比会引起麻烦,特别是在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时候:这些传统小说中的万物有灵论,与“五四”作家所倡导的科学与人道主义人生观岂不相冲突吗?万物有灵论的寓言,比如《小河》,不也同此前不久周作人所谴责的传统小说一样,犯了宣扬迷信的罪吗? 这种超自然的寓言,难道不应该从周作人及其“五四”的同仁作家们所设想的新文化中清除吗?——就像柏拉图要把荷马从城邦中驱除那样,因为据说他的那些故事(mythoi)诽谤和丑化了诸神,因而被看作是不真实的。毕竟,周作人怎样才能够将《小河》(写于1919年1月)与他一个月前刚发表的著名的《人的文学》调和起来呢?在《人的文学》中,他把《封神演义》、《绿野仙踪》、《聊斋志异》统统贬斥为“迷信”,说它们宣扬“神仙”“妖怪”。
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欧洲文学发展中,超自然主义让出了长期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回到一两种专为超自然主义保留的体裁里。其中,儿童文学可能是最重要、最无邪的。这一点在西方,从格林兄弟(the Grimm brothers)、汉斯·基里斯督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周作人译作“安得森”)、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直到最近的哈利波特系列的儿童文学传统中,都得到验证。如果我们把《小河》看作是安徒生等人的传统下,针对儿童而写的一个寓言——这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Märchen(童话), 一个德文借词——或者至少是为仍保持着一颗童心的现代成年读者写的,那么,诗中的万物有灵论对那些潜在的理性主义批评家来说,就应该能说得过去些了。的确,周作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让这首诗和他对描写超自然生灵的那些传统小说的指责,得到调和的。

安徒生(1805年—1875年)
在《小河》写作的半年前,即1918年6月,周作人在一篇题为《安得森的十之九》的文章中, 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童话”丹麦语为Eventyr)的中文翻译做了评论。在这篇评论中,周作人认为,把安徒生的童话翻译成文言,是个双重错误,因为这位丹麦人的文学作品具有两个特征: “小儿一样的文章,[…]野蛮一般的思想”,它们与汉语文言所必有和所暗示的东西是背道而驰的。一方面,他的童话的风格,是孩子般的,或者,用与安徒生相识而又常被周作人当作权威来引用的英国文学学者G·戈斯(G. Gosse)的话来说,“它是松弛的、不规则的、直接的儿童语言”。 周作人认为,口语化是安徒生童话的第一特色。另一方面,他的童话所体现出的思維和想象方式,十分接近儿童的思维。而儿童的思维,周作人援引戈斯的话说,类似于野蛮人的思维。
周作人从安特路·阑(Andrew Lang,1844-1912)、哈利孙(Jane Harrison) 等人类学家那里得知,野蛮人的思维,特征常常是相信万物有灵(animism)。 同样的信仰,或者至少,这种万物有灵论的倾向,也见于喜欢幻想和阅读像安徒生等所写的那类故事的孩子身上。在这样的故事中,玩具、家具器物和动物,都有了生命,并且依照社会常规法则行事。显然,周作人所指出的安徒生童话的两个特征,对于《小河》也是适用的:它的风格也是纯口语的、松弛的,几乎就像对小儿说话一样的语言;它具有“野蛮人”的想象,因为它使用了能表情的植物、会说话的动物以及其他被赋予了生命的事物,来演出一个寓言。然而,正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特征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可能并不完全协调。不错,安徒生的童话与周作人这首诗的口语化风格,与新诗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的确是完全符合的,即用白话来反对文言以及旧的诗歌辞藻;但是,作为寓言的标志的万物有灵式的想象却不会,因为这似乎和当时所鼓吹的启蒙原则相悖,就像《西游记》和其他中国旧的志怪小说一样,很可能在煽动迷信。在“五四”作家反对古代迷信的热潮中,——他们其中一些人公开反对所有宗教——, 《小河》中的万物有灵论可能会造成严重问题。它可能会被看作是迷信的、蒙昧的过去的残留物,而且会潜在地危及“五四”运动所拥抱的严格的科学主义信条。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的写作中的这种矛盾,反映了他在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原则和艺术想象力原则之间做出选择时,所经历的挣扎。它还突显出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持论较公允的思想者们,在“五四”时代所面临的理论难题的严重性。

1922年5月23日 摄于北京世界语学会。前排左起:王玄、吴空超、周作人、张禅林、爱罗先珂、鲁迅、Sofoklof、李世璋。后排左起:谢凤举、吕传周、罗东杰、潘明诚、胡企明、陈昆三、陈声树、冯省三
然而,周作人的困窘,很快就得到克服。与其他“五四”作家不同,由于对西方文学以及人类学的最新发展了解较全面,周作人最终能够承认,万物有灵论和其他形式的超自然主义对想象力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为之开脱。在1920年后不久,他便得出结论说,超自然主义出现在文学中,不仅是说得过去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在根本上是人道的。在《人的文学》与《小河》发表差不多三年半之后的1922年4月,周作人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艺上的异物》。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第一次毫不含糊地宣称,科学的原则“不能为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而万物有灵论,尽管对国民文化的发展是有害的,然而用于艺术中还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他还特别为欧洲浪漫主义作品中所运用的超自然主义进行了辩护。这将在下文中作为重点提及。 实际上,他不但对文学中的万物有灵论持宽容态度,而且在同一年,甚至还在一份提倡宗教自由的宣言上签名。 因而,如果《人的文学》代表了周作人对理性原则和艺术想象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的第一个阶段,《文艺上的异物》则体现了它的最终结果。正如《小河》与其他1920年之后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周作人表现出一种对超自然主义越来越兼顾全面的态度,这种态度让《人的文学》中的立场向《文艺上的异物》中的立场的过渡,变得清晰可辨和可理解了。尽管他经过了一些内心的挣扎才得出《文艺上的异物》中的结论,他还是当时唯一有资格得出这一结论的人,因而能在1920年代认可和保卫超自然主义在艺术想象中的作用。从某种角度说,1920年代中期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那些相信科学的力量可以解决人生中所有问题、并因而宣布一切不严格遵守科学原则的观念为不足信的一派人压倒了他们的对手——显示出周作人与“五四”和“五四”后以科学和理性启蒙为中心的关于现代性的权威话语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分歧。 与许多“五四”的同代人和后继者不同,周作人的人性观念和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展望,在1920年前后得到很大拓展,最终超越了那种严格要求“从科学性上说必须是正确的”的诗学准则。其结果,是他拒绝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超自然主义。对他来说,超自然主义,对于作为物种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相应地,它在人的文学中的出现,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实在是有裨益的。
周作人从人类遗传的角度对超自然主义所得出的理解,是他对万物有灵论和文学中其他形式的超自然主义看法的理论基础,而这种理解主要来自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进化人类学(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其实,周作人对人类学的了解也就仅只这些。 进化人类学是在他钻研希腊神话时进入他的视线的。 早在1903年,周作人甫抵东京时,他就对神话,主要是希腊神话及其现代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产生的最初动力,仅仅是出于了解西方文学基础知识的需要。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通过人类学来研究神话——不仅限于希腊神话——的更大价值。 这特别是因为当时在英语世界主宰着希腊神话研究的,是以哈利孙、安特路·阑和詹姆斯·弗雷泽(周译:茀来若)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这些人类学家的著作,将他引向了关于人和文化的更为普遍的问题。在1944年写作的自传性文章《我的杂学》中,周作人透露说,他在人类学中作进一步探索的动机,就是要了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首先要涉及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在思想上,对文化起源问题的好奇,最终将他引向了对“野蛮人”的研究。他指出,野蛮人可以分为三类:古代的野蛮人,小野蛮和文明的野蛮人。 作为一个业余的人类学研究者,也由于中国缺乏可以提供证据资料的海外殖民文化背景,不难理解,周作人对第一类原始人没有机会接触。他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所作的任何工作,都只能限于第二和第三类,即“小野蛮”和“文明的野蛮人”。周作人所说的“文明的野蛮人”,指的是那些仍然表现出某些原始习俗的“文明”人。不难理解,周作人在中国社会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国旧时的志怪小说和故事,根据《人的文学》的说法,正属于这一野蛮人的范畴。而至于“小野蛮”,周作人根据戈斯和其他人的说法,指的是儿童。儿童是野蛮人,因为他们处于个人发展的原始时期,就像原始人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儿童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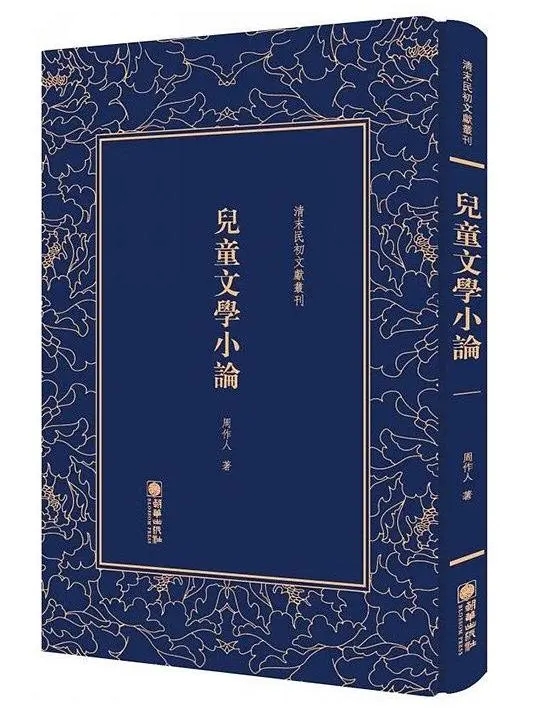
《儿童文学小论》2018年版,本书据一九三二年刊本影印,周作人著
周作人对他所说的“儿童学”——这是个来自德文的新造的词——的兴趣——和他对神话和人类学的兴趣一样由来已久,事实上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兴趣产生于他在东京的时候。作为其儿童发展研究的重要部分,周作人转向了儿歌文学或为儿童而作的文学。他从1912年,即由东京回到故乡绍兴后一年,到1917年定居北京之间这几年的日记,表明他的很多研究都集中在儿童文学上:他到处收集英文和日文的相关作品; 他还在家乡分发搜集儿歌童话的告示; 他撰写并在当地发表了关于童话和儿歌的论文。 其中的四篇,连同后来在北京写的七篇关于同一主题的文章,都收入了1932年出版的文集《儿童文学小论》中。这四篇文章属于他首批严肃的文学论文。还有更多1917年前写作的关于儿童文学或相关主题的文章和翻译,没有被作者收入集中。更为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周作人是将儿童文学作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总构想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来呈献的。然而这一事实几乎被所有的文学史家忽略了。他关于儿童文学的文章《儿童的文学》(1920年10月首次进行演讲,两个月后发表),紧随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构想的三篇著名文章之后:《人的文学》(1918年)、《平民的文学》(1918年12月)、《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这四篇文章一起成为《艺术与生活》(1931)这本文集的前四篇。这本重要的文集所收入的文章,其作者认为表达了他迄于1920年代中期对文学和生活的确定想法。 很明显,论儿童文学的文章,被作者置于和前三篇更著名的文章同等的位置,而人们如果认识不到这第四篇文章的意义,就不可能理解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构想。
从一开始,周作人就把儿童文学,或者说Märchen——他执意使用这个德文词,而不是英语的“fairy tale”或者“wonder tale” ——理解为在根本上是与神话或传说(saga)一样的。 早在1908年,周作人就写过和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以下简称《文章及其使命》)的重要论文。这篇论文和鲁迅在同一年写作、发表在同一份刊物上的《摩罗诗力说》一样,都是用文言写的。 在这篇论文中,周作人引了约翰·哥特弗里特·封·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的观点,即认为文学是民声的表达。根据赫尔德的说法,“民声”(Stimme des Volks或vox populi)在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阶段,或者在其人民文明的原始阶段,表达得最为有力,它被保留在那些含有古代神话和英雄传说的歌诗中。 依照赫尔德的“民声”说,周作人在《文章及其使命》一文中认为,童话同样也是天籁(vox caeli)的表现。 他从赫尔德那里推论出,童话与原始人或古人的歌谣一样,保留着同样的灵的纯洁和同自然的亲近,因为童话与生命的早期阶段相关,正如古代的歌谣是人类历史早期阶段的产物一样。因而,童话和那些古代歌谣一样,同样可以被看作是天籁的载体。

德国浪漫主义代表画作弗里德里希《雾海的漫游者》
后来,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周作人转向了安特路·阑,并转述了他对童话所作的人类学解释,提出童话在根本上与“mythos(神话)”和“saga(传说)”是一样的。周作人在转述时特地使用了西文原文。 周作人将阑的《神话、仪式与宗教》(Myth, Ritual and Religion)奉为圣经。在这本书中,童话被当作神话的一个体裁分支,对它的研究构成了人类学的一部分。 以阑为依据,周作人试图通过展示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童话之间的相似性,来把童话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中那些明显非理性的因素合法化。这种普遍论的观点认为,在那些彼此之间差异巨大的民族和文化中所各自产生的童话里,存在着共同的模式和结构。这种观点为周作人的文学和哲学主张提供了很好的支持,作为基础支撑着并统一了周作人多种多样的观念和思想兴趣。没有这个基础,这些观念和兴趣会显得散漫无章,甚至相互矛盾。因而,周作人对童话及其与人类处境中更广泛的关注之间关系的思考,其背后的推论,就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既然,按照阑和其他进化人类学家的说法,在地理上和文化上相隔遥远的民族的神话和童话,具有一些相似之处,而这些相似之处又意味着人类发展的共同模式,那么,仅因为古代神话和童话中含有超自然因素,就简单地排斥或清除它们,在思想上就是幼稚的;既然儿童时期在很多方面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早期相似,那么,儿童对万物有灵论的故事或童话的需要,就像我们的祖先需要神话一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法的。确实,这些故事对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的健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古代神话和现代童话的模式与结构,正如周作人从阑和其他人类学家那里了解到的那样,并不是某种过去的东西,或者某种仅仅属于原始人的东西;它们渗透在我们各个时代的文明和文学之中。
周作人建立在进化人类学基础上的关于童话的想法,使得他对文学之一般而不仅止是对儿童文学,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把文学看作一种人类活动这样一种文学观所具备的全面性和历史感,使周作人有别于许多持一种狭隘而实用的文艺观的同代人。他对文学更开阔的看法,让他最终超越了他早些时候基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批判。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这种文学观使他甚至接受了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

赫尔德(1744年 – 1803年)
周作人的童话观和超自然观,如上所述,来自像阑这样的人类学家。在接受了阑的进化人类学之后,周作人在讨论儿童文学的时候不再提赫尔德。然而,在西方文学和思想史的广阔背景下,阑的人类学和周作人由之派生出的观念,特别是有关童话的观念,不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孤立的学说。事实上,它可以回溯到赫尔德的时代。人类学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取得的进步,除了欧洲人在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进行殖民的因素外,也是十八世纪晚期以来欧洲的几种文学和思想潮流的结果,这些潮流不仅仅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这种广泛的思想背景,在周作人那些取材于或者传播英国进化人类学思想的文章中,都可以感觉到。在他最重要的文章《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用进化人类学作为论说的根据:“照进化说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发达的历程。” 但是,在这个进化论的外表下,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人类发展观同样可以回溯到欧洲的浪漫主义。 进化论早已被认为是支撑着中国文学和民族现代性话语的主要西方理论之一。与之相比,周作人对儿童文学所做的理论说明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学术上的关注。然而,它们同样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在讨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的同时,有必要介绍一下有关的浪漫主义概念和这些概念的相关历史。
对童年的文学兴趣的浪漫主义根源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在其著名的反击一位理性主义者对诗歌的攻击的时候,曾经说:“野蛮人之于时代就如同儿童之于年龄。” 用“野蛮人”比况儿童,雪莱走在了周作人前面。实际上,以 “小野蛮” 这个词指儿童,周作人是从十九世纪晚期英国文学批评家戈斯(Gosse)那里转借来的,它成为周作人最喜欢用的词。然而,雪莱其实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持这种看法的人。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把人的自然状态同文明状态相对比,才是现代童年崇拜的真正根源, 而德国的大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观,为那种把人类史想象为个体生命历程的观念,提供了基础。 对卢梭和受他影响的欧洲浪漫派来说,文明状态是堕落状态,它偏离了与生俱来的天然的优雅状态,给人类戴上枷锁。弗里德里希·席勒修正了卢梭的观点。他意识到真正的自然状态,很可能远非让人感到愉快和舒服,并认可用理性来取代自然状态的必要性;然而,他还是承认,自然状态是人类想象中最理想的状态。
在《美育书简》的第三封信中,席勒用童年和成年的比喻来分别描述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他的描述揭示了自然状态(人类史上的野蛮状态和个人的童年)何以对文明人具有怀旧的吸引力:

席勒(1759年-1805年5月9日)
因此,人在他的成年,以人为的方式找补回他的童年,在观念中构造了一个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他虽从未经验过,但必然要由人的理性规定来假设出来。在这个理想状态中,它给了自己一个目的,在实际的自然状态中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它还给了自己一个选择,而那时他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于是,他现在仿佛要重新从头开始,出于清醒的洞察和自主的决定,把独立状态交换为契约状态。
对席勒来说,是想象力让理想中的自然状态成为必需的,没有想象力,人就会变成蛮子(Barbar),就像没有理性人会变成野人(Wilder)一样。 在另一篇著名的批评论文《论天真的诗与感伤的诗》中,他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的童年是我们在有教养的人性那里仍能遇到的唯一未被摧残的自然。因此,如果我们身外自然的任何足迹,都把我们引向童年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 道德的和感伤的人,依照卢梭和席勒的说法,是丧失了天恩(natural grace)和天真状态的人。对这种人来说,“儿童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对象,这个对象借一个观念(Idee)的伟大,消灭了任何经验的伟大。”席勒从康德那里借用了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来阐发儿童的神圣:“它在知性判断(die Beurteilung des Verstandes)中不管失去了什么,都在理性判断(die Beurteilung der Vernunft)中丰富地重新赢回了。”
圣婴(the holy child)的意象,当然起源于基督教。但是,浪漫主义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意义。在这个基督意象的背景下,浪漫主义者创造了所谓“浪漫派儿童(Romantic Child)”这一形象。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它贯穿了约从1789年起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它是包括布莱克、华兹华斯、诺瓦利斯等诗人在内的英国和德国主要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中心主题。它还超出了文学之外,塑造了社会上通行的童年的现代形象。
以上是以席勒的美学理论为基础,对浪漫派抬高童年背后的理论的简要阐述。然而,周作人,如前所述,并不是主要通过文学和美学来接近童年这一主题的。正如他在《我的杂学》中所声明的那样,童年这一主题一开始是作为进化人类学的一部分引起他注意的。当他虔诚地阅读安特路·阑的时候,他注意到阑的这样一个观点,即童话是神话的一个分支。这一人类学入手点,规定了他最初对童年的兴趣和构想。翻译成具体的话,这就是说周作人并没有去钻研卢梭、席勒、华兹华斯或者诺瓦利斯。周作人最初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在于那种为童年写作的文学,而不是关于童年的文学。这就难怪他最初写下的和儿童文学有关的作品,更多是学术性的,而不是创作性的。在整个1910年代和20年代初,周作人尽力搜集、翻译和研究各种儿歌、童话,以及其他体裁的儿童文学。值得一提的是,在从事这项工作这一点上,他与格林兄弟,即雅各(1785-1863)和威廉(1786-1859)不无共同之处。格林兄弟收集并在1807年出版了他们经典的儿童和居家童话,他们自己被称为“浪漫主义时代之子”, 尽管他们不算是创作家。
周作人从阑那里获得的人类学研究途径,又进一步为他对美国一些有关早期教育和儿童文学的著作的阅读所增广,比如H·E·斯喀特尔(H.E. Scudder,1838-1902)的著作。与安徒生以及《小说之童年》(The Childhood of Fiction)、《民间故事与原始思维研究》(A Study of Folk Tales and Primitive Thought)(1905)的作者J·A·麦扣洛克(J.A. MacCulloch,1868-1950)有过书信往来。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还有其他几篇在20年代早期写作和发表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中的基本原理,就是从这些文献中得来的。这些西方著作,教给他从事儿童文学的人类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而且,一时间,周作人似乎完全致力于此。他发掘出鲜为人知的中国古代儿歌集,用现代的思想观念加以评论; 他评论新出版的儿歌集,赞扬它们的成就,也指出它们的不足; 他还对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进行评点,比如刘易斯·卡罗尔的《阿里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和安徒生的《童话》, 有时候,他也亲自动手翻译。 通过自己的努力,周作人让学者和大众提高了对儿童的心理、智力和精神健康的必要性的认识。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当时对这一题目有一场踊跃的公共讨论,这些讨论保留在赵景深(1928)编的几部论童话的论文集里。然而,周作人虽然最初是从当代进化人类学、而不是从浪漫派的高祭坛上降落到儿童游戏场的,但这并不应掩盖他的这一事业的浪主义性质,也不应减轻他对浪漫主义遗产的欠债。而且由于他最终并没有成为一名早期教育的活动家或学者,也没有成为一名人类学家,而是做了一个文学批评家、诗人和散文家,因此,对于理解他的文学思想来说,揭示他从人类学家那里和其他地方接受到的浪漫主义遗产就愈发关键了。周作人或许没有像钻研阑那样深入钻研过卢梭和席勒,但是现代人们对神话的兴趣——作为儿童文学的主要体裁的童话,就属于神话中的一种,而且,现代进化人类学也正是从神话研究中诞生的——,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根源。实际上,对席勒所说的“孩子般的民族”的研究, 特别是对其神话的研究,与文学上对童年的兴趣,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旨趣。周作人在不止一处表示,通过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他对这段历史是熟悉的。

维柯(1668年-1744年)
在欧洲,对“孩子般民族”的研究,始于对欧洲各民族童年期的研究。这一研究开始时集中在对他们的神话和传说的研究上。在十八世纪晚期的欧洲,正如对童年的兴趣一样,对作为文学和哲学模式的古代神话的日益浓厚的兴趣,是对英国的牛顿和洛克以及法国的启蒙哲学家们所代表的那种主流理性主义的一个反动。乔姆巴蒂斯塔·维柯和赫尔德这两位公认的现代神话研究的奠基人,都出于,或者部分地出于,纠正启蒙运动的乐观和唯物的理性主义的需要。既然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大部分时期,维柯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对古代神话的重新思考和在促进人们对北欧传奇和神话的文学与思想兴趣的过程中,是赫尔德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赫尔德生活在一个古代神话的谬误和迷信被戳穿了的时代,但是他并不同意那种简单地把神话的使用从现代文学中完全废除的观点,不过他也反对泛滥于现代文学中的把古代神话当点缀或学究式地运用神话的做法。相反,他要求德国文学应该从在古代诗歌中创造和使用了神话的那种诗的精灵中汲取灵感。 在赫尔德看来,古人在神话中保存的对生命力不受阻碍的表达,应该能帮助现代诗人建立一种新神话。只有这种对神话的创造性运用,才能让现代诗人超越对古人的简单模仿。 对神话加以创造性运用的思想,促使赫尔德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神话这种通常的资源之外,又在北欧神话中去寻找别样的资源。实际上,连同卢梭在欧洲思想界引发的对原始状态的热情,他在希腊罗马之外寻找神话和他的大历史观,导致了思想界生成一种氛围,而这种氛围最终引向了现代人类学的诞生。 从阑那里,也从其他地方,周作人了解到现代进化人类学对包括浪漫派先驱赫尔德在内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遗产的债。
作为他对神话研究的贡献的一部分,赫尔德还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原始主义在文学中的兴起,而正如上面我们对席勒美学思想的阐述所示,这种原始主义与童年崇拜有直接关系。作为原始主义者,对于影响并先期了席勒的赫尔德来说,在本质上,野蛮人的心灵比文明人的更有诗性。“一个民族越有野性,也就是说,越生机勃勃,越有自发性,”赫尔德在著名的《关于莪相和先民歌谣的通信节选》中恣洋挥洒地写道:
他们的歌——如果他们有歌的话——也一定就越有野性、越生动、越自由、越感性、越抒情!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和教育越是远离人为的、科学的方式,它的歌就越不是为了纸笔而作,他们的诗就越不是死文字:在它的歌的抒情的、生动的、舞蹈般的节奏里,在其图画的栩栩如生里,在其内容、情感的一贯性和急迫性里,在词语、音节甚至在很多人那里包括字母的对称性里,在旋律的运动里,在属于活生生的世界、属于教诲与民族歌曲、并与之一同消失的千千万万其他东西里,——在这一切里面,而且只在它们里面,存有其本质、目的以及创造神奇的全部力量,它们为这些歌所拥有,为了成为民族的极乐、驱动力和永远的世代相传与欢乐的歌!
周作人充分认识到这段话的重要性,并在他的《欧洲文学史》(原本是1917年在北大的讲义,次年出版)中引用了它。 赫尔德赞扬原始人更具诗意,距离席勒赞扬童年是文明人一生中最理想的阶段,只有一步之遥。依据他们共同的对文明的不信任,尚未开化的,即儿童和古代民族中才有的自然状态,被认为最适于神话创作(mythopoesis)和想象。因而,就算周作人对席勒的美学思想没有详细的了解,他在神话、野蛮人的思维及其与诗歌的密切关系等方面对赫尔德的了解,足以令他成为浪漫主义事业的一个有意识的继承者。

德国哈瑙市的格林兄弟雕像(1896)
应该强调的是,对赫尔德来说,创造性地运用古代神话的紧迫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德国的“落后”,因而它急于创造出一种能与英国文学媲美、能和法国文学对抗的民族文学。 从一开始,赫尔德对在德意志文学中使用希腊罗马神话的指示和他对北欧神话的热情,就是一个更大的民族事业的一部分。对他来说,与发源于地中海地区的古典神话不同,北欧的神话和传奇是“民族的”。以北欧传统为基础创造一种新神话,将是对地中海古典传统霸权的一种反动。因为这个和其他的原因,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广北欧文学。他对北欧传奇、民歌和其他形式的诗体民间传说怀有极大热情,他还以自己的声名赌所谓莪相(Ossian)诗歌的真实,后来才揭穿所谓莪相诗歌其实是苏格兰人麦克弗生(Macpherson)伪造的。 赫尔德的喜好对文学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先不论别人,歌德曾回应了他的号召,他的号召促成了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这是德国文学史中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这段历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自然不会略过。 格林兄弟搜集德国童话的工作,也应放到这一背景下来考察。在整个欧洲文学史中,对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神话的狂热兴趣,和要制造“北方太阳”的热忱, 连同浪漫主义的童年形象,共同促进了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作为反启蒙主义的最高运动的诞生。
就热衷于神话、民谣、民间诗歌、儿歌和旧中国的野蛮习俗而言,周作人几乎成了赫尔德的化身。 凡是德国和其他欧洲浪漫派作家涉猎过的主题,几乎没有不引起周作人注意的:他对儿歌和民间传说的热忱、他对原始主义的兴趣、他对性解放的提倡、他对文明的不信任、他为了反对垂死的道德主义和文明而对在儿童和原始人身上表现最为明显的生命力的肯定、他的寓言创作, 乃至他的爱希腊(philhellenism,不管有多么不正统、在深度、得力的教授和学识方面有多么不足)。 实际上,他和赫尔德之间的相似,超出了他们各自兴趣之间的共同点。因为他们各自的思想兴趣和他们所面临的历史处境背后的动机,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方面,在赫尔德那里,古典神话和它在理性时代的尴尬处境,促使他在自己的北欧传统中去寻找他类的替代品;另一方面,英国对民间传说的研究以及吸收了民间传说的英国文学——包括伪造的莪相——对赫尔德来说,都是德意志文学要效仿的榜样。(事实上,那时的大不列颠,在德国人的想象中,几乎每一方面都是先进的。)在周作人那里,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正统的破产,以及更先进更适合现代的欧洲文学和文化的涌入,促使他在先前被压制的文化中去寻找一种中国正统文化的他类替代品。在这种探索中,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和德国的——文学史,为周作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榜样。因而,和赫尔德一样,在周作人的思想追求背后,有一个关乎民族的主张打算,即克服中国的落后,创造一种有价值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关乎民族的打算给他所从事的工作注入了紧迫感。因而,几乎在每一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在童年崇拜方面,不管他自己对此有多少自觉,周作人都是在忠实地追随着一位德意志的(还有英国的,尤其是在考虑到雪莱的时候)浪漫派先驱的足迹,在1920年前后的批评文章中,周作人显示出明白无误的浪漫主义向和冲动。
儿童的声音:威廉·布莱克
如上所述,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大约开始于1905年左右在东京的时候。但这一兴趣,直到“五四”运动前不久,一直未能引他欣赏欧洲经典的关于童年的文学。要考察他是怎样发现欧洲文学中那些经典的关于童年的文学,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他和白话诗的关系上来。
周作人被认为有“建立[中国现代]诗坛”的功劳。然而,他却屡屡拒绝接受“诗人”这一头衔。 从他一生的工作来看,我们也会同意,他主要不是个诗人。与他的散文相比,他的诗歌作品为数不丰。他主要是个散文家,而且在这方面罕有能与之媲美者。他声明不是诗人,也可以从他阅读浏览的书目中得到支持。在他的日记、讲稿和散文中所载或所反映的书目中,诗歌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他早期的白话诗实验,他的名字将永远和中国现代诗歌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一辈子都在写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声誉和资格,却主要是建立在1920年前后写作的有限几首白话诗的基础上的。 他在1931年后写的那些打油诗,尽管在数量上大大超出了他的白话诗,在文学和历史重要性上,都不能与他的白话诗相提并论。基于这一事实,他在诗歌领域里短暂却严肃的早期探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这种探险主要是受一位英国浪漫派诗人激发的,并且这一影响史又与童年和其他浪漫主义主题有着内在的联系,就使得他的白话诗作品特别值得考察。
我们已经证明,《小河》与周作人在安徒生《童话》里所看到的特征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但是,除了周作人总结出的安徒生童话的一般特征,比如万物有灵论、松弛直白的语言等等这些多数童话都有的,而不仅仅是安徒生童话独有的特征,还没有文本上的证据能够证明,周作人的诗歌直接受到了那位丹麦人的影响。作为一首诗体作品,《小河》另有灵感来源。
如上所述,在19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周作人一直专注于研究和搜集儿歌。但是,在这个十年的末期和1920年代初期,可能是为了配合当时方兴未艾的白话诗运动,要为它注入活力,周作人发表了几篇论诗的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几位欧洲诗人。这些诗人包括萨福、谛阿克列多思、雪莱和波德莱尔。 尽管他很喜欢希腊的东西,但是,萨福和谛阿克列多思与他自己的创作并没有明显的关系。雪莱和波德莱尔对他的文学观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但他自己的气质与这两位性格独特的诗人差别很大,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与他们的诗歌世界相去甚远,使他不能直接从他们的诗歌中获取灵感。尽管周作人在《小河》首次发表在《新青年》时的说明中承认,他的这首诗在缺乏格律方面同波德莱尔那些散文诗——他翻译了其中一些 ——好有一比,但写乡下的《小河》与波德莱尔写都市的《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在他的诗歌写作中,除了避开雪莱和波德莱尔以外,周作人作为读者和批评家,也具备足够的鉴别力,使得他不大看重安特路·阑和哈夫洛克·蔼里斯(Havelock Ellis)的诗作,尽管他很欣赏他们的散文作品。
然而,周作人的白话诗确实仿效了某位欧洲诗人。文本证据和传记研究表明,当时其天才刚开始得到西方批评家深入理解的神秘诗人威廉·布莱克, 在1920年前后比任何别人都更是其诗歌灵感的主要来源。
现有的传记证据表明,周作人在1917年,大概第一次,得到了一本布莱克作品集。 在日本时,他极有可能已对这位英国诗人有所了解,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并没有留给我们足够的线索。 在1917年左右,他至少得到了两种版本的布莱克诗集,这一点很可能表示他当时兴趣的强烈程度。 然而,现在还不清楚他阅读了这两本诗集中多少首长诗,因为没有好的注释,这些诗是非常深奥晦涩的。但是我们知道,他确实阅读了布莱克最流行也最容易阅读的诗作,即《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和《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这两篇作品在主题上对于童年的关注,可能是最能引起周作人注意的东西,也可以解释他兴趣的陡增。在《欧洲文学史》中关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那一章里,周作人用了整整一节来介绍布莱克。 其中《经验之歌》被描述成“以真纯之诗,抒写童心”。 除了作品原本外,周作人还罗致了一些对布莱克的批评著作。1918年2月,他弄到卡罗琳·F·E·斯珀津(Caroline F.E. Spurgeon)的《英国文学中的神秘主义》(Mysticism in English Literature)(1913)一书。 他在自己关于布莱克的文章中引用了这本书。 从这本小书里,周作人对这位神秘诗人的神话系统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开始意识到,布莱克不仅仅是一个专写儿童诗歌的诗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写了一篇关于布莱克的诗歌与思想的文章,并用不同的标题发表了两次。 此前,周作人从未在任何一个现代欧洲诗人那里这样下工夫,而且是在这样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

威廉·布莱克(1757年-1827年)
关于布莱克的影响,比间接证据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存在于周作人1920年前后写作和发表的白话诗里。实际上,在《小河》中,在诗歌构思和意象方面来自布莱克的影响,就已经可感了。下面这首诗是布莱克的《经验之歌》中的第二首,它极有可能为《小河》的写作提供了灵感。
“Earth’s Answer”
Earth rais’d up her head,
From the darkness dread & drear.
Her flight fled:
Stony dread!
And her locks cover’d with grey despair.
Prison’d on watry shore
Starry Jealousy does keep my den
Cold and hoar
Weeping o’er
I hear the Father of the ancient men
Selfish father of men
Cruel jealous selfish fear
Can delight
Chain’d in night
The virgin of youth and morning bear.
Does spring hide its joy
When buds and blossoms grow?
Does the sower
Sow by night?
Or the plowman in darkness plow?
Break this heavy chain,
That does freeze my bones around
Selfish! vain!
Eternal bane!
That free Love with bondage bound.
土地的回答
土地抬头,
从可怕又可厌的黑暗。
她的光逃掉:
石样的恐惧!
她卷发罩着灰色的绝望。
囚在水边
星的嫉妒令我穴窟
冰冷苍白
哭着
我听见古人的父
自私的人父
残忍嫉妒自私恐惧
难道快活
锁在夜里
青春的处子和黎明能忍受。
春天岂会藏其喜乐
在幼芽和百花生长时?
播种人岂
在黑夜里播种?
或是耕夫在暗中耕地?
砸碎这沉重的锁链,
它冻僵我全身筋骨
自私!徒劳!
永远的毒害!
把自由的爱用绳索束缚。
在构思、修辞和意象方面,这首诗和《小河》都有相似之处。两首诗的主题都是受阻的生命力渴望被释放。而且,两首诗都使用了土地和水的意象。在布莱克的诗中,土地被“囚在水边”,而在《小河》中,中心构思是被堤堰阻遏的水流。周作人后来声称,《小河》表达的是一种儒家式的对天下的忧惧。 然而,在诗文中,没有什么能把对这首诗的解释局限在儒家的框架里。布莱克的“把自由的爱用绳索束缚”,就像同样受困于嫉妒的锁链的兽人(Orc)一样, 可以指想象力和性自由。同样,如果把《小河》放在作者整体的思想兴趣中来考察,“把自由的爱用绳索束缚”也可以,或者说比儒家式的忧惧更可能,是这首诗的主题。毕竟,周作人当时正大力倡导哈夫洛克·蔼里斯的高度自由化的性伦理。在《小河》中,“水要保住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暗示,在诗中被截流的水,的确应该被理解为被遏制的生命力的譬喻。这样的解读,与周作人反对以伦理、迷信和伪善的名义对生命力进行任何压制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在他所有的白话诗中,包含着一个完整寓言的《小河》,与布莱克诗歌中的神话创造方面,可能是最接近的,尽管它那松弛的风格与布莱克的《土地的回答》的紧张节奏并无共同之处,而且它所讲述的寓言,就复杂性而言,无法与《土地的回答》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那个宏大的神话系统相比。但作为一种创造神话的尝试,《小河》仍然可以看作是以创造神话的布莱克为榜样的。
然而,《小河》并不是唯一一首受布莱克灵感激发的诗。事实上,它也不是周作人最典型的模仿或者效法《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的诗,因为它的主题同儿童或者童年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的白话诗中有相当一部分,就童年的主题乃至就构思、意象甚至语言而言,都显示着受《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影响的不容置辩的痕迹。 下面这首写于1921年4月20日的诗,就是一个例子:
小孩
一个小孩在我的窗外面跑过
我也望不见他的头顶
他的脚步声虽然响
但于我还很寂静
东边一株大树上
住着学多乌鸦,又有许多看不见的麻雀
他们每天成群的叫
仿佛是朝阳中的一部音乐
我在这些时候
心里便安静了
反觉得以前的憎恶
都是我的罪过了
与这首诗相对应的,是分别收在《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中的两首《乳母之歌》。在周作人的《小孩》中,小孩子的吵闹声,反悖式地让诗人获得内心的安静。这样获得的安静,又让诗人意识到先前对安静的丧失,并由此清除了他精神上的不安静的根源。《天真之歌》里收的第一首《乳母之歌》中,特别是其第一节,儿童的叫喊声能造成同样的效果:
When the voices of children are heard on the green
And laughing is heard on the hill,
My heart is at rest within my breast
And every thing else is still
Then come home my children, the sun is gone down
And the dews of night arise
Come come leave off play, and let us away
Till the morning appears in the skies
No no let us play, for it is yet day
And we cannot go to sleep
Besides inthe sky, the little birds fly
And the hills are all covered with sheep
Well well go & play till the light fades away
And then go home to bed
The little ones leaped & shouted & laugh’d
And all the hills ecchoed
当孩子的声音回荡在草坪
笑声响在山冈,
我心安于胸中
别的也全都寂静
回家吧,孩子们,日已平西
夜露升起
来,来,别再游戏,我们走
等黎明重现天际
不不让我们游戏,因为还是白日
我们不能入睡
更何况天上有鸟飞
山坡为羊儿遮蔽
好好去游戏直到天光曛微
再回家入睡
小儿们又跳,又叫,又笑
山丘全都回应
《经验之歌》中的《乳母之歌》属于经验世界,在语气上是讽刺的。但在儿童的声音招致乳母的反思这一点上,周作人的《小孩》仍然遵循了其范本。布莱克的第二首《乳母之歌》是这样的:
When the voices of children are heard on the green
And whisperings are in the dale:
The days of my youth rise fresh in my mind,
My face turns green and pale.
Then come home my children, the sun is gone down
And the dews of night arise
Your spring & your day, are wasted in play
And your winter and night in disguise.
当孩子的声音回荡在草坪
呢喃响在谿谷:
我青春的日子在心中鲜活升起,
我脸转青转灰。
回家吧,孩子们,
日已平西
夜露升起
你们的春你们的天,浪费在游戏里
你们的冬和夜穿上伪装。
这两首《乳母之歌》,比《土地的回答》更能代表《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 这是因为虽然童年在《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中是中心主题,《土地的回答》却与童年主题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两首《乳母之歌》与周作人自己的创作计划关系更密切。
周作人在布莱克那里,发现了对他所钟爱的“小野蛮”这一主题的诗的表现,并且被布莱克的《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的诗歌魅力所俘获,这也许不无偶然。但是,布莱克把童年作为他的《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的主题,则绝非偶然。生活在人的内在和外在的天性开始削弱洛克和牛顿所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时代里,正如彼得·柯文尼(Peter Coveney)正确指出的那样,布莱克“是我们的现代感受力的第一个受害者”。对布莱克来说,童年等于想象力,而儿童,或者任何有想象力的人,都与培根、牛顿和洛克这样的“白痴的推理者(Idiot Reasoners)”相对立。在1799年8月23日致特鲁斯勒(Dr. Trusler)的著名信中,布莱克清楚地说明,他推举儿童,乃是因了他们的想象官能:
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可能会幸福。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想象和异像(vision)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所画的我都能看见,但每人见到的都不一样[……]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延续的幻想和想象所成的异象,有人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备受鼓舞[……]
但是我很高兴发现我同类中大多数都能够明了我的异像,尤其是儿童,他们在观看我的画时所感到的快乐过我所望。无论青年和童年皆非愚蠢或无能有些儿童是愚人,正如有些老人也是那样。但是,绝大多数是在想象力和灵的感受一边的。
灵的感受首先存在于异像的官能里。说绝大多数儿童是“在想象力和灵的感受一边的”,实质上等于说,“野蛮人的心灵内在地比开化了的人的心灵更有诗意。”显然,布莱克基于儿童内在的更强的想象力官能而给予儿童重要的地位,在本质上与浪漫主义关于童年状态更接近自然、更能创造神话的形象是一致的。尽管对布莱克而言,儿童的天真是一种未经组织的天真,他称之为“Beulah(安乐地)”,而且它仅预示了、但本身并不是那种组织起来的天真或者伊甸园(Eden),然而“无论青年和童年皆非愚蠢或无能”,不应被看不起、受斥责或受教训。

威廉·布莱克为弥尔顿《基督降生的早晨》所作的插图
在《小孩》中,同样,周作人让小孩成为带来平静的信使和激发反思的人。孩子不是像周作人以早期教育为主题的那些讲稿和散文中所出现的那个样子,是教育的对象和成年人监管的对象。相反,在这里,儿童无意中成了成年人的老师和监管人。从受监管到成为成年人灵的监管人,周作人事实上透露出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转变。这一转变不但突出了他提倡儿童文学时总能显示的人文主义动机,而且带有一种在他的批评文章中不那么明显的灵的或者说精神的维度。它给了对童年的表现一个意识内的(immanent)维度。实际上,这个维度几乎接近宗教。
入神(enthousiasmos)与忘我(ekstasis),或者神人合一(hen kai pan)
布莱克的第一首《乳母之歌》和其他许多诗中,特别是《天真之歌》里的诗中,有着明显的基督形象因素。人们想不到这些因素会出现在公开宣布不信教的周作人身上。 但是,像《小孩》中“反觉得以前的憎恶/都是我的罪过了”这样的诗句,离宗教情绪已很近了。然而,《小孩》在他所有的白话诗中并不是最有宗教性的。在写作《小孩》四个月后写出的《对于小孩的祈祷》,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在语气上更具有宗教性:
对于小孩的祈祷
小孩呵,小孩呵
我对你们祈祷了
你们是我的赎罪者
请赎我的罪罢
还有我未能赎的先人的罪
用了你们的笑
你们的喜悦与幸福
用了得能成为真正的人的矜夸
在你们的前面,有一个美丽的花园
从我的头上逃过了
平安的那边去罢
而且请赎我的罪罢
我不能够到那边去了
并且连那微茫的影子也容易望不见了的罪
在《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中,没有具体哪一首诗能被指作本诗的原型。然而,《天真之歌》常常暗示,儿童离神更近。《小黑孩》、《扫烟囱的孩子》和《捡到的男孩》都暗示这些孩子会升天堂。《乳母之歌》和其他的诗都公然把婴儿和圣婴联系在一起。周作人《对于小孩的祈祷》中的小孩,扮起来自《天真之歌》中的基督形象,因而成了诗人的“救赎者”。
考虑到周作人并不掩饰自己不相信传统的超验主义,包括基督教,他白话诗中的基督形象因素确实就非常显眼了。这些因素不是无谓的,就像他之后有些年轻诗人那样。这些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中嵌入一些庸俗廉价的基督教意象,仅仅是为了制造异域情调和出于审美上的势利。 这些因素反映出,周作人对宗教以及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看法,有了微妙的变化。在《对于小孩的祈祷》写成和发表的同时,周作人,尽管并未皈依,在一封公开信中,却对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作用,作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评价。 在1921年9月3日的这封信中,他指出,“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这首暗含基督教调子的诗,显示出他对基督教态度的这种转变,事实上超越了信中所表达的社会的与民族国家的考虑。实际上,这首诗指向了他的文学观中一个很重要的、却从来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方面。 周作人不仅仅从布莱克那里借用了童年的母题,他还接受了一种超验的维度,并把它带入了中国当时的文学和文学话语中。
周作人曾在介绍布莱克的文章中引用过斯珀津的《英国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一书。在这本书中,斯珀津将布莱克最著名的诗歌中那种儿歌风格与他的神秘异象和超验的感受联系在一起:
布莱克在使用神秘的方法,在那些表面上很微小的事物中结晶出一个伟大的真理方面,是特别大胆和有创意的。其中一些,我们在《箴言篇》(Proverbs)中已经看到了,而《无知的占卜》(the Auguries of Innocence)无非是一系列这样的事实,是最深的智慧的仓库。其中一些具有儿歌般的朴实,它们把儿童语言的清新直白,同受灵感激发的预言家的深奥的真理结合起来。
这里提到的《无知的占卜》,也是周作人最喜爱的一首诗。在前面提到的介绍布莱克的文章中, 他翻译了这首诗开篇著名的四行格和随后两个偶行。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 Robin Red breast in a Cage
Puts all Heaven in a Rage
A Dove house filld with Doves & Pigeons
Shudders Hell thro all its regions.
一粒沙里看出世界,
一朵野花里见天国,
在你掌里盛住无限,
一时间里便是永远。
一只笼里的红襟雀,
使得天国全发怒。
满关鸠鸽的栅栏。
使得地狱全震动。
不仅如此,周作人并不满足于引用和翻译这首格言诗;他还试图以诗体来模仿布莱克这首诗的情感与创意。1921年夏,周作人在北京西北郊养病。在这个疗养地,他写了一组诗,其中第五首最有布莱克风味:
山居杂诗,五
一片槐树碧绿的叶
现出一切的世界的神秘
空中飞过的一个白翅膀的白蛉子
又牵动了我的惊异
我仿佛会悟了这神秘的奥义
却又实在未曾了知
但我已经很是满足
因为我得见了这个神秘了
这首诗亦步亦趋地模仿了布莱克的《无知的占卜》开篇的四行格的模式,这一点应该是昭然若揭的。 比他模仿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写成的那些儿童诗更引人注目的是,这首诗中对超验世界的更明白的暗示。他描绘了一个自然的世界,而这个自然的世界同时又是它之外它之上的超自然世界的显现。考虑到这一点,“神秘”这个词,就特别关键了。它两次出现在这首短诗中,在周作人的诗歌词汇中非常不同寻常。跟随布莱克,周作人在他的小诗中公开承认,存在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神秘。与《小河》中对万物有灵论的采用相比,这一承认标志着向超自然主义迈进了一大步。 比起儿童诗里对基督形象的暗示,这是关于作者宗教情绪的更有力的证据。在他的其他儿童诗中所潜藏着的东西,在这里被明确表达出来了:《山居杂诗》的第五首表明,效法《无知的占卜》,周作人也相信无知(天真)的力量可以——借用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的话来说——“从自然之花中吮啜神性(suck Divinity from the flowers of nature)”; 这意味着尽管他不能够让自己皈依基督教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有神话系统的宗教,而且尽管他尽可以像华兹华斯那样宣称:
所有的神力——所有的恐怖,单个儿的还是成伙的,
所有曾被赋予人形的——
耶和华——同他的雷霆,以及天使们
歌呼的合唱,天庭的御座——
我经过它们一无儆惧。
他仍然能够接纳一种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而这种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是可以被纯洁的心灵——原有的和重获的天真——感知到的。这种神秘的存在在他对文学的看法上就意味着,对他来说,文学在其最高状态里,是为神所激发的,而且,由此可以推断,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神性来说,它是其应有的载体。尽管这可能显得与他那种通常被概括为世俗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观相矛盾,然而,这和他以进化人类学为基础的关于人的一般看法,有着相同的思想来源。无论如何,这首诗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无谓的例子,而我们也不能够把它看成是纯粹的诗歌辞藻,没有真正的思考和感受充实它。
然而,乍看上去,如果把《山居杂诗·五》和周作人最著名的一些论文学的言论放在一起读,这首诗中的超验倾向会显得很有问题。在这里和其他一些诗中存在的超自然主义的暗示与在他一些最著名的批评文章中对这些思想的否定之间,似乎存在明显的矛盾。在写这首诗的一年半之前(1920年1月)写成的著名的《新文学的要求》中,周作人将“神性”和“兽性”排斥在他所构想的中国新文学应有的内容以外。他宣称,中国新文学所需要的,是与为艺术而艺术或者唯美的文学相对立的“人生的文学”。“人生的文学”,他称,“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 这一思想背后的根由,根据周作人的说法,就是“凡是人情以外人力以上的,神的属性,不是我们的要求”。
尽管在早期的批评文章中对超自然主义进行了这样的否定,周作人并没有坚定地反对一切超验主义。在那一年的后期,他对那种代表了“人情以外人力以上的”文学,似乎变得更宽容了。先是在10月26日,在前面提到的《儿童的文学》演讲中,他为那种“保存着原始的野蛮的思想制度”的文学进行了辩护。一个多月之后,在11月30日,他在燕京大学做了《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圣书与中国文学》是理解周作人关于宗教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超验主义与文学的关系的观点最重要的文献。在关键地方,它修正了作为《艺术与生活》一书中前三篇文学论文的基础的那种纯世俗主义,在文学中赋予了超验更大的作用。同样还是借助于进化人类学对诗歌起源的解释,在这篇演讲中,周作人描述了在原始社会中宗教仪式是如何进化成艺术的。按照他的说法,起初,唱歌、跳舞、雕刻绘画,仅仅是一种自发的感情的表达,并不在乎在观众面前表演。当这些活动的仪式和法事方面的功能衰减之后,它们就带有艺术性了。“从表面上看来变成艺术之后便与仪式完全不同,但是根本上有一个共通点,永久没有改变的,这是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原始仪式里的入神(Enthousiasmos)忘我(Ekstasis),就是这个境地。” 周作人试图用具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浪漫派作家所钟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段落,来定义这种境地。在这个段落中,耶稣替他的门徒们祈祷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hina pantes hen ōsin);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入神与忘我,就是雪莱所说的“走出我们自己的本性”。 这就是说走出我们自己的本性,和神或者无限合而为一,或者用雪莱自己的话说就是:“诗人参与了永恒、无限,和太一”。 这种神人合一的思想,是浪漫派一个最根本的思想。雪莱的《诗辩》和他整个的诗歌观就都是坚实地建立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的。雪莱之外,德国浪漫派典范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也将这一思想当作他诗学的最基本信条之一。在他的书信体小说《旭裴里昂,或希腊隐士》(Hyperion or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中,他让主人公旭裴里昂反复吟诵这样的句子:“神人合一,这是神的生活,这是人的天堂。”就好像是在唱诗念经一样。

荷尔德林(1770年—1843年)
周作人嗅到了“神人合一”这一浪漫派观念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气味,认出了其《启示录》式的末世拯救的维度。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周作人指出,通过入神和忘我而实现的神人合一,就是新柏拉图主义所提倡的接近神的方法。这样明确提出新柏拉图主义,说明周作人对他所传布的艺术起源观中的新柏拉图主义内涵,是有充分意识的。 在《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后不久,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一次关于宗教的演讲中(1921年3月),周作人告诉听众,宗教朝向未来的趋向,也是文学所具有的。 把艺术创作看作入神与忘我,这一看法所具有的《启示录》式的末世与超验含义,动摇了人们对他的美学所做的一般性概括——即世俗的人道主义——的根基。如果人们只考察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中前三篇著名的文学论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而忽视其他文章的话,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样的概括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倘若我们注意不到1920年周作人文学观念的变化,我们就会忽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也会忽略一种其后续发展的重要来源。作为周作人沿人道主义路线展望未来中国文学的一个最晚的发展阶段,《圣书与中国文学》清楚地表明了周作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终设想:它应该有一个超验的维度。尽管他自己的诗歌作品从未超出含蓄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例如《山居杂诗》第五首,然而,通过引用“入神”和“忘我“这两个词,他在理论上对文学中的宗教和超验经验更开放了,实际上,他为其他作家沿这一方向的未来发展,发了权威许可证。比如,在他文学思想发展中这个公开的超验阶段过去后很久,他仍因废名的小说《桥》中的人物“有点神光”而加以褒奖。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在1920年超越了世俗人道主义而达到那样的高度,绝非偶然。这反映了他当时整个的思想、心理和精神状况。我们必须记住,同样是在1920年,他对一个乌托邦的合作社计划的推动最积极,这个计划就是新村运动。后来他把三篇写于1919年和1920年的关于新村运动的文章,连同五篇前面提到过的文学论文,收入到同一本文集中,即《艺术与生活》。正如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的自序中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两组文章分别表明了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看法,而他的那些文学宣言和对新村运动的提倡是“相当的”。因而,周作人将自己关于美学的文章和关于社会乌托邦的文章一起编入《艺术与生活》中,就是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了,这意味着在超验美学和社会理想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与文学中的超验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还可以在另一篇重要文章中看到。1922年,为了纪念雪莱逝世百周年,周作人撰文赞扬了雪莱对一个能够与想象力相符的理性社会的热情,并把他同拜伦诗中个体的那种恶魔式的破坏做了对比。 通过引用雪莱为《解放的普洛美透思》(Prometheus Unbound)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他解释了雪莱以威廉·戈德文(William Goldwin)的社会理论为基础的社会理想主义与他的浪漫主义诗歌之间那种精微而至关重要的统一性:
我的目的只在使[……]读者的精练的想象略与有道德价值的美的理想相接;知道非等到人心能够爱,能够感服,信托,希望以及忍耐,道德行为的理论只是撒在人生大路上的种子,无知觉的行人将把他们踏成尘土,虽然他们会结他的幸福的果实。
在自序中,雪莱明确指出,这首诗,虽不是说教诗,却与理想社会的异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他对雪莱的讨论中,周作人如实地阐明了雪莱对理想社会的异象展望和诗歌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看法。考虑到他投身新村运动与发表这篇关于雪莱的文章在时间上很接近,那么,他对雪莱的社会理想与诗歌作品之间关系的格外重视,就不能被看成仅仅是对一段熟悉的文学史的简单回顾或者对一位英国诗人例行公事的纪念了。事实上,在利用引文或关于他人的评论来传达或注解自己的观点方面,周作人是个高手。通过介绍雪莱,周作人微妙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理想主义和诗歌之间的相互交织的关系的看法,而周作人在那篇百年忌的文章中所阐述的雪莱的社会理想和诗歌之间的密切联系,映照出周作人当时在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之间的统一性。由此,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中将自己的文学论文和关于社会乌托邦的论文并置的编辑策略,和他论雪莱的文章,都毫无疑议地告诉我们,对周作人来说,乌托邦的异象和《启示录》式的末世异象是相辅相成的。
新村运动,对周作人来说,就像是雪莱眼中的戈德文那种正义社会。它是受基地设在日本的新村运动激发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武者小路实笃在日向建立起第一个新村的时候,周作人深为它的理想所吸引,以至两次到日本考察了新村原址。在根本上,周作人对新村运动的热情来自于它的人道主义。 这种人道主义与周作人的文学论文中表现出的那种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周作人拥抱这一乌托邦运动,是因为他相信在它的理想状态中,新村运动的合作社会在满足大众福利最基本要求的同时,能够保证个人主义。在一篇收入文集的文章《新村的精神》中,周作人宣称“新村的精神,首先在承认人类是个总体,个人是这个总体的单位”。 这让我们想到周作人认为对于他所翻译和编入《点滴》中的那些外国小说来说最为根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写于1920年的《点滴》序言中,周作人认为集中所有短篇小说都有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
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因为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
毫不奇怪,在这里,周作人提出对个体中的普遍人性的展示应是中国现代文学唯一正当的主题。 这种人道主义一方面将周作人引向社会乌托邦的异象,另一方面让他拥抱超验感受的文学表现,这两个思想动态都缘于他对人的内在的善的人道主义信仰。作为一种信仰,相信人内在的善,与斯珀津所说的布莱克对“人内在的神性” 的信仰非常相近。事实上,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确引用了布莱克来为人性是灵与肉的统一体这一观点辩护。但是在1920年前后,周作人在这种肉体与灵魂的平衡的观点上,比他文学生涯中的其他任何时期都更明显地倾向于唯灵思想和观念论。 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他反复使用“理想的”这个词——理想的文学、 理想的写实主义、 理想的人的生活, 而他将人道主义文学等同于理想的文学,表明了这种超验的倾向。 他称欧洲经典作品——他认为它们是中国将来文学的模范——为理想的文学,因为它们包含着他所阐述的那种人道主义,就像他称乌托邦的新村运动的人道主义原则为“理想的”一样。理想的文学和理想的社会都将体现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作为物种和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 他关于人的思想,是这种人道主义的中心。这种思想最终既是理想的又是目的论的,因为它超越了所有经验现实,其用处在于作为一个目标。这种关于人的理想观念,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现实环境的抽象,把任何有关文化、国别、种族等偶然特征或者其他经验环境抽去。 它是人注定要成为且有能力成为的一个目的论的楷模。文学,作为对人的理想化的异象的展现,因此也是理想的。作为入神与忘我的艺术和文学,意味着艺术家有如神附身一样必须为这样的人的理想所激发,超越他那个经验的、世俗的自我。周作人援引托尔斯泰说,最高的艺术必须同时是宗教的,对于艺术作品来说,要成为宗教的,就是要表达神人合一。
结语
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作为欧洲文学史上一个历史阶段的浪漫主义的定义上,批评界已达成共识,这个共识被艾布拉姆斯的名作《自然的超自然主义》的标题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正如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和德国文学中所体现的那样,是以在自然环境中获得的《启示录》那样的经验为中心的。《启示录》那样的经验,在艾布拉姆斯遵循《圣经》批评中通常的解释所使用的意义上,“意味着一个异象,在其中,旧世界被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取代了”。 同对这种经验的传统描述不同,浪漫主义在重启超验传统时,一般都限制在自然世界中,并不进入旧的神话系统。作为一场广泛的文学和思想运动,欧洲的浪漫主义包含了很多不同方面,其中,童年崇拜、文学和哲学中对野蛮人的兴趣、各种形式的自然主义、社会政治的激进主义等最为突出。周作人在寻求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未来社会的过程中,尽管从多种不太系统的资源中接受影响,却表露出了所有这些浪漫主义方面。从推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到倡导乌托邦社会,周作人具备所有浪漫派的资历。实际上,他曾经呼吁当时的新诗运动要吸收浪漫主义的诗学,而不是他所谓的古典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短暂时期,周作人为他自己也承认是理想主义的那种关于未来中国和中国文学的异象所鼓舞。和欧洲那些逆启蒙运动而动的浪漫派一样,周作人在与“五四”时期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础的启蒙主张相配合的同时,也用他自己的浪漫派的种种追求补充和修正它。如果理性、世俗和科学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主流话语模式,周作人的浪漫主义追求,甚至在他后来转向培养趣味推崇闲散雅致之前,已经提出了对文学和民族现代性的“另类”(alternative)设想。 但是,这种“另类”设想很难说是“中国的”。与他后来他越来越依赖先前被禁的或偏僻的中国旧时材料的做法不同,在周作人的思想发展史中,这个浪漫主义阶段很明显是西方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设想,本质上属于苏文瑜所说的那种“第二层次的现代性(second-order modernity)”,即以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的西方为典型模式的现代性。 然而,正是这种对西方模式的服从,使得周作人的浪漫主义热情出了麻烦。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设想,和他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乌托邦灵感,与他的那些欧洲前辈相比,晚了一个多世纪。在二十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国快速融入它——不管多么被动多么勉强——的过程中,适于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那种历史势头早已丧失了。尽管他也许并不能从一个全球的角度对这种迟到有足够的认识,周作人意识到,他的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异象的意识内趋向,与总是挫败它的物质现实之间,是不协调的。这想必是他在二十年代初期感到那样痛苦的主要原因。
最终,周作人不得不承认,他的乌托邦和浪漫主义异象,“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于是,在他的浪漫主义阶段还没得机会充分展开之前,他就把它了结了:1923年《自己的园地》的发表,实际上标志着这个浪漫主义阶段的夭折。 尽管“迟到”和“无效”,他这几年里的浪漫主义探险其实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还有其他几位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受了周作人的新村运动的激发,绝非是偶然的历史事件。 周作人在那几年里拥抱的乌托邦和《启示录》式的异象,反映了一种深层的民族渴望,回过头来看,它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连同其所有的修改和扭曲。 不管有多短暂,周作人在1920年前后的浪漫主义冲动把他和当时其他主要文学和思想人物区别开了。那些人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动机,与《启示录》式的异象或超验的灵感没什么关系。那个常常罩在他和他的同代人头上的称号——“偶像破坏者”——因此必须要被看成是一个并没有包含全部事实的否定性描述。因为它仅仅描述了他想要废除的,没有描述他想要建立的。有了这一《启示录》式的倾向,他那种通常被人们用纯世俗的概念来讨论的人道主义,就不乏味了。周作人与胡适不同,后者事实上更是一个偶像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并且在气质上是绝对世俗的。周作人的前瞻异象,和他对这个异象的描述,构成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贡献。
尽管他后来很快从这三年里的“理想主义”倒退出来,他所接受的浪漫主义文学事业项目,却大部分留了下来。事实上,这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他后来的思想兴趣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后来的文学生涯中。比如,他继续写作关于儿童和童年的诗,终生不辍:在40年代他重又写起关于儿童和童年的诗来,只是不再使用自由体,而是重新启用了传统格律;而且他选取这一题材,更多是出于对民间传说的学术兴趣,而不是出于任何明显的浪漫主义事业计划。 他的另一个从浪漫主义阶段残留的兴趣,就是对旧时超自然传奇的爱好。在30年代和40年代,他写了为数不少这方面的散文,它们是显示他散文写作艺术已臻炉火纯青的标本,尽管它们已不再有1920年前后的写作中那种公开的浪漫主义关怀。

废名(1901年-1967年)
就文学史来说,周作人的浪漫主义遗产与通常被描述为现实主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五四”运动的占主导地位的遗产之间存在着冲突。 尽管从未能像后者那样被树立为经典,然而,周作人的遗产是丰富而深广的。追随周作人的一些人,属于现代文学中最有趣的文学人物之列,这些人物通常与所谓的“京派”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说,在把儿童经验提升为最有想象力、最接近超验方面,在自然的环境中呈现超自然方面,在经由自然和童年来追求《启示录》式的异象方面,废名都以其导师和朋友周作人的不容置疑的继承人身份特立挺出。如果周作人没能在艺术创作中让自己被那些浪漫主义冲动冲得很远,那么,可以说,他的这些冲动在自己最有天赋、最忠诚的弟子身上得以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