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逆袭原生家庭的成功绝非偶然,也不尽是努力前提下的必然

从斑驳的原生家庭出走,成功实现教育逆袭的故事,仿佛一碗熬好的鸡汤。莉丝·默里出生在纽约的贫民窟,当她在母亲肚子里时,她的父亲还在监狱里,母亲因为怀孕被提前释放,而她的姐姐被暂时送往寄养家庭生活。孩童时期,父亲出狱与家人团聚,全家四人靠每月的救济金生活,她看到父母总在卷闻起来不像香烟的香烟抽,内心不愿离开寄养家庭的姐姐,则对日复一日的鸡蛋餐发怒,也迁怒与她不和自己一起,向父母争取更好的生活。这条父母铺陈好的堕落之路,她从童年走到了青春。母亲的去世直接导致了家庭的崩溃,却也终于有机会,让莉丝将维持家庭的权力转移到她自己身上,她成功地用2年完成了4年课程,走向她早知存在于自己生活以外的、光明的世界。这段破晓的人生被她记录下来,她称之为“从无家可归到哈佛的旅程”。(《风雨哈佛路》)

莉丝式的成功绝非偶然,也不尽是努力前提下的必然。如同一张显像的胶片,也受动力、决定、时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家庭视教育为优待而非权利,但这还不算最大的阻力,求学后不能双栖在家庭旧秩序和个人新世界之中,这是他们更大的困境。与其神化逆袭,如何在此困境下适应和进化,才更体现受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经历过偷东西、捡垃圾的绝境,在地铁站学习或是在连夜运行的地铁里过夜,对莉丝来说都不是问题,反而是一张借宿的沙发一条柔软的毛毯,消磨着她出门去上学的意志。如她遇过的一个男孩所说,从贫民窟出来混很不容易,但你必须保持清醒,做梦可以,但不能睡着。命运是场绵长的抗争,不是转折后半小时就结束的超级英雄电影,此处和别处的生活像水流入水,无法划清界线。逃出原生环境的人,依然很难摆脱重心般的家庭影响力。
埃莱娜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逃离充斥着暴力的那不勒斯,抛下无可恋的童年,尤其是避免自己与母亲的一切相似性。但当她被比萨高等师范录取,掌握了精致优雅的意大利语,嫁入了书香门第,甚至有了一位能为她的事业助力的婆婆,她仍会在情急之下操那不勒斯方言破口大骂,更惶恐地发现自己怀孕时的步态像极了瘸腿的母亲。而如果有人假想过,自己留下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她的天才女友莉拉就是她的平行世界。莉拉启蒙了她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渴望,激发了她的好胜心,自己却选择守着(或者说掌控)这座小城。对埃莱娜来说,这又成了一种煽动,她感到自己缺席了这一时期的家乡。(《我的天才女友》)
混乱中成长起来的人,因为优异的成绩去了大城市,人们习惯在他们身上施加光辉和想象,但真实的人生不是媒体投下的一片闪光灯。他们的原生家庭是人们眼中的异类,求学深造并非这些家庭的理想,更像玩笑般的念头,没有人想真的实践它,除非自己被逼到了绝境,借此出逃。而从教育中得到的秩序感令他们与混乱格格不入,他们反而成为了家庭中的异类。如果说求学是对原生家庭的拒绝,那它必然也要遭到原生家庭的拒绝。埃莱娜的母亲为自己女儿取得的成就自豪,但同时她也会粗鲁地对女儿说,别自以为太了不起,如果这么聪明的人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那么我至少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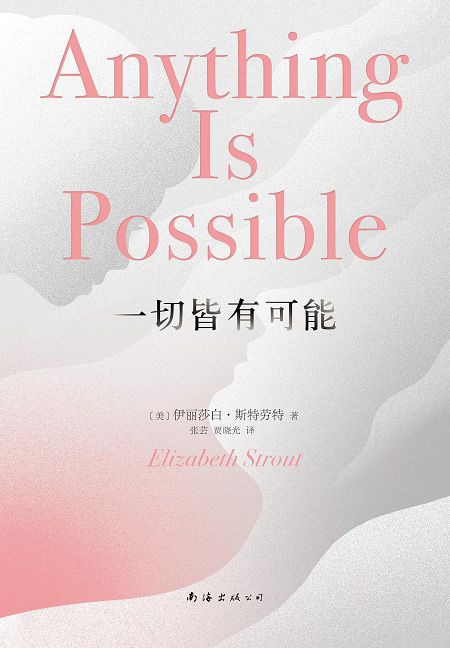
露西小时候住在丁点大的村镇的一间车库里,会在操场上被同学指着说“你们一家都臭烘烘的”;她的姐姐二年级的时候,被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穷不是耳后有污垢的理由,没有人穷得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她和姐姐没有朋友,只能用打量世界的怀疑眼光打量彼此;高中时她因为梦到自己身在大学而不敢再入睡,原因是害怕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还在这间屋子里、并永远在这间屋子里。得偿所愿,她念了大学、谈了恋爱、结了婚,如今是一位生活在纽约的作家,17年她没有再见过任何家人。小镇上的人对她有形形色色的说法,有人觉得她高傲冷漠,一走了之,也有人记得她小学时候为了取暖,一直留在图书馆,必不得已才回家。而她的婆婆在她的婚礼上,向自己的朋友介绍她时,补了一句:从一无所有中来的露西。(《一切皆有可能》)
搭新书宣传的顺风车,露西终于要回去和哥哥皮特见一面,姐姐维姬也不约而至,问她怎么从广阔的世界回到了这里。直到露西的恐慌症事隔多年再次发作,无法停止大哭,消解了维姬对她的嘲讽。“她不停地说,我来也是错的,走也是错的,都是我的错。”维姬对皮特说,“她只是受不了回到这里。这对她太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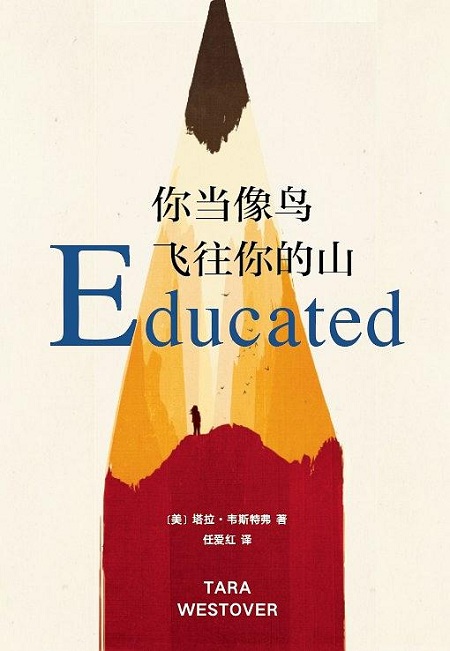
我是“一个叛徒,羊群中的一匹狼”。塔拉是这样定义逆袭后的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她与六个兄弟姐妹、一家九口人生活在山间,因为父亲的信仰,所有孩子都不去上学,所有人都不去医院。不去医院的意思是,从助产护理到烧伤坠落,都由母亲用草药和精油疗愈。不去上学倒不能和绝对的愚昧划等号,父亲会为全家朗读《圣经》,几个孩子在帮工之余也可以去镇上买课本和书来看。但不去上学必然导致了她的落后,对她来说,拿破仑和冉阿让一样,都是从未听说过的人。当她走出这座山,她无从辨别虚构的故事和真实的事件。(《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恰恰是知识,为她提供了理解现实的工具,她为此感到惊奇和着迷:零散、反覆、不稳定的物质世界,可以被捕捉、理解和预测。知识让她相信外面有一个“规则而理性的世界”,与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顺序逆行。在崭新的世界面前,理解成了要务。一开始,这并不容易。尽管通过了入学考试,尽管进入了高等学府,塔拉自知“我不是唯一感到迷茫的人,但我比任何人都迷茫”。她犯低等的错误,比如不理解备考的方法和考试的法则,不理解“大屠杀”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但她高强度地疯狂学习,竭力留在学校,为了把自己和家分开,成为一个比自己更好的人。她找到了精英社会的节奏和自我融入的切口,拿到了学位,又被导师推荐至更好的教授,攻读更高的学位。但这些常人眼中的果实,于她只是受教育过程中的表征。她“悬浮在对过去和未来的双重恐惧中”,真正的难题是自我救赎,真正的教育是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
对塔拉而言,接受教育和回归家庭是个进退两难的选择,只不过求学反而成了一条退路。家人都有存在自己生活中的价值和理由,只是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就成了泥潭。父亲被(他们不愿承认的)被迫害妄想操控,成为一个执意建造方舟的诺亚,在上帝并没有让洪水泛滥的时代,显得荒谬。母亲坚持塔拉是家里“冲出熊熊大火走出去的人”,斩断她顾及父亲反对而对上学的迟疑,催她赶快离开;又拒绝独自出席她的毕业典礼,不敢相信她会期待一个人女人在丈夫不到场的情况下出现。更不用说几次对她实施身体暴力和精神羞辱的哥哥,她向父母揭穿他的暴力行为后(依然得到了包括其他受害者在内的众人的包庇)间接和直接受到了他的死亡通牒,最后被他从生活中完全隔离出去,在绝交的谩骂电子邮件最后,他却伤感地写道,爱家人胜过一切,爱你胜过家人,你却在我背后捅刀。他们出自天性地爱她,也同样出自天性地伤害她。家庭中爱的型态令人生疑,家人的情感充满不确定性,每一次温情的发生都像奇迹。奇迹会出现,但人无法仅仅依靠奇迹活下去。她愿意离开家,接受学校的催眠。
通过接受教育,塔拉窥见了人类的历史并思索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对显而易见的事实渐渐觉醒,对自我形成了基本认知。当她假期回家,父亲或哥哥一如既往地向她开着玩笑,他们的语气没变,动机没变,但她的耳朵变了,它听到的不再是其中的玩笑,而是一个信号。沿着求学这条路,她退出了父权的边界。理解。理解身在其中的冲突,理解对自己的谴责,理解通往辩解和发声,不再沉默或白白阵亡。过去塔拉身上除了无知,还有无知带来的羞耻感。旁人对此困惑、心怯,但“困在过去的自我”,只能亲手将她“送往别处”。受教育改变了她看待世界的方式,她不再活在别人的讲述中,洗刷莫须有的羞耻感,承担剥离原生家庭的痛苦。推翻旧信仰才能搭建她的新生活,才不负她为此付出的全部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