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匈牙利文学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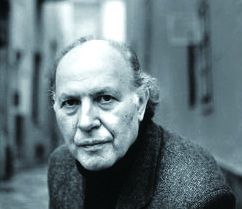
凯尔泰斯
匈牙利文学译介历史回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匈牙利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友好关系全面发展,领导人互访等各种形式的往来密切,各领域合作不断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受到当时的文化策略导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主要译介能够体现民族斗争意识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这其中,最多的要数匈牙利民族主义代表诗人裴多菲。
早在1907年,鲁迅就将裴多菲同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大作家相提并论,并称他为“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从上世纪二三十年起直到21世纪初,中国对裴多菲的研究从未停止。50年代开始,国内译介了一大批匈牙利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包括费雷斯·彼得的《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纳吉·山多尔的《和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约卡伊·莫尔的《金人》《铁石心肠人的儿女》(作家出版社,1953年)、《黄蔷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此外,我国译介的国际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作家查尔卡·马特的《查尔卡小说选》收录了三类作品:描写帝国主义战争、描写苏联国内战争以及揭露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本质的作品。另一位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伊雷什·贝拉的两部作品《祖国的光复》和《蒂萨河在燃烧》则分别由俄文和德文转译。现如今,当我们回望历史时不难发现,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和意识形态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介匈牙利文学时的选择,同样,当时中国了解到的匈牙利文学也不全面。这一时期的匈牙利文学译介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大多通过其他语言转译;二是选择作品倾向性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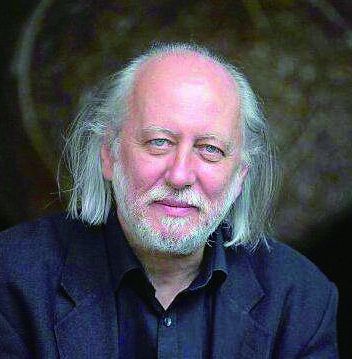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1976年之后,经过了10多年的沉寂,对西欧与北美文学的译介日渐成为外国文学译介的主流,中东欧文学的译介传统也很快得以恢复。这其中,有一批作品是经典重译,比如兴万生译的《裴多菲文集》。另外,选译文学作品集的趋势日渐明显,收录有匈牙利文学作品的集子有《东欧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东欧短篇小说选》(冯植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匈牙利民间故事选》(孙小芬编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匈牙利现代小说选》(德里·蒂博尔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神秘的王后:匈牙利民间故事》(徐汝舟编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东欧剧变后,我国对东欧文学的译介面临许多的挑战,东欧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曾一度走向没落,最显明的例子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室解散,这个曾经人丁兴旺、业绩辉煌的团队建制不复存在;再加上出版行业的过度市场化,无法盈利的东欧文学作品最终没有逃过被边缘化的命运。然而,即便如此,东欧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仍在进行,只是动作放缓了些,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打磨,最终呈现出系列成规模体系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收录有匈牙利文学的成果有:《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的“捷克—匈牙利”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东欧卷》《世界经典戏剧全集·东欧卷》《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东欧卷》《东欧国家经典散文》以及《祖国母亲爱情:匈牙利著名诗人诗选》等。
新世纪以来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匈牙利文学在中国逐渐受到重视。如果说中国读者通过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认识了匈牙利文学,那么,阅读凯尔泰斯·伊姆雷才让中国读者真正地靠近匈牙利文学。凯尔泰斯的诺奖授奖辞称,他的作品“以个体的脆弱体验反抗历史的野蛮强权”。裴多菲和凯尔泰斯,一位是捐躯沙场的民族烈士,另一位则是看透了“屈从即生存”的弱势公民,遥遥相隔一个世纪,虽然他们的生活年代、个体经历、创作内容都不一样,但两人的创作主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反抗强权,这也是匈牙利文学史的精神写照。

艾斯特哈兹·彼得
2002年,当瑞典学院宣布凯尔泰斯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谁是凯尔泰斯,这个在此之前从未走入过中国人视野的作家,激起了所有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好奇。不过,人们迅速行动起来,2002年底时,对凯尔泰斯的介绍便逐渐展开。《世界文学》2002年第6期率先公布了凯尔泰斯获奖的简讯,随后,高兴在《外国文学动态》2002年第6期撰文介绍了作家的生平以及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凯尔泰斯获奖,让中国读者的目光重新聚集到匈牙利文学。匈牙利著名文学评论家瑟雷尼曾说:“以前我们的文学旗帜上写着裴多菲的名字,现在什么人也没有了。”这话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匈牙利确实没有再出现像捷克的昆德拉、波兰的米沃什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不过,凯尔泰斯获奖后,匈牙利文学译介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开始逐渐得到改变。这首先体现在对凯尔泰斯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上。作为一份译介外国文学的前沿杂志,《世界文学》在2003年第2期推出了由旅匈学者李震翻译的《侦探小说》《惨败》《无形的命运》《苦役日记》《另外的我》五部作品的选译以及作家的获奖演说辞,这是凯尔泰斯的作品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
2003年开始,一批从奥斯维辛之于作家的生活、创作等角度出发探讨凯尔泰斯作品的文章相继发表;凯尔泰斯的早期创作不被世人认可、其作品推出后不受重视的遭遇也被研究者挖掘、剖析。而凯尔泰斯代表作Sorstalanság的题目翻译也曾一度成为学界的探讨热点。该作最早被译成《没有命运》,应该来自英文标题Fatelessness。2003年的一众评论文章中,又将该译名改成《无形的命运》。《一步一步——凯尔泰斯·伊姆雷和他的〈一个在命运之外的人的传奇〉》一文的作者杨宏芹为德语研究专家,她根据该著的德文题目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将中文题目译成《一个在命运之外的人的传奇》。2004年,此书以《命运无常》为题出版单行本,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广为人知的译名。不过,匈牙利文学专家许衍艺在她的研究中发现,凯尔泰斯曾在《苦役日记》中对“命运”做过这样一番诠释:“我将什么称作命运呢?当然是悲剧的可能性。然而外部的决定,那耻辱的烙印将我们的生命挤压进了特定的集权主义的一个处境中,一种无能为力之中,使这种可能成为虚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强加给我们的决定当成一种事实自始至终地生活在其中,而不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相对的)自由所带来的必然性中,我便称之为无命运”。因此,许教授认为,该著应该被译为《无命运的人生》。2010年,许衍艺翻译的《无命运的人生》问世,这也是凯尔泰斯这部代表作的第二个权威译本。2004年,凯尔泰斯的《命运无常》《英国旗》《另一个人》《船夫日记》四部作品陆续翻译成了中文。2014年,《清算》和《侦探故事》又被译介进来。
2006年以后,随着凯尔泰斯第一批作品的中文版推出,对作家的研究也转向了纵深。《西西弗斯的神话中的石头——评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小说〈惨败〉》(侯景娟,2007年)对小说《惨败》中贯穿始终的母题——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发展演变进行讨论,并具体分析了小说《惨败》对这一神话的独特运用。凯尔泰斯身上背负的奥斯维辛烙印,总是能引起研究者对其作品中“大屠杀”主题的兴趣。《凯尔泰斯生存哲学探析》一文(阚兴韵,2007年)一文揭示了凯尔泰斯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所有人都只是功能性的人,并对凯尔泰斯的这一思想进行溯源,进而分析了作家对于现代性和集权主义之间关系的探索。《凯尔泰斯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初探》(商金艳,2010年)一文关注的是在奥斯维辛的集权统治下,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形成过程,及其在作品中的呈现。基于“无命运”这一结构性诠释《论凯尔泰斯小说的自传性书写》(孙燕君,2013年)一文考察了凯尔泰斯小说“集中营”主题与其创伤记忆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通过对个体“无命运”性的探析,呈现出对集权制度的反思。《无命运的存在性建构——试论〈无命运的人生〉的主体性反思》(李安斌、张凡,2017年)一文从对《无命运的人生》的隐喻性解读、主体性解读两个方面,对作品中人的“无命运性”进行反思,并认为,人的主体性反思可以超越“无命运”,具有荒诞感的现代人不必选择非生即死的穷途末路,而是能够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反思达到对自我的肯定,安抚时代带给一代人惨痛的回忆。
凯尔泰斯获奖后,作为东欧文学重镇,有好几位匈牙利作家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线。艾斯特哈兹·彼得是当代匈牙利文学中一个绕不开的作家,他的两部作品《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在2009年和2010年被引进中国。这位作家出生在19世纪欧洲最显贵的家族中,有人说,一个欧洲人,即使没读过彼得的作品,也不会不知道艾斯特哈兹伯爵家族。这个家族曾经走出过匈牙利的大臣、将军、主教和大主教。艾斯特哈兹的祖母曾是一位法国公主,他的祖父莫里茨伯爵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担任过匈牙利总理。但1950年作家出生时,这个家族早已衰败,艾斯特哈兹成了一位被剥夺爵位的农民的儿子。一个整天踢足球的数学系青年,成为写作领域的领头标兵,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人看来都颇为离奇,却被艾斯特哈兹视为理所当然:“我觉得写作、足球还有数学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都是一个场地,这个场上有特定的规则。”艾斯特哈兹在写作时善于创造新式词汇,经常串用拉丁语、德语、法语、英语和各种谚语、俚语,还曾经创作过一部名为《悬》的实验性作品,该作两百页的篇幅,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并以半个前括号结尾,以示作品的开放性,正因如此,艾斯特哈兹被称为“匈牙利的乔伊斯”,他在世时曾多次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是匈牙利文坛的领军人物。我们从《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这两部作品中,看到了作为数学家的艾斯特哈兹在各种对立的矛盾中追求着细腻的平衡,比如男人和女人、荒谬与严肃以及冷峻的写作技巧与形而上学的敏感。这是多年来,他作为一个受过专业数学训练的创作者为自己建构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艾斯特哈兹在不停破坏、重建。而对艾斯特哈兹的作品进行中文翻译,也是对译者文字功底、学养和耐性的一种挑战,需要他们用中文建构一种全新的、与原文相对应的文学语言。
苏契·盖佐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太阳上》是一个选集,前半部分是诗歌,后半部分选自他的两部故事集《假如章鱼在克罗日瓦尔喘息》和长篇政治寓言小说《林普普》。2017年,苏契以诗人的身份出席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他在诗歌周的开幕式上朗读了诗歌《太阳上》。苏契本人拥有多重身份,他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历史上曾归属于匈牙利,一战后被划到罗马尼亚,因此这个地区也成为20世纪匈牙利人寻找身份与激情的土壤。上世纪70年代后,面对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苏契是当时少有的敢于站出来的反抗分子,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也为他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现在,他也是惟一一位能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个国家的高层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的政治家,也是他,在匈牙利政治思想领域率先提出了“打开东大门”,成为高度重视与亚洲关系的倡导者之一。他频繁出访中国,不仅在政治贸易领域,也在文化、知识领域为两国的关系体系打下了新的根基,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苏契的作品中,会不时出现与中国相关的元素,比如《假如章鱼在克罗日瓦尔喘息》中的一篇《屠龙的圣乔治克罗日瓦尔兄弟》提到了克卢日龙和中国龙的不同:“在我们这里跟在中国不同,中国人的龙日是在春节之后。”作家说的应该是我们的农历二月二吧。同样的,在《林普普》中,一篇《关于灵魂、中国皇帝和长城》让人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说残篇《中国长城修建时》。卡夫卡文中对中国长城修建的想象与奥匈帝国的政治现实之间存有一定程度的隐秘关联,这正是卡夫卡自身对国家认同方式的表现。同样的,在这个短篇中,苏契用中国长城的意象,表达了他努力追求理想,但却无法达到理想的现实。他说,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都是在为同样的问题寻找答案,有朝一日,这些问题会受到关注。苏契在第二部中文版诗集《忧伤坐在树墩上》收录的一首诗歌《一位宇航员的日记摘抄》中向李白等唐朝诗人致敬:“在一家名为‘死亡诗社’的北京酒吧……李白正在谈论死亡/我插言说:——诗人们,你们对月球都知道些什么?”
谈到李白,就必须提起另一位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他也是李白的崇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曾来过中国三次。1998年,作家被欧洲的一家新闻组织选为世界范围内十二位有影响力的作家,来到中国。按照要求,他选择了自己最崇拜的李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座古城,所到之处,他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的作家、学者谈论李白,甚至在路上与普通行人谈论这位“诗仙”。旅程结束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说,他所记录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作为诗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记。作家的散文体游记《只是星空》便展现了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形象。中国读者读到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第一篇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说《茹兹的陷阱》,刊登在《小说界》2006年第2期;两年后,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狂奔如斯》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直到作家2015年获得了布克国际文学奖后,他的成名作《撒旦探戈》才被译介到中国。
匈牙利作家群与“蓝色东欧”
20世纪的匈牙利历史决定了这个国家有许多作家走上了“流亡”的命运。他们有的从匈牙利前往海外,有的从被分割出去的土地上回到匈牙利,而“分离”是他们的创作中无法拭去的一抹生命底色。这些年,国内的匈牙利文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翻译了一批这类作家的作品,这里面有马洛伊·山多尔的六部作品:《一个市民的自白》《烛烬》《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反叛者》《分手在布达》《草叶集》。1948年,在国家的政治文化面临巨大转折的关口,马洛伊去国离乡,开始了逃亡的漂泊生活。他在瑞士、意大利生活过,最后客死美国,其作品曾在匈牙利文坛消失达40年。马洛伊去世多年后,作品才在匈牙利出版。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展现了他对一个理想“市民”的追求:平静、郑重,充满尊严。这令人联想到《布达佩斯大饭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那个世界早在他进入之前就已经消逝了,只不过他极为优雅地维持了那个幻象。”难怪有中国读者感叹:马洛伊的文字中最令人感动的不是一个人内心暗潮和时代浪潮的暗合,而是一个作家对自己命运的确认。
另外还有一些流亡作家来自罗马尼亚境内的匈族区,比如德拉古曼·久尔吉和巴尔提斯·阿提拉。这两位作家的身世非常相似:80年代中后期,他们随家人从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逃到匈牙利,当时罗马尼亚社会的高压生活,为作家的青少年时期涂上了一层晦暗的色彩。我们在德拉古曼的《摘郁金香的男孩》中看到了一个十岁孩子对苦难的记忆,也在巴尔提斯的《宁静海》中看见了社会制度对人造成的戕害,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正一点点地丧失掉灵魂和人性,沦为只为制度而存在的僵尸。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流亡成了思考的土壤,苦难成了写作的养分,怀疑成了观察的方式。
自从匈牙利“向东开放”和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和“16+1”经贸合作以来,中国与匈牙利之间不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在文化交流上也更为频繁。与此同时,国内的翻译者也对早期的东欧文学译介进行了深刻反思。《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说:“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个既定的概念。” 因此,花城出版社自2012年起,推出了“蓝色东欧”系列,希望让中国读者从中读到一个另一种色彩的东欧。在“蓝色东欧”系列中被译介的匈牙利作家作品有瓦莫什·米克洛什的《父辈书》、查特·盖佐的短篇小说精选《遗忘的梦境》、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和《天堂超市》、萨博·玛格达的《壁画》和《鹿》。《父辈书》的作者瓦莫什·米克洛什被称为匈牙利的国宝级作家,他的这部著作是一部宏伟的家族传奇,时间背景纵跨三百多年,记录了整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马利亚什·贝拉既是作家,也是一名画家,他的艺术作品总会给人一种“疯狂”的感觉,曾被人拿来与查特·盖佐的小说作类比:“马利亚什画画,就像查特·盖佐写日记:低调但刻意地表现粗暴,几乎是用变态的方式。”我们如果去读查特·盖佐的《遗忘的梦境》中的《弑母》和马利亚什的《垃圾日》,就会明白这句评语的真正含义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作品均是在中国第一次被译介,且都译自匈牙利原文。这些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算萨博·玛格达——从新文化运动介绍匈牙利文学以来,这是惟一被译介的匈牙利女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萨博·玛格达的作品已被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无论冷战中还是冷战后,“萨博·玛格达”都是匈牙利文学的一张国际名片。
自2006年起,文学杂志《小说界》的“外国新小说家”栏目先后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凯尔泰斯·伊姆雷、塔尔·山多尔、帕依·安德拉什,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诗人沃洛什·伊斯特万、德拉古曼·久尔吉、纳吉·盖尔盖伊、蒂萨·卡塔、马利亚什·贝拉、巴尔提斯·阿提拉、马洛伊·山多尔、桑多·T. 卡波尔、帕尔蒂·纳吉·劳约什等人的短篇小说或是长篇选译,这个“外国新小说家”栏目,是由旅匈翻译家余泽民主持的。在新世纪的匈牙利小说译介方面,余泽民功不可没,2017年的布达佩斯国际书展上,他被授予“匈牙利文化贡献奖”。颁奖词称“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当代匈牙利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他在这个领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但与匈牙利思想巨擘辈出的情况相对的是,除了余泽民等数量极少的匈牙利文学专业译者以外,我们很少能够找到愿意将身心扎根在文学土壤中的译者。同样的,在对引进作品的后续研究方面,目前看来是明显不足的。我们不缺需要介绍和研究的作品,我们缺少的是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两国文学交流的优秀译者和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