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作品能见证奥斯维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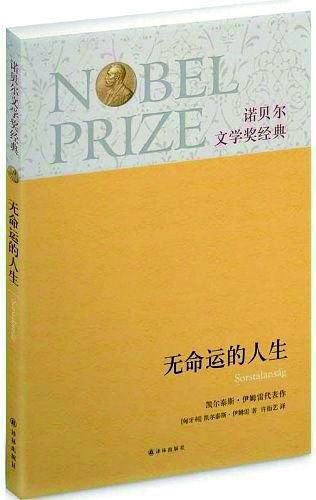
虚构作品能见证奥斯维辛吗?这几乎是一个伪问题。然而,如果打开关于大屠杀的评价史和叙事史就会发现,其中的表述和逻辑波谲云诡,很多人对事件本身的态度相当暧昧,远非三言两语能描述清楚。据彼得·诺维克考证,即便是在远离欧陆的美国,人们对大屠杀的态度也一度“冷漠”,形成相当复杂的“集体记忆”。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里,大屠杀的确是不可以不容易不可能被言说的,它太残忍、太恐怖、太无情,以至于成为某种神秘的禁忌,所以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写首诗,也是野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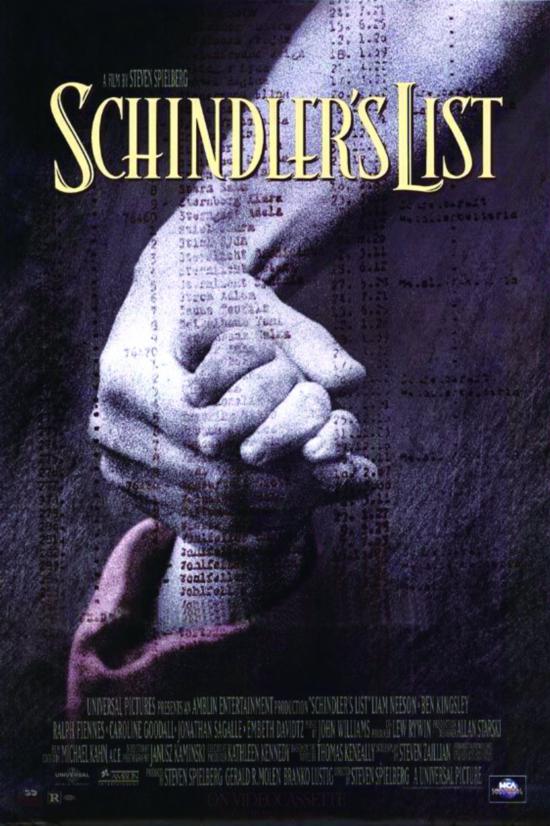
《辛德勒名单》电影海报
艺术面对大屠杀彻底失语,以至于人们第一次看到乔治·史蒂文斯的《纳粹集中营》和阿伦·雷乃的《夜与雾》时,其震撼程度不亚于直面集中营本身。这导致以电影建构大屠杀话语的可能被付诸于实践,并不断丰富:《浩劫》成为反思大屠杀电影的开山之作,《辛德勒名单》开启了用虚构的艺术还原真实大屠杀的“描述”时代。那之后,大屠杀电影开始兴起,及至2015年,匈牙利电影《索尔之子》已经成为众多大屠杀电影其中之一,如果不是获得了包括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甚至籍籍无名。这部电影讲述了纳粹集中营“特遣队”队员犹太人索尔在清理毒气室时发现自己“儿子”的尸体后历尽艰难险阻执意夺回“儿子”尸体并寻找犹太牧师为“儿子”下葬的故事,冷静、克制、缓慢但发人深省,继承了杨索和贝拉·塔尔的匈牙利电影传统。有所不同的是,《索尔之子》最重要的表征是作为背景的大屠杀,若不考虑大屠杀,这部电影绝不至如此深刻。
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看到了这种深刻并不能自持,以深沉慷慨的激情给《索尔之子》的导演拉斯洛·奈迈施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他对这部电影的欣赏与热爱。这封后来被命名为《走出黑暗:写给〈索尔之子〉》的信一气呵成,即使不是收信人的读者也舍不得喘息,想尽快读完。信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地表明,《索尔之子》用影像虚构的“噩梦”带着电影的力量深深俘获了写信人的心,再一次唤起他对“噩梦”及其意义的思考。第二部分指出,如果奈迈施以四张纳粹行刑队员拍摄的照片为逻辑原点思考电影,那么电影注定是“黑色”的,要么是阿多诺所谓激进艺术的象征,要么是沉默的象征,可是导演却另辟蹊径,用色彩组织影像,让主人公和观众“走出黑暗”,并在此过程中使观众“碰触”到电影的本质,以完成对“恐惧-影像”的建构。第三部分分析了索尔的性格和形象,认为在这个寓言中,索尔表现出的是一种“分裂的人”的意志,是一种“超越绝望”的意志,这是他能够坚持下去的行动元。第四部分指出,虽然索尔看上去是一个如俄尔甫斯一样的失败者,但是他却创造了奇迹,电影结尾的几个镜头建构了一个关于“创造儿子”的谱系,使观众能从历史的“黑洞”走出来,并对此深信不疑。

《索尔之子》电影海报
这么一封30多页的长信,于贝尔曼究竟想表达什么呢?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封长信呢?除了作为电影观众的热情之外,当然也是他作为艺术史家的身份使然,所以在这封信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影像或图像的表述和言说。比如,他分析了电影第一个镜头中的黑色、绿色和红色,以及画面从模糊到清晰和使人局促的场面调度,认为这是导演引导观众“走出黑暗”的预言,在这个镜头中建立观众和电影的“触碰”和关联。再比如,他分析了影片最后小孩子在门口出现的镜头以及索尔惟一的笑容,索尔的身体在当时虽然是危险和不安全的,但他的内心世界非常平静,为“奇迹”画上句号。这些具有图像学意义的画面虽然重要,但只是形式而不是意味,似乎并不是于贝尔曼想要言说的主题。实际上,于贝尔曼想要和奈迈施讨论的是,如何用虚构的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的问题。在于贝尔曼看来,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看上去是一个简单又充满挑战性的问题,但他对奈迈施信心十足,他说:“您每一个镜头都不停地提出了场面调度的现实主义这个深刻的问题。您冒着风险去建构了某种被判定为不可想象的历史事实的现实主义。”奈迈施的策略何以如此高明呢?是因为,他一方面把“每一个镜头都聚焦于一种令人赞叹的记录的精确”,另一方面又“警惕聚焦”而寻找到一个“恰当距离”。可见,在于贝尔曼看来,用艺术再现大屠杀,需要平衡真实和“距离”之间的关系,惟其如此,才能准确把握关于虚构与“真实”的艺术尺度,也正在此意义上,《索尔之子》对真实和虚构的拿捏使于贝尔曼在观影之后产生了与奈迈施通信的激情。
无独有偶,就在于贝尔曼给奈迈施写下这封长信的几年前,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也在思考和于贝尔曼相似的问题,并于2011年出版了《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如果说于贝尔曼将着眼点放在艺术和大屠杀的关系上,那么米勒则对小说与大屠杀的关系进行了集中探讨。他的理论支点在于,对阿多诺所谓艺术作品不能反映大屠杀的反抗,和小说如何为大屠杀作证。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米勒以他惊人且令人敬佩的文本细读能力分析了大屠杀前后多部与大屠杀存在必然或不必然联系的小说,深刻地洞察到了卡夫卡小说对奥斯维辛悲剧的预言,并以《辛德勒名单》《黑犬》《鼠族》和《无命运的人生》为中心深入分析了几部大屠杀小说与事件本身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指出托妮·莫里森《宠儿》中黑人奴隶所遭受虐屠的文学表达与大屠杀小说对历史的还原与呈现异曲同工。其中,米勒最重视的是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他用大量的篇幅分析文本,认为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成为大屠杀最有力的“证词”。
《无命运的人生》是匈牙利小说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久尔考毫无征兆地在上学的途中被送进集中营之后的所见所闻,和其他犹太人命运不同的是,他奇迹般地活着走出了集中营,并回到故土,但却少有人相信他所描述的集中营经历,就更不用说理解了。小说中久尔考的经历也是现实中伊姆雷的经历,加之大屠杀本身已经不断地被确证,所以读者和小说中的其他人不一样,宁愿也必须相信久尔考在布痕瓦尔德和蔡茨的经历是真实的。伊姆雷凭借《无命运的人生》和之后的两部小说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也必须注意到,伊姆雷的犹太人身份和匈牙利读者对他的不认同,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争议使若干年来对《无命运的人生》的研究乏善可陈,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部平庸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自传体小说。
就是这样一部小说,被米勒挖掘出了巨大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回答《共同体的焚毁》提出的问题,即小说如何为大屠杀作证。首先,必须厘清米勒的初衷,他并不相信“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写首诗,也是野蛮的”,所以不断挑战阿多诺关于大屠杀表述的权威,认为保罗·策兰和伊姆雷等大屠杀幸存者无视阿多诺的禁令并创造出了并不野蛮的“诗”,已经说明文学是见证奥斯维辛的有力方式,也为“小说具有作证的意义”提供了历史的明证。其次,单就《无命运的人生》而言,米勒认为,伊姆雷在小说中运用了特定的叙事方法,用有效的故事和更有效的情节为大屠杀作证:叙述者语言反讽;作为叙述者的我和作为经历者的我在同一个虚构人物中合二为一,“我”的双重性贯穿始终;严格的时间“顺序”,都是在指向大屠杀的真实性。再次,恐怕连米勒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无命运的人生》虽然只是他“小说可以为大屠杀作证”的一个注脚,但是他对这部小说的文本细读显然挖掘出了其中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让若干年来关于伊姆雷文学造诣的争议得以不存在争议地终结。
虚构作品能见证奥斯维辛吗?在《共同体的焚毁》中可以看到,米勒不厌其烦地反复翻阅这部小说并尝试在文字的细节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和于贝尔曼做的是相同的工作。他们都相信,虚构作品能够见证奥斯维辛。在《索尔之子》和《无命运的人生》中,观众和读者可以看到很多相似的东西,就内容而言,索尔和久尔考那种对“生的挣扎和死的坚强”,在“无聊”中存在且向死而生,表现得惊人一致。虽然他们的人生已经没有命运,但他们事实上无时无刻不是在反抗绝望。就形式而言,《索尔之子》中缓慢的跟镜头、颤抖的手持拍摄、清晰的特写及模糊的后景和《无命运的人生》中本身是经历者又是叙述者的“零度”叙事,实际上存在着关于历史真实的共同指向。同样,也能在《走出黑暗》和《共同体的焚毁》中找到电影和小说的相同之处,比如,索尔的“成功”被于贝尔曼看做是一个“奇迹”,而在《共同体的焚毁》中,米勒认为,“久尔考这种顽固的、难以遏制的情形警觉和他从‘穆斯林’状态的回归,是小说带有奇迹特点的地方,这两个特点和其他‘奇迹’一道,让久尔考渡过重重危情,成为幸存者。”“奇迹”,甚至可以被看作所有从集中营中走出来这个“事件”的共同特征,其本质在于,共同体被焚毁了,共同体卑微的意志还在。
更重要的是,在如何用虚构的艺术作品表现真实的历史这个问题上,于贝尔曼和米勒也给出了惊人一致的答案。于贝尔曼认为,一是要准确地描述和再现,所以他感佩奈迈施“记录的精确”,比如“所说的台词、表演的手势、色彩的使用、建筑元素以及纳粹行刑队内部的社交关系等”,都指向了《索尔之子》高度的真实,电影中赤裸的尸体和将赤条条的活体推入焚烧坑的镜头,能够引起观众极大的感官不适,即便耐受者也不寒而栗,就是在证明再现的真实性;二是要保持“恰当距离”,也就是用一些艺术再现和表现的手法对客观真实进行文学和艺术的“装饰”,这种装饰也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电影迸发出更璀璨的艺术光辉。米勒也是这么说的。在米勒那里,虽然为奥斯维辛作证是困难的,但阻碍可以克服。《无命运的人生》将叙事者和经历者合二为一作为叙事的主人公,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本身就是《索尔之子》中“精确的记录”。另外,米勒相信,伊姆雷关于大屠杀的历史与文学“事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所以久尔考与集中营的很多“往事”存在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通过反讽表现出来。米勒说:“久尔考的反讽叙事与他所再现的可怕事件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以便读者有深切的感受。这样的反讽瓦解了读者不愿直接面对大屠杀的心理。”就是说,“距离”使读者稍稍走出历史世界而进入艺术世界,这也是小说艺术张力的一个侧影。由此可见,于贝尔曼和米勒在并不相同的著作中发现并回答的是一个相同的问题,他们都相信,艺术可以表现大屠杀,虚构作品能够见证奥斯维辛,而且奈迈施和伊姆雷等人实现了这种可能。所以,奥斯维辛之后,还可以写诗。
如果不是大屠杀,《索尔之子》和《无命运的人生》不会相遇,《走出黑暗》和《共同体的焚毁》也不会相遇。然而机缘巧合,这四部作品真的就在关于大屠杀的文学和历史场域相遇了。其实,小说和电影是在讲故事,历史也是在讲故事,区别在于,历史的故事需要绝对精确,小说和电影的故事则更侧重于关于艺术的“装置”。大屠杀小说或者大屠杀电影似乎是一个特例,必须高度平衡“精确”和“装置”之间的关系,它们才具有有效性和通约性,才能回答“虚构作品能见证奥斯维辛吗”这个问题,并给出准确而精致的答案。从人类如何通过艺术面对历史的意义上说,于贝尔曼和米勒的思考都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