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记日记与看月一样,首应成为赏心乐事
记得上小学时,曾经热衷于写日记。所记不过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却忘不了在日记本的扉页写上“日记日记,个人秘密”的字样,日记本也郑重其事地深藏在抽屉里,为的是不让家人看见,免得不愿被人知道的“小隐私”曝光,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这时还隐约听说,日记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每天记日记于是成为一种乐趣。
可没过多久,《雷锋日记》发表了,我的日记观开始动摇。雷锋做的那些好事令人感动,当时也佩服他会写出那么多传诵一时的格言,不过,读的时候,忽然发觉日记也是可以写给别人看的,不一定为自己而写。原来日记不一定属于个人秘密,可以不必保密。

《雷锋日记》
一个暑假,老师规定我们每天写一篇日记,开学时,和假期作业一起上交。这次虽然坚持下来,受到了表扬——因为班里很少同学能一天不漏地写到底——但那完全是靠毅力,不是凭兴趣。实际上,这一次记日记成了一件苦差事。每天要想出一些老师可以接受的事情、观点,想不出来,就关心国家、国际大事,抄报纸,再加点评论,心里明白,塞责而已。写写给别人看的日记的滋味算是尝过了,不好受。
年渐长,见闻渐多,发现现在公之于众的日记情况并不一样。以我接触较多的近代人物日记为例:一类初心是为自己而写,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表了,如吴虞的《吴虞日记》;另一类本来是为自己写的,但也出示给别人看,如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还有一类根本就是为他人而写,如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即系遵照清廷“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的规定而作。后两类日记还不在少数。记日记时,心中已存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原则,也许表现了其人的磊落光明,也许是心有顾忌、文网森严的反映。
前者无甚可说,后者却有实例。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写的《使西纪程》,就因为肯定了西方文明而大受围攻,并遭到奉旨毁板的厄运。若是这样,为他人而作日记(不论是否情愿)也不无值得同情之处。当然,不写也是一种避短的办法,不过那对后世的历史文化研究损失太大。
撰写日记古已有之,只是难以考订谁是“吃螃蟹”的第一人:或说是东汉《封禅仪记》的作者马笃伯,或说是唐代《来南录》的作者李翱。不作文体学研究,倒也可以不去细究。有意思的是,古代人的日记往往是文章的一部分,因此大多以一个事件或一次旅行的始末为日记的起讫,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陆游的《入蜀记》等;而《徐霞客游记》也是几次旅游的日记合订而成,不出游时则付阙。这或许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日记卷册不多的原因。

到了近代,李慈铭“始以巨册自夸”(王闿运《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序》),其《越缦堂日记》今存六十四册,从1853年到1889年,三十余年不废其事,确可佩服。《越缦堂日记》也借给人看,最后的八册日记即因李慈铭去世、借者不还而失踪,可知李慈铭记日记并非只为自己。想要留名后世的名士反为名所累,竟使巨册日记不能全帙,未免可惜。由此想到,日记或许还是写给自己看的好。
不过,这里又有新的矛盾。为自己而写的日记往往记一己之琐事微情,与史学研究者期望从中发现第一手重要的社会史料的要求相违拗;而为别人而写的日记又往往多有隐晦,抹煞或模糊了作者的真性情。明人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中描述了五类看月之人,最后一类为“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我以为,用后世人的眼光来拣选,前人日记的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记日记与看月一样,首先应成为赏心乐事,娱一己之情;被他人看到,也觉得有情趣、可援引更好,只是不要故意作出给他人看之态。
能兼顾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其实不容易,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相当的社会交往就办不到。现在流传的日记既富史料,又经得起反复阅读的并不多,原因就在这里。而这类日记也因此多出自文化名人之手。如此推究,作者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就成为保证日记传世的必要条件。这在近、现代人物日记的印行上,表现尤其明显。

我读日记,倒也不苛求。有因研究需要而读的,更多的是为了有趣、好玩。既非史学工作者,对资料性要求自然不高。甚至看到收录了几种日记的《庚子记事》一书,编者为突出史料价值,特意将“资料中所记生活琐事和空泛的诗词,均略为删节”,至今仍觉得颇为遗憾。这些不被史家看重的东西,在我读来,也许更有味。
我的眼光比较偏,我感兴趣的地方,别人可能会觉得毫无意思、没有价值。可我还是认为,正像作诗要讲究“诗眼”,诗才有神;看日记也要能窥破作“眼”处,方得其趣。
胡适的《藏晖室日记》(1910年),我专读他的叫局、打茶围;梁启超的《双涛阁日记》(1910年),我专读他的斗牌;吴虞的《虞山日记》(1911—1912年)与《爱智日记》(1913—1919年),我专读他的计算稿子发表迟速;黄尊三的《留学日记》(1905—1912年,《三十年日记》第一部),我专读他的思乡梦及多病;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1893—1903年,中缺四年),我专读他的新学书目与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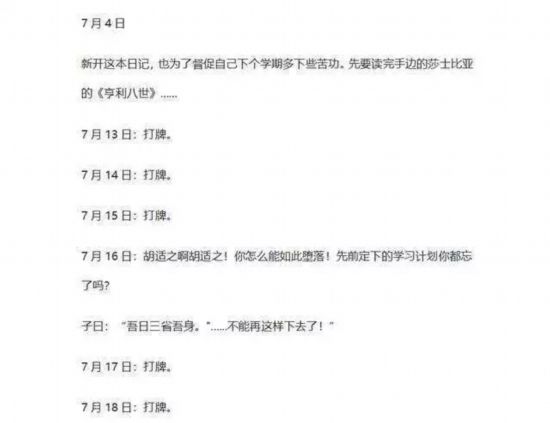
胡适日记节选
胡适日记使我发觉,出入娼家是清末上海文化人的时髦,从而想到林纾小说写革命党在妓院谈革命(如《梅寿阳》),未必是诬蔑不实之词。梁启超日记使我惊异,他的牌瘾如此之大,据说每天最少要打八圈麻将,却仍能毫不费力地以日成五六千言多至八千言的高速率写作,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字的著述。吴虞日记使我发现,这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对个人的文章影响极为看重,他的固执与自信见诸文字,便时有惊人之论产生。黄尊三日记使我感觉压抑,数万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求学的壮举中,竟包含着如此多的艰辛与痛苦。孙宝瑄日记使我欣喜,他认真研读新学书籍,日有所进,正好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演进的艰难历程。
如果不作专门研究,读日记尽可凭兴趣出发,和读专著不同,不妨随意翻阅,或跳读,或倒读。一本内容丰富的日记,经得起读好几遍。像《忘山庐日记》,我起码读了四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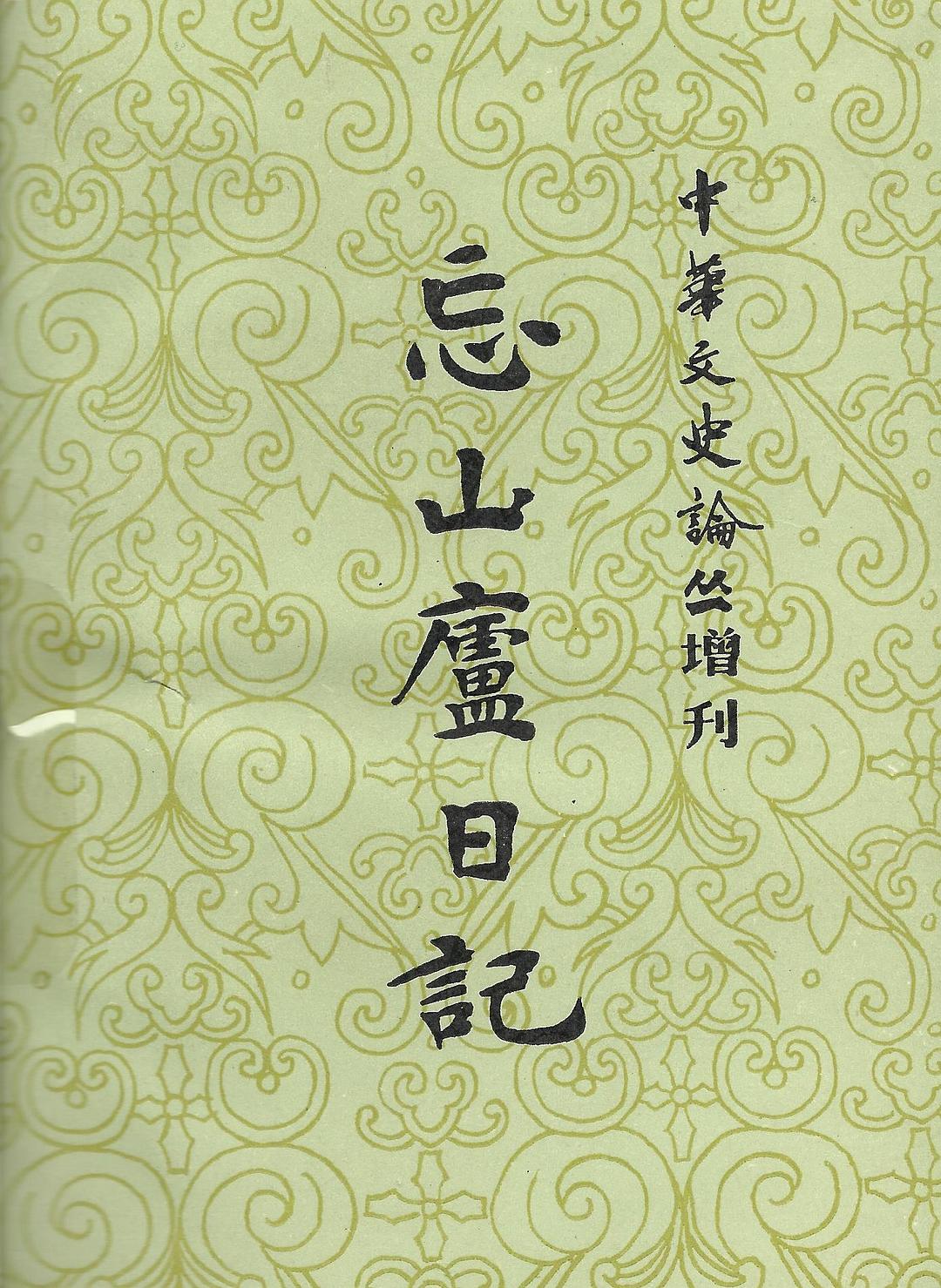
孙宝瑄日记初名《梧竹山房日记》,后改名《忘山庐日记》,取释家“见道忘山”之意。日记始于1893年,大部分毁于兵燹,今仅存1893、1894、1897、1898、1901—1903、1906—1908诸年的日记。
第一遍专为寻找有关梁启超的材料。看到孙宝瑄记章太炎等“戏以《石头》人名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在田,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等等,觉得妙不可言。他又称道梁启超的“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无论其所言为精为粗,为正为偏,而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因此为“奇人”。梁启超的影响既已遍及亚洲,则其对于国人的感召力自不待言。
第二遍是看其新学长进情况。孙宝瑄1901—1902年所读所购新书中,居然有不少诸如《男女交合新论》《普通妊娠法》《男女造化新论》《生殖器》《男女交合无上之快乐》一类性学、生理学书籍,足见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观念的开放。他对读旧书与读新书亦有妙说:
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
此类精妙之论尚多,时时给人以愉悦。日记中常自夸善作论,“以义理雄”,信乎不假。
第三遍读《忘山庐日记》,是因为编“新小说”研究资料,从中查找有关材料。孙宝瑄果然与旧派文人不同,也喜读小说。旧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新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新中国未来记》,以及翻译小说如林译小说多种,都在阅读之列。见识亦超卓,如说:
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有非我国所能及者。故观我国小说,不过排遣而已;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
读小说也是求学之一道,这是当时的典型说法。第四遍是观其作日记的态度。《忘山庐日记》绝非随意之作,孙宝瑄不仅逐日记述,因病遗漏数日,愈后亦必补作,而且记日记本身已成为其整个生活的中心。客来,可以展读日记;访友,可以携日记以为谈资;闲来无事,可以“观旧时日记,饶有味”;甚至读书,也是为日记准备材料:“余迩来览书,几若无可寓目者,然不阅书则日记枯索,几不能下笔,亦一苦事。”孙宝瑄很以“余之日记,可谓能耐久”自豪,从甲午年决意“每日所看之书、所历之境,苟有心得,志之勿忘”,此后日记即不复间断。没有如此执着、认真的写作态度,是不可能坚持这样长久,其日记也不可能这样耐读的。
虽然翻过几次,但我其实并没有从头至尾、一字不遗地读过《忘山庐日记》。留下未读的部分,以后若有兴致,还可以换个角度再读。
从兴趣出发读日记,也未尝无益于学问。编“新小说”资料时,见到一本《松岗小史》,作者署名“觉奴”,不知何许人也。吴虞为之作序,也未明言。阅《吴虞日记》,1915年八月初六日记有“午饭后作富顺刘长述《松岗小史序》”,即获知“觉奴”的真姓名。至于日记中记吴虞与其父结仇涉讼及买妾事,则是这位反礼教的激进分子思想矛盾的有力佐证。《藏晖室日记》记胡适因醉酒殴伤巡捕被拘留,也是胡适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插曲。《留学日记》记湖南省高等及师范学堂官费留日学生行经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要学生们行跪拜礼,遭到拒绝,便恼羞成怒,不放行;学生们亦群情激愤,“谓宁甘撤退,断不以人格牺牲”。后经调解,张之洞同意“不拘定行跪拜礼”,以学生们进见时或鞠躬、或长揖、或立正了之。张之洞号称开明、爱才,尚且如此专横,其他顽固官僚更可想而知。此一学潮在中国留学史上颇著名,正是靠亲历者黄尊三的日记,才保存下这段详情。

张之洞
此数人中,记日记为自策自励的有黄尊三,其《三十年日记·自序》说得明白: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记之作,意在斯乎?
孙宝瑄日记之作,也是为验证学识之进步。胡适《藏晖室日记》则有寻求精神寄托之意,其“自志”云:
今岁云莫矣,天涯游子,寒窗旅思,凡百苦虑,无可告语,则不能不理吾旧业,而吾第五册之日记,遂以十二月十四日开幕矣。
《吴虞日记》更是纯属“个人秘密”,从内容可以考知,他的日记连妻子也不得观。《双涛阁日记》恰好相反,是边写边发表于《国风报》,显然不专为自己而作。不过,由于梁启超习惯于公开袒露自己的思想意识及情感活动,其日记并不因公之报刊而有所隐匿。这在一般人就很难做到。
我之所以对这几种日记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作者的不做作,不装假,能见出其人的真性情。当然,并非所有人的真性情都值得赞赏,起码黄尊三的注重道德修养,有一年的日记几乎全是每天“译格言”二三条,又自撰“励志浅语”二百则,就让我看了觉得不舒服。于是,只好跳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