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淘来的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一个此前教科书中没有的世界 傅国涌:十七岁北行淘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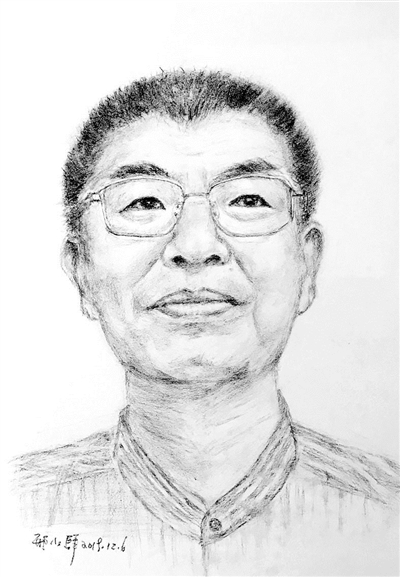
傅国涌:历史学者,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发现廿八都》等。(邢小群绘)
◎第一站:杭州
我不知道城站离西湖多远,却被书店所吸引,一头扎了进去
1984年8月4日,大晴天,我起了个大早,大约天还没怎么亮就动身了,戴了顶既可遮阳又可挡雨的小斗笠,背了一个包,翻过谢公岭,前往雁荡车站。说是车站,其实,就是马路边有几间小平房,卖车票的姑娘陈芳是我二姐的小姐妹,我每次到车站,透过那扇卖票的小方窗,总看见桌上那本厚厚的《创作技巧谈》,那五个字一看就是鲁迅的笔迹,大约是集的字,白色花边的淡蓝色封面看得我心动。终于有一天我央求二姐去向陈芳要,没想到还真的要来了。从此,这本书成了我的,一直跟我到如今。这是1981年杭州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和浙江日报社资料组合编的,收入了83篇文章,除了老舍、冰心、叶圣陶、茅盾、曹禺这些人,许多作者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从这里看到的,比如研究古典文学的傅庚生、研究《红楼梦》的蒋和森、诗评家李元洛、研究古代文论和美学的吴调公等。
此前,我已买好前往杭州的车票,目的地是北京,要到杭州去乘火车。家乡跟杭州之间唯一的班车就是雁荡出发的,大荆镇上没有。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北行的旅途。17岁的我除了去过县城和台州的路桥,还没有见过城市的样子。从看连环画起,版权页上的地址:杭州武林路196号,常常引我远想,杭州离雁荡几百公里,那时的公路还是砂石路,要翻越好几座大山,盘山公路令人生畏。车到杭州武林门已是傍晚,足足开了一整天。
西湖的民间故事从小看连环画就看得滚瓜烂熟,我手里还有一本《西湖人物》,从钱缪、赵构、岳飞、贾似道、于谦、张苍水、康熙、乾隆、秋瑾到白居易、范仲淹、苏东坡、杨孟瑛、阮元、林启,从葛洪、林和靖、毕昇、陆游、关汉卿、张岱、徐文长到袁枚、陈端生、李渔、龚自珍、胡雪岩、俞曲园、章太炎、李叔同、苏曼殊,讲述了数十个与西湖有关的人物故事,我对其中许多人发生兴趣,最初就来自这本书给我的影响。
车过钱塘江大桥,杭州到了,有一段从西湖边开过,车窗外就是我纸上熟悉、念叨了十来年的西湖。下了车,搭上公交车,前往城站火车站,买不到次日开往北京的火车票,找了个廉价的国营旅馆住下,没有空调,只有吊扇,大房间里满是上下铺的床,挂着蚊帐,我睡的是上铺,就像我曾住过的学生宿舍。天太热了,我不知道城站离西湖多远,却被书店所吸引,一头扎了进去。那时的书店开架的不多,挑书很是费劲。
我的心思全在书上面,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等,在城站一带的书店我淘到了阿英的《小说四谈》《明清小说序跋》《〈歧路灯〉论丛》等。8月5日凌晨,我在睡意蒙眬中去车站售票厅排队,离窗口开门售票还早着,所以买到了119次杭州到北京的票,然后一整天就在书店淘书,连西湖都放弃了。
◎第二站:天津
谢绝去天津著名的水上公园,整天只在各家书店转
8月6日早晨5:28 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从杭州缓缓开出,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远行,充满了好奇,一天一夜很快过去,没有觉得太累,也忘了在硬座上是否睡着了。一路上列车员都会拿着大水壶给我们加水。我忘了自己带的是怎样的茶缸,大概一路上要么看窗外的田野、山川,要么埋头于杭州淘来的书中。
次日早晨6:30就到了北京站,公交车到中关村,辗转找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然后找到我舅舅家,他们一家四口去北戴河度假了,那时他们的住房是与邻居合用厨房和卫生间的,邻居知我远道而来,做了蛋炒饭招待我。然后我又回到北京火车站,乘坐中午十二点的大巴前往天津,我二姐当时在天津做生意。下午三点才抵达,辗转找到我二姐,在天津住了一个星期,换了三个旅馆,这些旅馆的名字我记在一张纸片上,竟然还在,“新时代”“西南楼”“永安街”,吃饭我记得二姐经常带我去“清真”吃面食。到8月15日离开,那一星期,二姐的朋友说带我去天津最著名的水上公园玩,我也谢绝了,我哪儿都没去,整天只是在各家书店转,在开架的外文书店买到了查良铮译的《雪莱抒情诗选》、杨德豫译的《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雪莱、拜伦的诗我是1983年下半年从《名作欣赏》上最初接触到的,课本中从未出现过他们的作品。雪莱的《自由颂》《西风颂》《给云雀》《云》等都是我喜爱的,尤其是那首长长的《含羞草》令我念念不忘——
……
等冬天过去了,春天又回来,
含羞草已成了无叶的残骸;
可是毒菌、羊蹄草、毒麦,曼陀罗,
却从它们的墓墟里死而复活。
……
因为爱、美和喜悦不会死去,
也不会变化;它们的威力
能超越我们的感官:而这感官
经不住光亮,因为本身太幽暗。
英国诗人雪莱1820年写下这首诗,距离我读到已过去了一百六十多年,含羞草仿佛还活着,“因为爱、美和喜悦不会死去”。
另一位英国诗人拜伦为希腊的独立而光荣地死去,他的《哀希腊》就是那年八月在天津第一次读到的——
希腊群岛呵,希腊群岛!
……
长夏的阳光还灿烂如金——
除了太阳,一切都沉沦!
三十多年后,十二个童子跟我到希腊游学,他们在爱琴海的碧波中朗诵这首诗时,我想到的却是1984年的夏天,我与拜伦的相遇,与《哀希腊》的相遇。
还有一本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我曾将她的诗句抄在了日记本的扉页。这本诗集后来送给了一个朋友。
北大教授吴小如的《古典诗文述略》是在天津的新华书店买的,这是本薄薄的小册子,是当年出的新书,0.54元,包括《古诗述略》《唐诗述略》《古典散文述略》三篇文章。他在讲初唐诗时,列举虞世南的一首《咏萤》:
的历流光小,飘飖弱翅轻。
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
在技巧上不如杜甫的“暗飞萤自照”,在思想内涵和艺术造诣上更不及李商隐的“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他说杜诗总有点顾影自怜的意味,而李诗更显得衰飒暗淡,不像虞世南的诗中所写纵然“光小”“翅轻”,却有与无边暗夜较量一下的勇气。他分析,大乱之后,即使是小人物也有了“暗中明”的机会。在我读来就觉得十分新鲜,从此记住了吴小如这个名字。
在天津还买到一册《与青年朋友谈治学》,这是“文史知识丛书”的一种,将《文史知识》上学者们谈治学的文字收集在一起,此前我曾在刊物上读到过几篇,也见到过此书的预告。书中有夏承焘、朱东润、郑天挺、余冠英、庞朴、何兹全、林庚、周一良等人的文章,在未来的岁月中,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还将不断地和他们相遇。正是从夏承焘先生《我的学词经历》开始,我陆续读了他的著作,乃至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埋下了我将来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中写下《夏承焘:“花事今年看斩新”》最初的伏笔。第一本夏承焘的书即是在天津外文书店买的《夏承焘词集》,其中就有他关于雁荡的词,他是温州人,抗战时期又曾在雁荡执教,“叩门一盏雁山茶”“龙湫雁荡家山好”,他也将雁荡视为家山。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本小册子: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增订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四次印刷的。这本一百多页,都是人名、书名的小书,却提纲挈领,给了我走进中国文化之门的简易门径。从工具书与语言文字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历史学与地理学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哲学与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到医学、科学与技术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中国文化基础书目……此书上起《诗经》《尚书》《论语》《易经》,下迄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穆、张东荪、梁漱溟、陈寅恪、潘光旦、冯友兰、陶行知等20世纪人。虽然简要,却非常清晰,循着他提供的线索,大致就可以明了该读什么书。此书虽小,在我早年的读书生涯中却是本宝书、大书,常常翻阅的书。正是此书的指引,我从那时起,陆续开始读梁漱溟、陈寅恪、张东荪、张君劢、潘光旦、钱穆、贺麟、李泽厚等人的著作,师复等无政府主义派、曾琦他们的国家主义派、战国策派……最早的印象就来自这本小册子。
天津,加上杭州买的书,我的行李明显有重量了。
◎第三站:北京
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故宫、颐和园,而是书店那么多
8月15日,我和二姐乘坐凌晨3:15的夜车前往北京,到达北京站才5:30,我们先去了天安门广场,到了故宫开门,才买票进去,宋元山水真迹迄今还有一些朦胧的印象,尤其是黄庭坚的一幅字当时给过我力透纸背的真切感受。我在地安门拍过此行唯一的一张照片,早已丢失,景山公园没有进去,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景山上的建筑。中午12点到了中关村舅舅家,我住了下来,二姐回天津去了。舅舅家在楼上另有一个单间,是给我住的地方。
窗外黄土飞扬,白杨树是我在雁荡山中见不到的。每天早晨公交车的声音、推土机之类机械的作业声会把我叫醒,当然还有鸟声。北京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广场,而是路边的白杨树、白桦树、槐树,公交车售票员报站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书店那么多,还能淘到很便宜的好书。
直到8月29日离京回家,我在北京住了两个星期,除了22日去动物园、23日去颐和园逛了一天,期间多数的日子都是一个人去书店淘书。去得最多的是白石桥的一家旧书店,我已记不起书店的名称了,常常从中关村乘公交车到那儿,一淘就是大半天。
我淘到了一些学术性或知识性的期刊,《史学情报》《文史知识》《文学知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除了《文史知识》,其他都是初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总第十辑),其中有顾颉刚论《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融合的论文,有孟森的遗稿《海宁陈家》,有汤志钧的《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还有赵俪生、蒋天枢、钟敬文等学者的论文,这些名字都是我初次遇到的,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会一次次遇到他们。我之所以注意到孟森的清史研究著作,就是起源于白石桥旧书店的偶遇,这篇《海宁陈家》与不久后读到金庸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交错互动,一虚一实,在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穿梭,给了我一种奇异的阅读体验。以后又读了孟森在清末的文章著述,了解他由立宪运动的积极推手到学者的转型,对其人其事其书无不感到亲切。
我读到的这些书、文章、诗篇都可以说是桥,是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产生的,让苦于跋涉的我在文明的路上可以前行。
海淀黄庄一带的书店,我几乎都跑遍了。有一本棕色封面的精装本《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大概就是在那里找到的,作者多为港台和海外的学者,余英时、唐德刚、周策纵这些名字都是首次遇到,他们研究《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的论文,带给我一种新鲜感,与我此前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读到的论文很不一样。从那时开始,这些人的著作将渐渐进入我的世界,跟随我一生。
我还买到了一本萧艾的《王国维评传》,1983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我与王国维最初的相遇,知道了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知道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词以境界为最上”,知道了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境界,知道了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和他在五十之年的自沉之举。这本小册子也许不是精深之作,却成为我走向王国维世界的入门书,前面插图中有一幅王国维海宁盐官故居的照片,海宁王国维从此在我的生命中就挥之不去了。
也正是循着王国维,我在一二年后找到了叔本华、尼采、康德,开始哲学的阅读,无疑是读王国维的结果。我将他的诗句抄在日记本上,常常念兹在兹:“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不久前,我又一次来到盐官,在他度过了少年时光的旧屋,我重温的却是17岁时与他初遇的时光。
柴德赓的《史学丛考》是1982年中华书局出的,柴是史学家陈垣的得意弟子,书中最后一篇即是《我的老师——陈垣先生》。但我那时之所以会买这书,很可能是因为其中的一篇《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初稿),以白居易有关的诗文与新旧唐书、《唐会要》、地方志等史料相互印证苏州唐时的繁荣。他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所言:“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与他的诗“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可以相呼应。至于这首《登阊门闲望》中的“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则可以和《正月三日闲行》中的“红栏三百九十桥”“杨柳交加万万条”相呼应,苏州的繁荣在这些诗句中几乎呼之欲出。我那时正热衷于雁荡山和温州地方史的研究,这篇文章启发我想写一篇《由叶适、王十朋、“永嘉四灵”的诗文论证南宋温州的繁荣》,当然最终没有写出来。
由顾颉刚、孟森、柴德赓他们的著述让我最初窥见了史学的缝隙,我舅舅建议我找到断代史的方向,如同吴晗专心于明史那样,但我当时没有放在心上。我对诗歌、历史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兴趣都很浓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可以说,还在阅读的早期摸索阶段。
从24日起,我连续四天都去排队买火车票,前三次都去晚了,没买到,27日晚上吃完晚饭就出发,带上凳子去通宵排队。早晨一开门,我在前面几个,不仅买了自己的票,还为几个南下杭州念大学的女生买了票。8月29日19:10的火车,表弟用自行车将几大袋子的书帮我送到木樨地地铁口。我扛着沉重的行李进站、出站,大汗淋漓,到了杭州站又辗转坐汽车回家。这一路累坏了我,但淘来的这些书将为我打开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一个此前教科书中没有的世界。累,也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