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卜荪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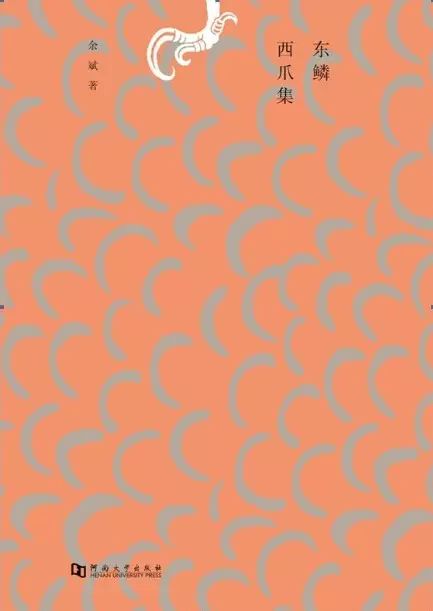
《东鳞西爪集》,余斌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一
所谓“隔行如隔山”,是说不是本行的人,便不知那行业里的门道。照“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说法,“门道”是内里的东西,其实对一些小众的圈子,外行不要说是“门道”,连“热闹”也没得看。比如,在某个人群中如雷贯耳的名字,圈外人可能一无所知。燕卜荪可能算不得神一级的人物,但在西南联大无人不知,亦不乏崇拜者,对现代诗及新批评理论感兴趣的人提起来更是肃然起敬,但对圈外人而言,若是说到他,第一反应也许是:燕卜荪?什么人?
有一种回答最省事,不过等于什么也没说——就是WILLIAMEMPSON。燕卜荪是中文的音译,说他是英国著名的文论家,“新批评”的重要人物,也还是模糊。但是说他在西南联大、北大教过书,是来华任教的最大牌的洋教授之一,感觉上离我们就近得多了。民国年间高校里洋人不少,像常出现在回忆录中的温德、马约翰等人,仿佛已是学校的一部分了。但多为寻常之辈,与今天的情形一样,倘能在本国谋得教职,大概不会千里迢迢跑到对他们而言仿佛尚在中世纪的中国来。赛珍珠当年在南京接待朋友,还因没有电灯而微感不安,生活条件差距之大,也就可以想见一二。
燕卜荪的老师瑞恰兹来华时已是名教授,当然是大牌,但他在清华待的时间不长,抗战暴发他就回国了,燕卜荪两度来中国任教,1937至1939在西南联大,1947年起在北大,直到1952年,已是清理门户的形势了,方才回到英国。
燕卜荪的名字我是读本科时就知道的,但也就是个名字而已。直到好多年后,本专业有个博士生以燕卜荪做博士论文,因要参加答辩,才把他的名著《含混七型》找来恶补。一下也没全读懂,只觉胜意纷陈,辨析精微。让人惊讶的是,这书是他学生时代写的,算来也就二十几岁。美国文学批评家兰色姆在学界要算大牛了,他曾有言,“没有一个批评家读过此书后还能依然故我”。还有一种说法更夸张,称西方的文学批评应以燕卜荪划界,分为“前燕卜荪时期”与“后燕卜荪时期”。假如还想给他添几分传奇色彩的话,就当提到他在剑桥时,数学成绩曾名列第一,他之转向文学令数学教授大为惋惜。
他来中国任教时三十几岁,还不像后来那么有名,不过就凭《含混七型》,说他是大牌当不为过。只是有文章说他放弃剑桥讲席不远万里来中国云云,不免有些想当然。事实上他最初到来到东方,是因为他在英国混不下去了:剑桥当局因校工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取消了他继续深造的奖学金(系因导师瑞恰慈推荐)。虽说多年以后,剑桥大学因他的成就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英国女王还封了他爵士头衔。
二
事过境迁,避孕套在燕卜荪获荣誉博士学位的七十年代早已不是问题,但当时很严重。燕卜荪遂听了瑞恰慈之劝,远赴东方。他在东方的第一站是日本,1931至1934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教书。聘期结束回到英国,过了几年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倘说到日本有避风头之意,那1937年来中国教书就应看作是他主动的选择了。事实上回国的第二年(1935)他就有了念头,这一年吴宓访牛津时,他即登门拜访,表露往中国教书之意。1937年他得到北大的聘书,然他来到中国时,北平已被日本人占领,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为西南联大,故接下去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了。
日本人来势凶猛,呈鲸吞之势,中国的大学实在是前途未卜,在华的洋教授选择离开战乱之地,也属人之常情。燕卜荪的老师瑞恰慈其时正在清华,就去了美国,并且劝他也走。他却留了下来,据说对老师的离去还颇有微词。燕卜荪不是个唱高调的人,“和中人民站在一起”之类的话是不会有的,对他而言,作为一个绅士,那是责任和义务,假如还需另外的理由,他宁可说他乐于和联大师生在一起。他的确说过,联大师生的学术素养是他不舍中国的重要原因。他的许多同事都是中国学界的一流人物,是那些在教师食堂同桌吃饭的同事的高素质让他留下,而联大的学生他认为更在欧美学生之上,好学生放在欧美大学里就是最好的。
有这样的学术环境,能够得天才英才而育之,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是可以忍受的了,——尽管他后来将在中国的两年概括为“原始生活,跳蚤和炸弹”。他经历了联大最艰苦的时期,在湖南南岳山村的临时大学和迁至昆明的最初阶段。这位洋教授并未享受特殊待遇,在南岳时他和金岳霖同住一室,也和叶公超做过室友,初到昆明时宿舍不够分,他和十多人同住一间,床铺就是一块黑板。
然而就像他的同事一样,这段艰苦的岁月倒是他创造力旺盛的时期。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都叙及联大人在艰难环境中卓绝的工作,若将燕卜荪视为联大人的话,就该补上他此时的成果。在南岳山村的茅屋里,冯友兰完成了他的《新理学》、金岳霖写出了《原道》,汤用彤写出了《中国佛教史》。燕卜荪作为诗人,写下了《南岳之秋》,作为学者,开始了据称为他“最伟大著作”的《复杂词的结构》的撰写,此外他的哲理小说《王家畜牲》也是在此时完成。
联大两年,加上后来在北大的五年,注定是燕卜荪难忘的岁月,他的权威传记,副题居然是“在中国人中间”,——传记的作者当然也是体他之意,虽然相对于他的一生,他在中国的时日只是一个小段落。
三
虽然著术颇丰,身在学校,教书育人才是燕卜荪的正业。他在中国的影响,最直接者,也是通过他的学生体现出来。他在联大教英语,同时教英国文学的专门课程,特别是英诗,日后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还有英语教学、研究方面的顶尖人物,举凡穆旦、袁可嘉、王佐良、许国璋、杨周翰等,皆曾从他受教。说到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传播,燕卜荪尤其值得一书,倒不是因其他洋教授不大讲这个,而在于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奥登等予穆旦们深刻影响的诗人与他都是哥们关系,这令他的课与学院派教授颇为不同,而有现身说法的意味,现代主义诗歌由此生动起来,不再是一个传说。
学生记忆中的“燕师”天份极高,记忆力极强。广为传布的一个佳话是,临时大学在南岳时连基本的教学条件也不具备,学生全无教材可用,燕卜荪凭着记忆,将全本《奥赛罗》(一说《哈姆雷特》)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供授课之用。燕卜荪显然对神话不感兴趣,他后来自毁形象说,那是误传,事实是他手边恰有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而能够背诵古典名篇也算不了什么,他的同事哪个不能大段大段背诵中国古诗文?然而学生心目中的“燕师”简直神了,虽然他似乎有几分羞涩,上课居然不大敢看人。平日他则又有几分放诞的味道,主要见于饮酒,不是斯斯文文的饮,是经常喝醉,有次醉后将眼镜放鞋里,醒来将一镜片踩得稀烂,而他便戴着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去上课。酒后高谈阔论,与学生衡艺论文,也是常事。这些地方,可说是他几年前在伦敦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余绪。
但这一点不妨碍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在西南联大的课是大热门,据说他与闻一多、冯友兰、吴宓的课,每每上演课前学生争抢座位的趣剧。至于是不是因为讲课生动,却不好说。1947年后他在北大任教,一位1949年后听过他的学生回忆,他讲课的方式是把讲的内容全写在黑板上,上课时拿着一整盒粉笔进来,而后就是快速的板书,写完一段稍做停留,擦去后接着往下写,令学生抄之不暇。有人希望他多些口头讲授,他称自己说话太快。据说这种授课方式在日本教书时即已形成,因日本学生听力跟不上。果真如此,他在联大授课,当亦相去不远。
形成对照的是,联大时他的教室人满为患,1950至1951年他在北大讲授英国现代诗歌,只有三人选他的课,难懂是一因,有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却不好说。而1952年他就回国了,其时中国高等学校的所谓“院系调整”,正在轰轰烈列地展开。
本文选自《东鳞西爪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