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作者阿特伍德推出续集《证言》 就像她爱的莎士比亚悲喜剧,荒野的孩子终将找回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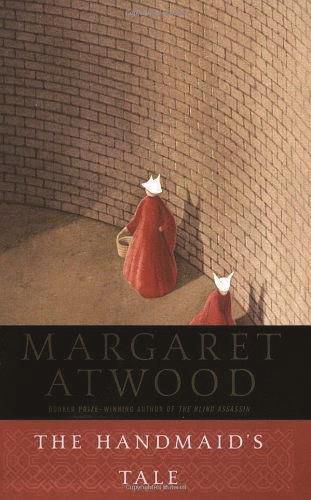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书封。 (出版方供图)
《使女的故事》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半个月前度过了她的80岁生日。在世俗人们觉得“只能颐养天年”的年纪,这位加拿大老太太给全世界的女人——包括女作家——打了一针强心针:如果你有热爱的事业,不要过早地放弃,坚持做下去,你到80岁仍然有可能制造出撬动地球的爆款。
蜂拥而至的读者,见证阿特伍德“出圈”记
今年9月中旬,《使女的故事》小说续集《证言》在伦敦上市前夜,书迷们和同名剧集的剧迷们蜂拥到皮卡迪利街的水石书店,他们穿戴着故事里使女们的红袍白帽,等待零点钟声敲响时由阿特伍德亲自卖出第一本《证言》。满头灰白卷发的阿特伍德站在人群中,如同唤起午夜魔法的巫师。伦敦的书店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盛景,上一次能达到同等轰动规模的新书午夜发售,还是《哈利波特》系列的大结局。
时间倒推到1985年,《使女的故事》小说出版时,并没有在书市制造大的反响,作家本人回忆:“只在出版人的小圈子里小小庆祝了一下。”“小小庆祝”是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布克奖提名,可惜最后未能获奖。此后十年里,阿特伍德又因《猫眼》和《别名格蕾丝》两获布克奖提名,但她最终拿到布克奖,要到2000年的《盲刺客》。直到当时,阿特伍德的声誉仍局限于小范围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爱好者中。2000年以后,阿特伍德因《珀涅罗珀记》和《女巫的子孙》两次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故事新编地重述了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到了2017年前后,她决定续写当年的《使女的故事》,也就是在这一年,根据她的《使女的故事》和《别名格蕾丝》改编的两部剧集先后上映,一夜之间,原作者阿特伍德真正意义上地“出圈”了。
苦难降临时,女性和孩子总是被迫承受更多
阿特伍德迟来的声誉未必是影视改编推波助澜的结果,至少不全是。英国科幻作家尼尔盖曼在读过《证言》之后的这段感言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在我读《使女的故事》时,曾以为她过分悲观。时隔30年,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过分天真。面对现实,我们中的大多数总是不够清醒,不够警惕。”阿特伍德本人接受《卫报》采访时,直接说:“过去的30年里,我们本来有希望远离‘基列国’,但现在眼看一步步地回去了。”
1984年,阿特伍德在柏林开始构思《使女的故事》,那是一个被认为“乐观的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在全世界展开,几代人的持续抗争,换来社会结构的一点改善,“第二性”逐渐发出被压抑的声音,争取着被父权剥夺的权利。在那样的大环境里,阿特伍德敏锐地察觉到始终存在强悍顽固的保守力量,时刻准备着把女性的身体、声音和自我意识,一样样地重新封锁到黑匣子里。为此,她写下了《使女的故事》——如果在北美,存在着一个威权运作的政治体,权力对“人”的征用,最显见也最终极的表现,是对女性的物化和工具化。
《使女的故事》上承《可以吃的女人》,后接《别名格蕾丝》和《盲刺客》,阿特伍德在写作中坚持一条明确的信念:为什么要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为什么女性处在风暴的中心?因为苦难降临时,作为弱势者的女性和孩子,总是被迫承受了更多。
严酷和希望、毁灭和新生的复调贯穿全书
阿特伍德拒绝认为“基列国”是想象的产物,她说:“即便我创造一个想象的花园,那里面一草一木连带一只乌龟都是真的。《使女》故事里的所有细节,来自清教徒时期的北美,我是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重新排列组合了。”
《使女》聚焦的是在残酷的、非人的环境里,个体怎样活下去。“活着”可能是奥弗瑞德那样向善的、向着明亮方向的挣扎,也可能是莉迪亚嬷嬷那样,来自弱势一方却成为强权者的帮凶。“生存”的命题延续在《证言》中,在这个故事里,莉迪亚嬷嬷的声音清晰起来。小说标题“证言”,其实也是莉迪亚嬷嬷的遗嘱,在这个多声部的文本里,莉迪亚的声音指向过去,她的声音成为基列国土崩瓦解时凄厉的背景音。阿特伍德认为,莉迪亚嬷嬷的意义在于她提供了内部洞察的视角,她把这个角色定义为“女版的克伦威尔”“一个被权力吞噬的人”。莉迪亚是一个被厌弃的反面角色,一个同流合污者,但也恰恰在她身上,阿特伍德把普通人从受难者走向加害者的过程透明化了。
阿特伍德的写作,既是出于对现实的洞察,所以她从莉迪亚嬷嬷的视角呈现了系统的崩溃;但同时,恰似奥弗瑞德留下的声音,“叙述”也可以是一种寄托着希望的行动。于是,在《证言》里,少女阿涅斯和黛西的声音是和莉迪亚平行展开的声部,阿涅斯成长于瓦解前的基列国,黛西是在襁褓中随母亲逃到了加拿大。严酷和希望、毁灭和新生的复调贯穿了整本小说,男权和女性的对峙逐渐退隐到背景中,前景中清晰的是少女的出走和回归,很多时候,这个故事就像阿特伍德钟爱的莎士比亚晚期悲喜剧,它几乎是带着童话色彩的——荒野的孩子终将找回家园。
也许是年迈让作家变成了布道者,但也正像她形容的,站在迷宫路口的人类仍然是有选择权的,也许打开对的那扇门,门后就有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