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乾先生肩头的鸽子

年轻时的王道乾先生
我和王道乾先生是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认识的。1979年4月我进入刚刚恢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还在筹备之中,几个月后姜彬所长、王道乾副所长上任,文学所正式成立。这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先生”、“女士”、“小姐”等称呼还没流行。文学所里对年长的同志,都习惯在姓氏前加“老”称呼,对王道乾先生大家都称呼“老王”,对姜彬所长也称呼“老姜”,人前人后莫不如此,他们都不以为忤。直到现在,文学所一些老同事谈到他们,仍称“老姜”、“老王”。我在这里称王道乾先生,是顺应现在的习惯。
第一次见到王先生,就被他的外貌所吸引:五十多岁,中等身材,身板硬朗,方正脸型,茂密且根根直立的头发剪成像鲁迅那样的样式,浓眉大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鼻子比一般人高些,下巴微微凸前,乍看面相很像古希腊哲人。我心里暗想,难怪他是法国文学专家,说他就是法国人,也有几分相像啊。王先生衣着朴素得体,常年穿中山装,偶尔也穿中式上装,待人总是彬彬有礼,平时话不多,说起话来语气平和,不慌不忙,而文静中又带几分严肃。他不是那种乍接触就让人想亲近的人,但同王先生交往久了,会渐渐感觉到他待人的真诚、善良和热情。
文学所成立初期,社科院分配的办公室只有三间:三楼一小间是所长办公室,一楼有一大间,一百多平方米,供办公室、资料室、外国文学研究室和古代文学研究室使用;三楼屋顶平台上的简易房一间,将近五六十平方米。由理论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当代文学研究室合用。由于王先生兼任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所以他在一楼大房间的外国文学研究室区也安置了一张办公桌,待在这里的时间比在所长办公室要多。
那时,社科院特别强调学术研究队伍的“老中青三结合”,也强调老年学者对中青年学术后辈的“传帮带”,而青年科研人员也大多虚心向中老年学者请教。我向王先生求教可以说是随时随地,走廊里遇到可以,院门口见到可以,然而最多的是在一楼他的办公桌旁。文学所的科研人员每周二、五两天必须到所,或研究室活动或全所集会。遇到这两天,午饭后科研人员陆续离去,我就到一楼的外国文学室向王先生求教。王先生从不厌烦,即使我的问题太幼稚肤浅,他也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并且针对我的欠缺指导弥补。这样的求、教慢慢多起来,我们的关系也由生疏变得比较熟悉,这当然承蒙王先生不弃。王先生吸烟,那段时间好像经常吸烟斗。讨教时,我隔着办公桌坐在他的对面,他边吸烟斗边说话,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夹握住烟斗,将烟斗的吸嘴部轻轻放进嘴唇的左角,慢慢吸上一口,烟斗里的烟丝随之闪亮微微的红光,蜜糖般的甜香飘溢四散,他缓缓吐出淡淡的青白色烟雾,在两人间形成一层轻薄的烟帘,透过它我看到慈祥的面容和深邃的目光,听到轻柔徐缓又清晰中肯的言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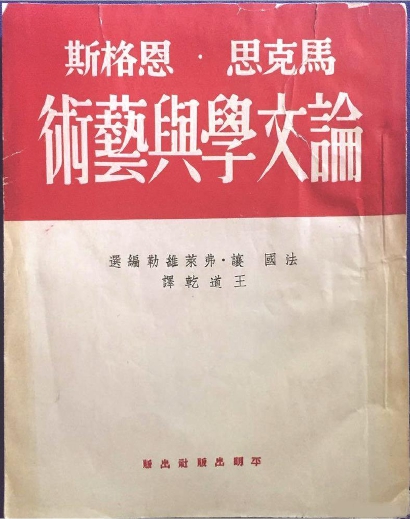
让·弗莱维勒选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平明出版社,1953) 王道乾译
我们谈过学术研究的兴趣,王先生说,治学离不开兴趣,但不能当成游戏,要有敬畏心、责任感。我们也谈过研究的视野、角度等问题,王先生说,学术研究也没什么神秘的或者规定的视野、角度,就好像切蛋糕,你怎么切都行,但你要讲清为什么这样切、这样切你发现什么、有什么好处等等。有一次我说起所里一位中年学者的词汇量特别多,文章写得华丽,要向他学习,王先生说质朴也是风格,他喜欢质朴的文字。王先生督促我学习逻辑,说掌握逻辑思维方法,是研究学术的基本要素之一;还说,在西方中学就有逻辑课程,而中国要到大学才讲授逻辑,这是不应该的。我问他中国哪位学者讲逻辑最好,我从哪本逻辑著作读起。王先生说,金岳霖研究逻辑是好的,建议我先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的《形式逻辑》。在这次谈话之后一星期再见到王先生时,我说没找到这部书,王先生听后没说什么。几天后,王先生找到我,递给我罗森塔尔的《形式逻辑》,说,“这是我自己的,你看时要当心,看完还给我”。我当天就开始阅读此书,越读越有兴趣,读了一遍又读一遍,然后还给王先生,还说了一些自己的阅读喜悦。在这本书里,有不少王先生的眉批,成为我学习逻辑的指引或参考。后来,我又结合阅读《资本论》读了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等。王先生的这些教导让我受益终身。
王先生在所里分管青年科研人员培养工作,非仅对我,对文学所愿意向他求教的其他青年科研人员,他都不吝赐教。古典文学室有位青年科研人员,经常在中午找王先生“讨教”,王先生常常因此不能按时进餐,却从不拒绝,待这位同志“讨教”结束再去食堂。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初进文学所,王先生写信给她,提醒她尽快适应生活环境、工作方式的变化,明确新的“社会责任已经落在肩上”,希望她“首先集中地抓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不是做到略知一二,而是从体系上力争掌握起来”,还叮嘱她要有目的、有计划、带分析地广泛阅读中外文论和作品,希望她写读书笔记,重视学习和研究方法,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敏锐地抓住”,还要“强制自己的思维活动按照严格的逻辑去进行。必须养成良好的健全的思维习惯”等等。当年参与文学所办公会议的一位同志告诉我,王先生对所里每位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规划逐一审阅,然后分别谈话,给以指导。我也听王先生说过,文学所每位青年科研人员上报的学术成果,他都找来看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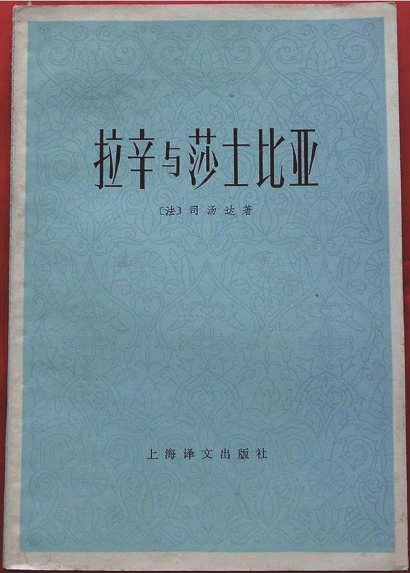
司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亚》(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王道乾译
王先生十分重视学识与学风建设。在文学所学术会议上或同我的交谈中,强调做学问要有深厚扎实的基础,要耐得住寂寞,甘于坐冷板凳,不要急于求成;他说学术研究不能赶时髦,不要曲意迎合,随波逐流;他说考据是必要的,是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但不能为考据而考据,不能满足于考据,考据要有史的观念,要为历史研究服务。他劝诫科研人员不要热衷在报刊发表“豆腐干”文章,研究要有长期规划,选择有意义有价值的课题,有阶段性目标;要敢于发表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又要有能够听取不同见解的襟怀气量,等等等等。那时,继恢复稿酬制度之后,全民经商的“下海”大潮正波涛涌动,这些治学的老生常谈,对于文学所优良学风的建立和青年科研人员的健康成长,都是矫枉扶正的金玉良言。
在我心目中,王先生是学者,是老师,也是父辈。因此,我们的交谈也并非总限于学术工作。我也向王先生“诉过苦”。1980年代初期,社科院恢复评定职称,规定同学历挂钩,“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律视为大专学历,实习研究员任职五年方得申请晋升助理研究员;如果是“大专”学历的,不仅每年完成的工作量必须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的一倍,而且五年间必须年年如此。我是“文革”末期上海高校“试点研究生班”毕业的,同样被定为大专学历。我在院内第一批定为实习研究员,每年的工作量达到甚至超过规定的一倍以上,但以后申请晋升职称一样有学历问题的困扰。于是,我想暂停研究工作,报考高校研究生。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王先生。他对我说:这样的规定的确不够公平,但不公平的事哪里都有,哪里都一样;做学问,归根结底还是看实际能力和成果;你的那篇讲“孤岛”时期上海电影情况的文章,就有硕士论文的水平;与其花几年时间拿个硕士学位,不如用这些时间好好研究课题,写几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他还说:“文学所是我最后的工作单位,没几年我就要退休了,你就在这里陪陪我吧。”就是王先生的这一席话,让我打消了报考高校研究生的念头,在随后几年里,专心进行创造社研究和“孤岛文学”研究。然而,为了解决学历问题,在王先生去世之后,我还是不得不通过在职学习,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让·弗莱维勒《左拉》(新文艺出版社,1955) 王道乾译
我和王先生经常中午一起在社科院食堂吃饭。那时,社科院食堂的午餐通常有六七种荤菜与素菜,主食有米饭、面条、馒头、包子等,在当时还算丰盛。王先生的午餐有他的“标配”——四个肉包和一碗菜汤,总共贰角钱。如果没买到肉包,就吃面条或馒头。我问他是不是喜欢面食,他说是,也因为肉包进食方便,节省时间。如果午间有事或与他人谈话不能按时进餐,他会递给我食堂的代价券,让我帮他先买好“标配”在食堂等他。有时“标配”已经凉了他才赶来,也毫不讲究地慢慢进餐。吃饭时,往往都不多话,饭后,有时我会陪他在社科院的院子里散散步。这也是我们聊天的时间。这样的散步聊天中,他讲过一些上海学人的趣闻,诸如:钱锺书先生在上海时便有了“两脚书橱”的雅号,他说“这样的学者不能没有,但学者也不能都这样”。
我第一次去王先生的家,是在1980年代中期,他的家在静安寺附近的美丽园,是上海常见的那种里弄楼房。按门牌号码找到房子的后门,门口就停放着王先生经常骑的自行车。这部自行车已经旧了,质量依然不差,好像是英国产的名牌“蓝翎”。从后门进去是几家住户共用的厨房,沿楼梯上到三楼,就是王先生家了。三楼好像有两个房间,近楼梯口的一间朝南,顺走廊向东走几步还有一间。朝南那间有一扇落地钢门,门外是小阳台。门里靠墙放了一张写字台。王先生和我就在写字台旁坐着讲话。我先说在门口看到他的自行车,问他车子是不是一直放在下面,因为当时上海经常有偷窃自行车的事发生。王先生说不是,车子到晚上就由儿子扛上楼,放在走廊里,早晨儿子再扛下去,放在门口。我说院里安排有车接送你们所领导上下班,你为什么还要骑自行车呢。王先生说,一部车要接送几个人,几个人又不住在一处,碰到有什么意外情况,等的时间更多,有次他站在弄口就等了二十多分钟,而自己骑车到社科院用不到一刻钟,“所以我就不乘他们的车了。自己骑车可以掌握时间,也是一种锻炼”。我们谈到阳台上花盆里种植的芦荟、紫罗兰等,王先生说,他种的都是生命力强的植物,不用太操心,它们也不死,“我喜欢绿色,没事就看看它们”。这时,从敞开的阳台门由外飞进屋内两只鸽子,落到楼梯口天花板下的一个凹处,咕咕咕咕不停地叫着。我说我小时候也养过鸽子,问王先生这两只是不是他养的。王先生点点头,说鸽子和他特别亲,他坐在这里看书写作时,鸽子常会停到他的肩上甚至头顶上,他也任由鸽子,而对家里的其他人鸽子却不这样。说这些时,王先生的脸上洋溢着孩子般天真纯净的笑容和得意。

安德烈·斯梯等《烟斗》(新文艺出版社,1957) 王道乾译
再一次到王先生家看望他是在1990年代初,他在三楼东侧的房间接待我。这间有一张大床,靠南窗处放一张写字台,靠西墙有不大且简朴的书橱,大概是王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吧。这次聊天谈到他的翻译。王先生说,一直想翻译几部外国文学作品,可上班时忙于公务,没有时间,退休后可以实现心愿了;有几处刊物等他的译作,他每天伏案苦干,还是难以应付。我问他一天可以翻译多少字,他说“五百,我要求自己坚持每天五百字”。我听了有些惊诧,这么著名的翻译家,对法语那么精通,而且王先生并不热衷社会交际,怎么每天只翻译五百字,也就是写满当时文学所可以领用的一张大稿纸啊。王先生一定看出我的不解,随后说,翻译文学作品不同于翻译法律、经济等著作,那类著作专用名词多,语法、表述有一定规格,熟悉了,翻译得可以快些;文学作品不同,不仅词汇量多,还涉及许多俗语、俚语、民风习俗、特定物品等等,而且每位作家还有自己的特殊表达习惯、修辞手法,要翻译得准确很不容易……。因为亲耳听到王先生的这些话,后来再看到人们称赞王先生译著、译品的文字,我没有感到惊奇。顺便提及,王先生生前遗留的未完成译稿,有些由他的公子王成或学生张小鲁续译问世了。
1980年代中期,社科院院部大楼加高两层工程完工,文学所被分配到新加的四层楼西部,这时全所办公室集中在一起了。所长室在南面,外国文学室和现代文学室在北面且隔壁紧邻。1985年初夏的一天,我在现代室看书,王先生在门口招手示意我到外国文学室。待我进门,王先生就递给我两册书,是梅陆林先生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说他已被批准退休,送这部书作为留念。此前,我向王先生索要过他的译著《莱辛与莎士比亚》。这次是王先生主动给我的,我没想到,接过书看着王先生,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待回过神,我请王先生在此稍等,立即跑到南面的编辑室,找到平时经常为文学所活动拍照的同事,请他为我和王先生拍了一张合影。二十多年后,我和几位同事合作编写《画说上海文学》,其中有对于王先生及其译作的介绍,显示王先生形象的照片,采用的就是这帧合影,当然裁去了我而仅保留了王先生,人像背景就是当年外国文学室的墙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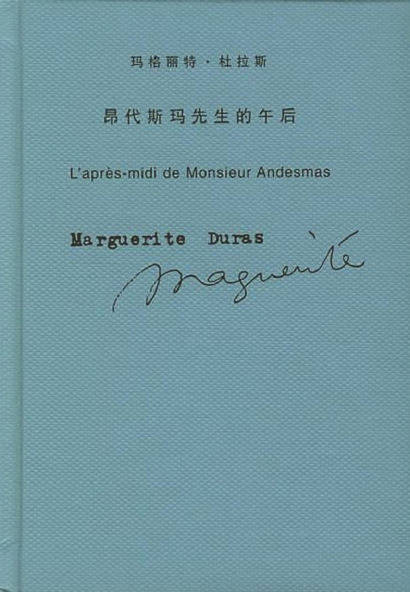
玛格丽特·杜拉斯《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王道乾译
王先生重感情、珍视友谊,提携后辈,也敬待同辈。有一年我到北京参加学术活动,王先生叫我带两条香烟给一位北京学者。到北京联系到那位学者,我到他家里,把用报纸包着的香烟交给他。他立即打开报纸,里面是一条“万宝路”,一条“七星”,而王先生自己平时常吸的是“大前门”。1980年代初期,在陈永志老师提议、规划下,我们合作进行创造社研究,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未出版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专门著述,我们的研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期间,我们写过一篇创造社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曾呈请王先生指教。王先生看后便推荐给当时着手中国文学翻译史工作的戈宝权先生,供他参考,也请他指教。王先生在信中说:
我这两位朋友是专门研究创造社的,收集有丰富的资料,外国文学活动是他们创造社研究的一个方面。我看了他们的文章,觉得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国内似乎还未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你看过文章之后,如以为尚可,是否可就近介绍给译协《中国翻译》杂志考虑发表,以之抛砖引玉,如何?戈宝权先生很快给王先生回信,说文稿看过了,“觉得很有意思,这是研究我国文学翻译家方面的一个新的尝试,而且我想还可做些对文学研究会、未名社、译文社等有关团体和出版社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进一步作相应的研究”;戈先生还指出我们文章中两处错误,并给予具体的改正指示,要我们将修改后的文章连同他和王先生的信“一齐寄给该刊编辑部”。王先生致戈先生的信,在随文稿付邮前,我特意复印留存;戈先生致王先生信,是王先生送给我的,让我“作个纪念”。我们的那篇文章后来在上海一家学报发表。后来我研究抗战时期上海文学时,拜访过好几位当年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的前辈作家如钟望阳、蒯斯曛等,也依赖王先生的介绍。
1991年,我和陈永志先生合作的《创造社记程》出版,我托人代呈王先生一本求正,很快就收到王先生的信。王先生说看到书“自觉欣悦无比”,向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信中还写道:
……你着手这项工作,自始我就知道,我们也曾多次谈及,就像我要写什么一样,我是很关心它的。书的内容结构严整,序列一目了然;特别是你写的后记,谈到著书之成、真诚的学术友谊等等,读来为之心动。我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上的友好情谊一向心向往之,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屡屡受挫,感慨良多,每想到这些,不免为之凄然;
质朴的风格也不妨挥洒驰骋,篇幅似亦可多方展开。……我觉得可说的话还不少,是还有写的余地的。
信中有夸奖也指出我们的欠缺不足,这当中饱含真诚鼓励与鞭策的情谊至今令我感动。
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王先生住进华东医院,先前也听他说过他患过肝炎,这次住院也因为肝病。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的精神很好,只比平时显出些许倦容,他还要我陪他到医院草地散步。散步时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到讲肝病的书,他知道我的妻子在医院工作。我回家找出妻子在军医学校学习时的内科教材,第二天给他送去。这次医院诊断出王先生患了肝癌,并通知了家属,而医生和家属都没告诉他。大概是他猜到些什么,想自己在医书里找到可以对号入座的病症。也是在这次见面,他说,我们住得太远,你来一趟不方便,但你要答应我,半年一定要来看我一次。我当然答应,且以后没有食言,只是我能再见王先生的机会不多了。
1993年秋天,王先生再次住院,这次进的是中山医院。听到消息,我就赶到医院看他。在一间小病房里,病床旁有一对圈椅,椅子中间是一张小茶几。他穿着病号服坐在靠近病床的椅子上,我坐另一把。这次他面容明显消瘦了,精神状态也不如以前。他说肝病加重了,要治好恐怕不可能,能缓解就可以了。他问了文学所的一些情况,然后说起退休前在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他说得多,我说得少。他问我近期的工作,说研究上海文学历史很有意义,不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一定要坚持下去。他说早先有位资料室的同志想转到研究室工作,所务会讨论没有同意,“其实当时我同意也就办成了”,为这件并无需他完全负责的事,流露出真诚的歉意。他说到他的一位学生,要我以后给予帮助,我说这位学生比我强,他就说“那你们互相帮助”。后来这位学生远赴美国,处处比我更强。怕时间长了妨碍他休息,趁他说话间隙,我告诉他近两天要到外地去,大概一周左右返沪,他说“你回来再来看我”。我从外地返沪那天,到家已是夜晚,刚进门,妻子就说“昨天有人打电话来,说老王找你,不知道什么事。”那时上海的一般居民只能使用里弄的公用电话,王先生有我家附近公用电话的号码。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社科院,想销假后就到医院,恰巧遇到文学所工会负责同志,他看到我就说“老王昨天去世了”。听后我顿时懵了,难过的心情无以言表,甚至后悔自己前些日子的外出之行。这时我才知道,王先生临终时陪护在侧的是早先上海作协文研所的一位同志,昨晚的电话是他打的,想通过我找到文学所负责人通报情况。我和这位同志一起赶到王先生家中,同王师母商议如何办理后事。王师母说,王先生生前有过交代,“丧事从简,不麻烦单位,不要惊动众人,只告诉几位朋友,家人送行就可以了”。我们说不能这样,王师母坚持按王先生遗嘱办。最后商定,家乡的人由师母通知,文学所负责发布讣告,通知有关方面,由文学所在殡仪馆租一个小的告别厅,以便愿意送行的同志瞻仰遗容。告别这天,文学所和王先生早前工作过的单位都有人前来,小厅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悼念仪式举行时,很多人只能站在厅外。不少人对文学所只租用殡仪馆小厅大为不满,特别是王先生早先在上海作家协会文研所的同事,都认为按照王先生的局级待遇,应该租用大的告别厅。文学所有人解释说是尊重王先生遗愿,但这些人把解释当成一种托辞,根本不愿意听。我一向不看重办理丧事的所谓哀荣规格,认为无论如何人死不能复生,与其丧事办得隆重,不如生前尽可能厚待,故而对于王先生告别仪式是大厅还是小厅,并不在意,但从这些人的不满看到了王先生留在世间的心碑。
王先生去世后,骨灰寄存在龙华烈士陵园。我的父亲年岁与王先生相差无几,他去世后我们也将他的骨灰寄放此处。有一年祭奠先父时,意外发现王先生骨灰寄放橱就在附近不远,于是,这以后每当我到陵园祭奠先父,也会到王先生处鞠躬拜谒;如果莳养的兰花恰好此时绽放,我会剪取几支,分别供奉给生前喜爱种植花草的两位先辈。
初识王先生时,我还是初事所谓学术研究的毛头小伙,现在已是年过花甲的垂垂老者。在自己坎坷曲折、磨难多多的问学求道经历中,有幸从一些专家学者那里获益良多,王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只是自己天资愚鲁,也不够勤奋,没能拿出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告慰王先生,总是感到疚愧。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