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怎样炼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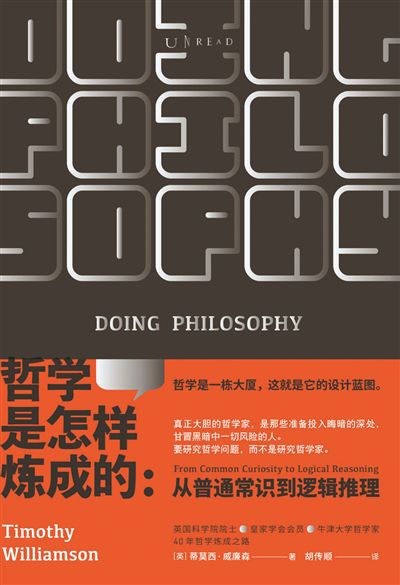
作者:[英]蒂莫西·威廉森 译者:胡传顺 出版:未读·思想家 |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上市时间:2019年11月
所有的学科都是从人类最初的好奇开始的,哲学思考的种子也诞生于每个普通人的好奇。我们从常识中逐渐推理出了各学科的精密体系,也建造出了人类的哲学大厦。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蒂莫西·威廉森教授的《哲学是怎样炼成的》近日由“未读”出版,书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这座由科学哲学、分析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逻辑学等学科铺展出来的设计蓝图。跟随作者的思考,我们会推翻自己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刻板印象,会认识到哲学是用什么工具让人们从业余走向专业,从兴趣走向对永恒与无尽的思考。
哲学,起源于惊异,致力于未确定之一切。在它之下,诞生了数学、天文学、心理学……但仍有无数人问哲学有什么用?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有什么意义?一谈起用处,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那种可以立竿见影的,最好还能够兑换成金钱的用处。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在一般人的眼里,哲学压根就没有什么用。
其实哲学并非如此。蒂莫西·威廉森教授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让-皮埃尔·里夫是橄榄球联合会的传奇人物,是伟大的法国橄榄球国家队1978—1984年间的队长。在一次新闻采访中,他谈到了他对战术的思考:关键在于,对你要试图获得的东西保有一个清楚和明白的观念;然后,你应该把每一个复杂的动作分解为最简单的组成部分,让它们易于直观,再从此处返回以建构整体。里夫虽然没有点出法国标签式的哲学家笛卡尔的名字,但他遵从了笛卡尔对清楚和明白这两个标语的需求和强调,也遵从了他的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的原则之一。法国的学校教授哲学课程,这让哲学有了意料之外的用途。
这个案例说明,哲学并不是某种完全与我们不相容的东西;它已经以各种琐碎和重要的方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如果你走进一所大学的哲学系,不久你就会发现,在某处,或者说大部分地方,正在有许多哲学史课程被教授。与之相反,在数学系或者自然科学系,就很少甚至没有数学史或自然科学史课程被教授。偶尔,数学家或科学家的名字与他们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是,学生们并不期待知晓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些成果的。学生们也很少去阅读他们的原始著作,因为,在原始著作中,这些结论很可能难以辨别,对于阅读者是陌生的见解和语言。而与此同时,哲学系的学生却必须阅读已经死去很久的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或者是其中的大部头,至少也得阅读译本。哲学与其过去的关系似乎不同于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其过去的关系。
很少有哲学家愿意把哲学史放到历史学系。当过去的哲学家在历史学系被研究时,被称为“观念史”。“观念史”更多关注的是哲学家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背景和约束;他们成长、写作、教育的环境;他们读了什么以及谁影响了他们;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和他们所反对的东西;他们为谁写作;他们的著作在当时意图具有的或实际上具有的影响等等。当同样的哲学家在哲学系被研究时,被称为“哲学史”。哲学史主要聚焦于他们的研究本身,而不是其与那个时代周遭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目的就是要把内容理解为一种鲜活的、一贯性的思想体系,它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意义。
哲学史是哲学的一部分。然而,将一个理论当作是某个哲学家提出的,和将一个理论当成是真理,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就学术上而言,哲学史学家通常很清楚这种区别:他们追问的是,这位哲学家坚持的是什么理论,而不是什么理论是真理。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种广泛存在的哲学写作方式,它模糊了这条界限。一些令人高山仰止的思想家,例如,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他通常都会这样撰写著作。当你读到“我们不可能认识物自体”时,你不清楚作者是否只是在主张康德认为我们不可能认识物自体,还是作者以自己的话语主张我们不可能认识物自体,而实际上正支持康德的观点。混淆这两种主张在辩护上是实用的,因为它使作者能够把针对第一种主张的批评斥为没有抓住第二种主张的关键点,把针对第二种主张的批评斥为没有抓住第一种主张的关键点。如果你论证,它作为历史是错误的,回应就是要讨论事情本身。相反地,如果你论证它作为哲学是错误的,回应就是要讨论康德。通常情况下,诸如此类的写作方式既不是好的历史学,也不是好的哲学。
有一种观点是,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因为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这个观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地区,不过,现在这个观点正在逐渐失去它的土壤。我的一位朋友,一位意大利的哲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第一次参访牛津大学。她发现这里的人们仍然在试图解决哲学问题,这是多么的天真可爱。她解释到,她是在这样一种哲学文化中受到教育的,这种文化理所当然地认为根本不同的体系之间没有以之为基础从而作出决断的共同根基。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不可能富含深意地追问,它们之中的哪一种客观上是正确的。我们只能在一种历史上给定的体系或另一种体系范围内进行思考,即使当我们试图从体系内部来颠覆它时。有时我被问到,我研究哪位哲学家,好像这是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必须做的。我以牛津的风格回复:我研究哲学问题,而不研究哲学家。
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这个观点是在自掘坟墓,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哲学选项,我们没有义务必须接受它。它没有证据的支持。在哲学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如本书提到的那些哲学家,是自己写哲学史的。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解释其他哲学家的理论,或者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而是首先建构这样的理论。例如,关于心灵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这与科学理论并无本质区别。这同样适用于今天仍然在发展的大部分哲学理论。而且,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有很多在诸种理论之间进行合理决断的方法。把哲学与哲学史看成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及其不历史的态度,因为它违背了历史本身。虽然研究一个哲学问题的历史(例如自由意志)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但还有许多研究问题的方式并不是研究其历史,正如对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就典型的不是研究它的历史。幸运的是,哲学史可以被研究,但并不是以让它接管整个哲学的帝国主义的野心来研究。
当我们意识到那个地区的人已经忍受了长期人权滥用的历史时,哲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有人权的观念。哲学家则在这个观念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笛卡尔同时期,还有著名的胡戈·格劳秀斯、约翰·洛克,以及其他哲学家。
哲学并不是某种完全与我们不相容的东西;它已经以各种琐碎和重要的方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但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家又在试图获得什么?
传统意义上,哲学家以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想要理解每个事物的本质:存在与非存在、可能性与必然性;常识的世界、自然科学的世界、数学的世界;部分与整体、空间与时间、原因与结果、心灵与物质。他们想要理解我们的理解能力本身:知识与无知、信仰与怀疑、表象与现实、真理与谬误、思维与语言、理性与情感。他们想要理解和判断我们与这种理解能力是什么关系:行为与意图、手段与目的、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事实与价值、快乐与痛苦、美与丑、生与死,以及更多。哲学极具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