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诗选》:大时代里的诗歌英雄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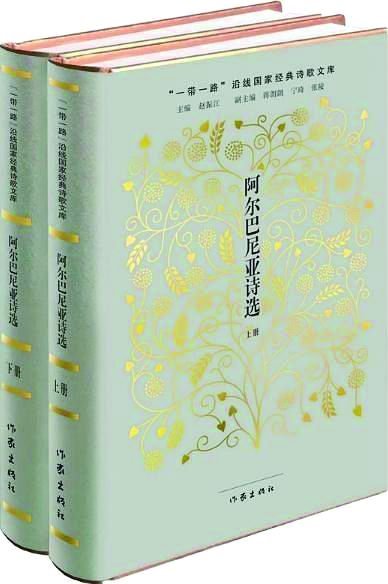
郑恩波先生翻译的两卷《阿尔巴尼亚诗选》(下称《诗选》)摆在我的案头多日,闲暇时翻开厚重的诗选随意读上几段,穿梭于文学与现实之间,与阿尔巴尼亚仁人志士对话的豪情便袭上心头。我对阿尔巴尼亚诗歌的特色有几分了解,质朴、饱满、奔放的诗歌质感虽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含蓄、内敛、隽永,却也因陌生化效果让人不免眼前一亮、心头一动,饶有兴趣地回味着这份异国情怀带来的心灵震撼,更何况,阿尔巴尼亚诗歌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语言魅力本身,这一点足以令人感慨。
郑恩波评价说,“阿尔巴尼亚历代经典诗歌最能反映时代变迁”,是“不同历史时代的烙印和人民的精神标签”,可谓一语中的。诗歌在阿尔巴尼亚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体裁,它代表着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精神气质,不同时代的诗人就是展现其精神气质的代言人,他们通过长短不一、风格趣味各异的作品形塑自身的民族形象,因此,虽然阿尔巴尼亚诗歌表达的情感恣意多彩,从本质上却是以爱国情怀作为其底色的。
在民族复兴时期,世界民族独立的浪潮风起云涌,阿尔巴尼亚诗歌无一例外地承担着反抗外族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重任。风景如画的国度、富饶神圣的土地怎能被外族侵占,健康质朴的男女、辛劳勤恳的耕耘岂容外族抢掠,诗歌用直率质朴的语言传达出对这片养育了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土地,对阿尔巴尼亚勤劳淳朴人民的深厚情感。民族的命运越是多舛,诗歌的情怀越能得到升华。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之父纳伊姆·弗拉舍里绝对是描绘阿尔巴尼亚自然与人文之美的大师,在他的代表作《畜群和田园》里,阿尔巴尼亚山川壮美、百姓朴实勤劳。“在那里,清凉的泉水响淙淙,夏季里刮北风/在那里,花儿芬芳艳丽,朵朵争艳喜盈盈/牧人放着牛羊,笛声向四处传送/带头羊的铃声叮叮响,那儿游荡着我的魂灵”,“鹧鸪快活地微笑,夜莺温情脉脉地啼鸣/玫瑰花飘散香气,那儿寄托了我的憧憬”。和谐美满的生活宛若天堂,娓娓道来的排比句如画卷般铺展,诗人的情感随之逐步提升。常言道,故土难离,美丽的家乡自然更是令人魂牵梦绕,后来者诗人菲利普·希洛卡就把这份故土难忘之情表达得无比真切感人,在姐妹篇抒情诗《飞去吧,燕子!》和《飞来吧,燕子!》里,诗人化身为南来北往的燕子,梦回故国。“请你为我捎上几句话/向我住过的老屋问好,祝愿/再向那附近的地方逐一问候/在那里我度过的年华美不可言”;“你在那里看到的群山/定是巍巍屹立白雪皑皑/你降落过的那些平川地/到处都是如锦似绣百花开”。怀想着儿时在故土的美好时光,对故国难以割舍的情怀萦绕在诗篇之中。当代阿尔巴尼亚诗人德里特洛·阿果里更是纳伊姆爱国诗篇的优秀继承者,他的长诗《母亲阿尔巴尼亚》对阿尔巴尼亚的美景描绘得细致入微,片尾更是直接引用纳伊姆在《畜群和田园》中的名句“啊,阿尔巴尼亚的群山,啊,你——高高的橡树/百花争艳的广阔原野,我日夜把你记在心头”,令人瞬间体会到两位大诗人之间一脉相传的爱国情深。在这些美景的掩映之下,诗人的爱国之情喷涌而出,寒暑日夜、高山溪流、鸟兽草木,都是一个个“爱”的篇章,诗人的笔墨所到之处,都流淌着深情的涓涓细流。
爱之深则失之痛,一旦山河破碎,昔日的美好逝去,阿尔巴尼亚诗人同样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纳伊姆·弗拉舍里的《过去的时光》便充满对旧日的慨叹。“噢,狡猾多变的时光啊/你到哪里去了,跑了多远的路程/你投到了上帝的怀抱里,把我也忘得干干净净……”家园的痛失令人如何不悲伤!然而,如何去争取家园的安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是有骨气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选择,追求民族独立的他们绝不接受妥协与偷生,诗人便以气壮山河的语言来讴歌勇士的铮铮铁骨,诗人西米·米特科写于1878年普里兹伦同盟成立前夕的抗土诗篇,“大家团结紧,齐心来抗争……/赶走奥斯曼侵略者/要么战死,要么英勇、自由地生”,呐喊般地重申了阿尔巴尼亚人同仇敌忾、抵死抗争的传统,也是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中最早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誓言。强敌当前之际,即便是浪漫主义诗歌的鼻祖戴·拉塔(戴·拉达),在《米洛萨奥之歌》《塞拉菲娜之歌》和《巴拉最后的歌》中也把爱情的温柔甜蜜融入了激昂高亢的战斗号角中,于是炙热的英雄美人之爱便融化在更令人感慨的抵抗外族压迫的英雄豪情之中。《巴拉最后的歌》中的“培拉特之歌”是何等的悲壮,长诗通过阿尔巴尼亚勇士尼克与卡乌尔亲王独生女玛拉的爱情故事,反映出斯坎德培时代阿尔巴尼亚人风俗中悲情感人的一幕:“摘下结婚戒指,把它分成两截;一截带到自己身上,一截让她留着”。就习俗而言,丈夫去前方作战,把结婚戒指分成两半,一半自己带在身上,一半留给妻子,如果丈夫牺牲了,妻子可以再婚,这冷冰冰的“遗嘱”看似极为现实,不通情理,勇士与爱妻不应分离,然而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英雄可以决绝地把生死和爱情抛于度外,悲壮的情绪和豪迈的气度自然也就推到了顶峰。
当然,阿尔巴尼亚勇士的决绝并非难以理解。自古以来,阿尔巴尼亚民族生息繁衍的这片土地纷争不断,先有东西罗马的分界线经过此地,后有周边民族不断崛起对此地侵扰不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更是祸及人民忍受近500年的奴役,民族自立之时又遭遇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世界大战。在无休止的战争中,相对弱小的阿尔巴尼亚民族生存不易,宗教、文化等内在因素对民族意识的融合与确立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各时期的诗歌里,我们常常看到,诗人在竭力地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摒弃宗教差异的成见,回归民族团结的根本,普里兹伦同盟时期的诗歌在这一点上最为突出。帕什科·瓦萨在《啊,阿尔巴尼亚》中为因宗教不同而四分五裂、兄弟相残的阿尔巴尼亚大声疾呼。“起来,阿尔巴尼亚人,快快起来别贪觉/大家把兄弟间的诚信永记牢/阿尔巴尼亚人的信仰就是阿尔巴尼亚化/别再去把教堂、清真寺那套玩意儿瞧”;现实主义诗歌奠基人安东·扎科·恰佑比在《祖国和爱情》中也发出了类似的心声。“我们都是同族人,一母生/阿尔巴尼亚是我们亲生的娘/是宗教把我们分离开/害得我们互相杀戮动刀枪”。在这篇通俗易懂的民歌式诗歌中,他鼓舞阿尔巴尼亚人共同抗击土耳其,把宗教的差异抛到一边,并肩作战才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时期,团结战斗的号角更加响亮激昂,诗人情思如泉涌,创作出一篇篇充满诗意、朝气蓬勃的游击队歌曲,青年人个个奋勇争先,兄弟同心,比如法特米尔·加塔的《青年,青年!》就是一首充溢豪情的战斗之歌。“青年,青年,你们要勇往直前/像太阳,像火石,像闪电/你们向前进,如同雷电燃起的烈火/为了家园和光荣,青年们要勇敢去作战”。这些歌词以激励青年人奋进为内容,以突击队进行曲为形式,让奋勇杀敌的壮志豪情与飞扬无悔的青春年华相互辉映;而梅莫·梅托的抒情诗代表作《我要上山去》更是点燃了女性为革命献身的铿锵之情。“我是一个阿尔巴尼亚女儿/我是一个山姑娘/我精力充沛心儿红/就像小伙子一个样”。女性与男人一同战斗,与男人一样战斗,成为阿尔巴尼亚革命斗争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青年男女渴求自由,更向往过真正当家做主的生活,诗人恩德莱·米耶达在《夜莺的哭泣》写道:“严密封闭的鸟笼子打开了/夜莺你飞吧,赶快逃离/飞过林海和小树林/夜莺你快快飞,要立刻离去”。把对自由的渴望竭力表达,而阿尔巴尼亚人热爱自由是骨子里血脉传承的基因,民族复兴和独立时期的伟大诗人,被誉为阿尔巴尼亚荷马的杰尔吉·菲什塔在名篇《阿尔巴尼亚》说得尤其斩钉截铁。“掸掉灰尘昂起头来/阿尔巴尼亚像女王一般娇美自豪/因为你用胸中的温暖把儿女养大/决不接受奴隶这个称号”。阿尔巴尼亚有这样的英雄儿女,有这样的战斗精神,即便弱小,也能排除万难,把民族独立的目标实现。
动荡纷乱的历史即使漫长,也终将结束,在20世纪后半叶,建设阿尔巴尼亚新生国家的挑战更加紧迫,更需要阿尔巴尼亚人的齐心、信心和恒心。诗人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讴歌新时代,点燃自己激情的岁月,成为投入热火朝天建设事业中的一代特殊建设者,他们真切地践行了20世纪30年代浪漫派诗人米杰尼《自由的诗》第五部分中对共产主义春天的憧憬与热爱,成千上万奉献青春报效国家的栋梁之才,从战场上的英雄豪杰转变为创业中的劳动能手,他们对祖国明天的坚定信念从传统中来,到现实中去,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那不再是纳伊姆·弗拉舍里《斯坎德培的一生》中激情的呐喊:“您可看到这把带钩的利剑?!……/整个阿尔巴尼亚民族就要消亡。……/让我们以诚信为荣立下誓言/让整个阿尔巴尼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但此时的阿尔巴尼亚依然需要团结一心,把对祖国的深爱转变为建设美好家园的行动,正如阿果里在《我的幸福的村庄》里描绘的那样,当年的建设者意气风发,“生活像麦子那样欢笑/笑声在山山岭岭回荡/我的幸福的村庄啊/你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他们沉浸在翻身做主的喜悦之中,他们将对自己与民族的爱体现在对党的忠诚上,犹如阿果里在《德沃利,德沃利!》中激昂地宣誓那样,“我是德沃利的共产党人……/啊,德沃利/我射出一发又一发子弹/都是为了令人向往的共产主义……/我一生/永远都做一个共产党人”。此时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与期待之心都是真挚质朴的,他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一定能旧貌换新颜,阿尔巴尼亚人都能阔步走在幸福的大道上。
然而,建设国家之路并不比争取自由独立之路来得平坦,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制度巨变给阿尔巴尼亚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精神创伤有目共睹,爱国诗人的敏感内心备受煎熬,他们的诗篇暂别了之前的奋进激昂,陷入困顿痛苦之中。在《我好像不是生活在我的祖邦》《烦恼地站在电视机旁》等诗篇里,阿果里时而“当众多的人把我团团围住/在我贫困的祖国对我现出陌生人的模样”,时而“你咒骂世界,发起脾气心急火燎/世界竟不把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制造”,为迷失方向的国家忧心忡忡、痛心疾首;泽瓦希尔·斯巴秀在《无名字的人》中流露出彷徨无助之感,“我是一个无名字的人,不知我们在什么时代生存”,诗人的言说变得无比艰难;在《灰色的宗教仪式》,他喊道“无味的风/无面包味的面包/无心灵的心扉”,似乎大家的生活都失去了往日的滋味;现实像无解的巨大疑问压在心头,“你把什么给了这一天/这一天又给了你什么”,迷惘的心绪令人对他们的苦闷与愤慨感同身受。
常言道,诗言志,阿尔巴尼亚国家贫弱,却也不乏壮士英雄,它是爱国诗篇的沃土,是爱国诗人的摇篮。在历史上,民族复兴时期、反法西斯战争,抑或国家解放战争时期,侵略者和奴役者来来去去,阿尔巴尼亚的仁人志士浴血沙场,报效国家,在诗歌里,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诗人与国家同喜同悲,慷慨赞英雄,奋笔书胸臆。战场上的英雄有的是豪言壮语,诗坛上的名家吟的是家国情深。一遍遍回味着郑恩波先生收录与翻译的这些名家诗作,在字里行间感受诗人激荡飞扬的情思,由诗作汇聚起来的碎片组成了一幅时隐时现的真切历史长卷,诗人们在上面挥毫泼墨,把他们最饱满的热情,心底最深切的期待都奉献给自己的国家,沉重的过往、短暂的幸福和眼前的困顿,阿尔巴尼亚所历经的酸甜苦辣他们都一一品尝,成为他们歌咏的出发点,让直率、质朴的语言中包含了无尽的深情。可以说,时代孕育了阿尔巴尼亚人的英雄壮士,也塑造了一大批写出肺腑诗篇的优秀诗人,他们以诗歌的方式同样有力地回应了时代的召唤。阿尔巴尼亚诗人无论身处什么时空,内心总牵挂着祖国的高山深谷、平原沃野,他们往往既用诗篇呐喊,让英雄长存,诗魂永驻,更用实际行动为国战斗,流血牺牲,而在诗篇中,二者融为一炉,他们不仅歌颂了不同时代的英雄人物,也描绘了自己为国为民忧思的胸怀。这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爱国志士和诗坛名家共同书写出一部时代英雄谱。
众所周知,译诗是最费力耗神的工作,精妙传神的诗篇常常得于“妙手天成”,然而,即将耄耋之年的郑恩波先生却以过人的勤勉与无限的热忱,将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的重要诗篇一一翻译,洋洋洒洒600页,译作之包罗万象可以视为撰写阿尔巴尼亚文学史的前奏,其倾注的心力与情感令人高山仰止,叹服不已。在这些汉译阿尔巴尼亚诗歌中,郑恩波先生以无比的勇气挑战了诗歌的“不可译”,他的译文不仅再现了原作语言的意义,而且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的意境与韵律之美,各色诗作,无论是热情奔放、激烈高昂,还是深情含蓄、婉转低沉,其诗歌风格均细腻地在译作中得以呈现,其诗歌形式也得到了巧妙的安排与把握,熟悉阿尔巴尼亚语的读者阅读时往往能够心领神会,体悟到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的奇妙反应,想必一窥阿尔巴尼亚诗歌世界的普通读者也定然心有所动,情有所感,在掩卷之后对阿尔巴尼亚诗歌的丰富性有了直观的印象。
在《诗选》末尾处,郑恩波先生精心挑选了为数不多的中阿友谊之诗和寄赠他本人之作,简要展现了阿尔巴尼亚与中国一段亲密珍贵的历史过往,记录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通过这些难得的视角,中国读者体会到阿尔巴尼亚诗歌中“托莫里山问候喜马拉雅”般恢弘的气势,异国诗歌的诗性语言之美与人文情怀得到了细致的展现与准确的表达。通过《诗选》,用最符合人性的诗歌语言历时地分享阿尔巴尼亚国家与民族的精神面貌,想必郑恩波先生略略完成了一些心中夙愿,而中国的读者幸运地可以一瞥阿尔巴尼亚诗歌语的质朴灵动,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内心世界来一番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