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人的萨迦故事是如何流传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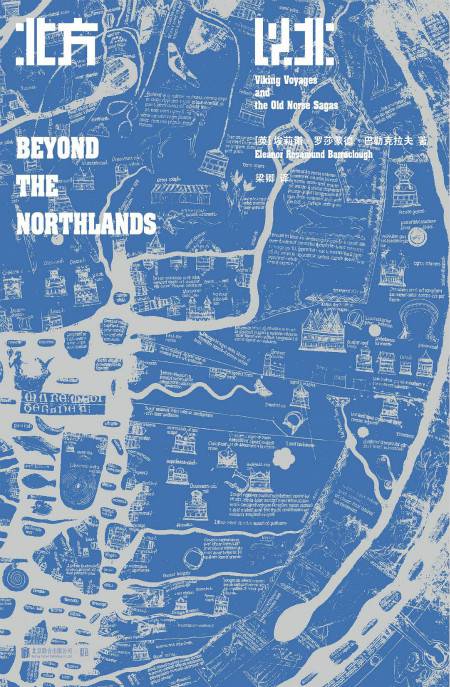
萨迦故事
今天,我们也许用“萨迦”(saga)这个词来描述一连串拖沓冗长、跌宕起伏的事件:比如上下班路上的倒霉经历或者持续演进的家族世仇。在文学作品中,“萨迦”往往指描写一个家族几代变迁的系列小说,例如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Forsyte Saga,1922年),或者近年来吸血鬼题材的《暮光之城》(Twilight Saga,主角是一名百岁吸血鬼,他泡在美国一所中学里,对一位少女倾心神往)。而这些用法几乎没有告诉我们萨迦究竟是什么。
萨迦是中世纪冰岛留给世界的讲故事的独特遗产。它们的题材和广度十分惊人,涵盖浩瀚的地理、历史和人文领域。萨迦紧张激烈的叙事即使削去枝叶,也足以媲美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喜剧或好莱坞的史诗巨制。受阻的恋爱故事错综纠缠,演变成家族积怨和仇杀的血腥乱象。勇士悍将死到临头依然谈笑风生,眼睁睁地看着刀剑刺入自己的腹腔。精力旺盛的青年与农夫的女儿、女王乃至女巨怪上床寻欢。武器寒光凛凛,律师策划阴谋,英雄周游四方,计策轮番上演,巨怪勃然大怒,飞龙喷火吐雾,长船风驰电掣,亡命徒东躲西藏,萨迦的天地在北方的天空下风波迭起。有些故事脍炙人口,包括悲剧《被焚者尼亚尔萨迦》(Saga of Burnt-Njal,冰岛语Kálfalækjarbók),结局有近百人死亡;《埃吉尔萨迦》(Saga of EgilSkallagrimsson)的主人公既是个喧哗吵闹的醉汉,碰巧也是一位情感细腻、才气四溢的诗人。在其他故事中,我们会见到悲剧人物、亡命徒格雷蒂(Grettir),他在旷野中与魔鬼和亡灵格斗,却有个致命的缺陷:如孩子般地害怕黑暗。出了冰岛熟悉的地界,叙事的线索向外伸出,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男男女女扬帆出海,驶过内陆水道,去往中世纪世界的天涯海角甚至更远。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见到远赴他乡的人们,比如古德里德(Gudrid),这个不可小觑的女人远赴北美洲,怀孕生子;还有“红色埃里克”(Erik the Red),这个脾气急躁的连环杀手在格陵兰建立了北欧定居点。
这些例子全都出自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组萨迦:“冰岛人萨迦”(Sagas of Icelanders,冰岛语Íslendingasögur)。故事聚焦于早年移居时期的冰岛,从公元870年前后、冰岛有人定居开始,到公元11世纪上半叶。“冰岛人萨迦”涉及许多真实有力的社会主题,比如定居情势、家谱细考、法律争端、领袖腐败、宗教皈依和需要杀一杀威风的外国国王等。但是,这些叙事同样可能变成讲述离奇故事的神秘钥匙:遇害者在坟墓里歌唱,女巫把用血写下的卢恩文刻在浮木上给人带去死亡,逝者的诅咒返回来折磨生者,不祥的武器给几代人的命运蒙上长长的阴影。
早期冰岛及其居民并非对所有萨迦都感兴趣。还有一类萨迦叫作“国王萨迦”(Konungasögur),主要描述来自挪威的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们多彩的生平和骇人的死亡。这些故事的地理跨度很广;我们跟随国王们走出北欧,踏入欧洲、罗斯和中东。这些故事是年代最早的萨迦,通常作为选本在手抄本中保存下来。这些手抄本的标题给人以丰富的视觉联想,比如《腐烂的羊皮纸》(Morkinskinna)、《美丽的羊皮纸》(Fagrskinna)和《皱巴巴的羊皮纸》(Hrokkinskinna)。
“冰岛人萨迦”和“国王萨迦”讲的是陈年旧事,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历史文献。其他类型的萨迦更像童话故事,把神话般的英雄、带有浪漫色彩的传说与民间故事、不可思议的冒险和淫秽下流的趣闻融合在一起。这些萨迦门类是中世纪和现代语汇的大杂烩。有人认为,大体上讲,萨迦体裁最重要的标志是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地理背景;确切地说,每种萨迦体裁都有一个时间和地点。
例如,“传奇萨迦”(Fornaldarsögur)营造了一个超越冰岛,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叙事世界。不同于“国王萨迦”,“传奇萨迦”发生在准神话、不确定的时代,发生在人们定居冰岛很久以前。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传奇萨迦”到公元19世纪才作为一种体裁整理成册,收录为三卷,标题叫作Fornaldarsögur Norðurlanda,字面意思是“北地古代萨迦”。当然,我们不能确信,最初的中世纪萨迦作者和读者也会以同样的思路把它们汇总到一处。
其他萨迦在起源上更富异域色彩。“骑士萨迦”(Riddarasögur)描述出身高贵的骑士和英雄的历险记,通常以欧洲为舞台,但也冒险进入更具异国情调的地区。这种欧洲特色最为浓郁的萨迦体裁不是诞生在冰岛,而是诞生在挪威,诞生在国王哈康·哈克纳森(King Hakon Hakonarson,约1217-1263年在位)的宫廷。最早的“骑士萨迦”编译自亚瑟王的宫廷传奇和四处求索的骑士故事。后来,冰岛人自认为可以青出于蓝,于是开始写作原创的“骑士萨迦”,相当于今天的同人小说。所以,现存两类“骑士萨迦”:翻译故事和原创故事。
口耳相传与手抄本
萨迦诞生于风起云涌的文化氛围,法律、家谱、航海细节、历史事件、创世神话、家族故事、民间传说和诗歌经由口耳相传得到传播。它们作为口述故事具有了生命,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又不断重复和修改,由许多人塑造,补充新的细节使之更为详尽,添枝加叶使之更加精彩,以便在冬日的炉火旁讲述。saga 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这一点,它与古诺尔斯语的动词segja 有关,意思是“说”或“讲”。在描述日后把萨迦记录成文的方式时所使用的措辞也反映了这一点:中世纪冰岛人称之为setja saman(拼凑整理)。虽然书面形式的萨迦均由一位(几乎全部佚名)作者书写,但叙事效果却很像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Greek Chorus),构建和记录萨迦的人好比歌队领头人,引导着众多声音,这些声音纵贯创作萨迦的较晚时期和故事发生的较早时期。因此,许多脍炙人口的萨迦既不是纯粹的虚构故事,也不是坦白明朗的历史记录。它们处在事实与虚构、口述与笔述、过去与现在之间模棱两可的地带。它们既包含本土对世界的了解,也包含从欧洲大陆传来的渊博学问。
现存的萨迦保存在几部大型手抄本合集中,主要收藏在雷克雅未克和哥本哈根。阅读古诺尔斯语手抄本的感觉很像吃力地破译战时密码,细密的笔迹中夹杂着神秘排列的圆点、破折号,小小的字母悬浮在字里行间。因为早期学者想出的妙点子,有些手抄本破解起来难上加难:为了放大字迹,他们会把水洒在上面。乔·黑尔加松(Jón Helgason)是20世纪中期研究诺尔斯语手抄本的大专家,他在哥本哈根的“阿纳玛格南研究所”还有边看手抄本边抽烟斗的习惯。中世纪研究专家克里斯廷·费尔(Christine Fell)日后回忆道:
我依稀记得,在大英博物馆(现图书馆),有人要求我们不得对着手抄本呼气。在博德利,我们必须发誓不把火种带入图书馆。这两条禁令在阿纳玛格南这里都没有做到,乔·黑尔加松教授坐在楼梯顶端吸烟区的沙发上,手中的烟斗很少熄灭。
部分中世纪冰岛手抄本配有雅致的彩饰和奇特的插图,内含举足轻重的法典和宗教典籍的手抄本尤甚。举例说明,一部手抄本有一段叙述漂流物归属权的文字,它用一个装饰鲜艳的字母开头,页面上画着四个小人剥一条搁浅鲸鱼的皮。对这部手抄本的检测表明,其中含有从欧洲进口的丰富颜料:猩红、雌黄、宝石红、铜矿蓝、赭石红和骨白色,宛如一道化学物质的彩虹。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照亮了中世纪欧洲装饰华美的著名手抄本相比,这些保存了诺尔斯语-冰岛语作品的中世纪羊皮纸或许显得相当朴素。即便如此,中世纪冰岛人为了制作这些宝贵的文本也没少花费心血。中世纪冰岛抄写员的信笔涂鸦透露,书写过程十分漫长而耗费体力。在一份手抄本的边角,抄写员评论道(也许基于惨痛的切身体验):“顶着西北风写字很不舒服。”在另一处,一个孤苦的身影陷入了存在主义的厌倦和怆痛中,他放下工作稍事休息,在页底胡乱写道:“我觉得独自在这间缮写室已经待了很久。”在另一部手抄本中,抄写员直抒胸臆:“我厌倦写字。”还有一名抄写员对一个叫多里(Dori)的人有意见,想必是他的老板:“你待我不公,多里,你给我的鱼总是不够。”
书写萨迦的不仅是修道院的抄写员,还有富裕的农场主和部落首领,这在中世纪世界很不寻常。难怪现存的中世纪羊皮纸中,有那么多萨迦手抄本装饰极少,且通常肮脏邋遢。这些土褐色、平淡无奇的书页成了把萨迦传承数百年的适当载体。它们不是举足轻重、张扬闪耀的故事集,需要用金箔装饰,封面镶嵌宝石。它们是为了供人消遣而写,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这些萨迦手抄本大多是务实的文化产物,收藏在全国各地的茅屋农舍,里面包含劳累一天后要大声给全家人朗读的故事。这些萨迦几经翻阅和转手,几乎到了散架的地步,人们用木板装订、用海豹皮缝制封面。它们由冰岛人书写,为冰岛人书写。这些手抄本不起眼的外观连同墨黑色的字母,也吻合了萨迦的叙事风格:高度简洁、情感内敛、阴暗滑稽、论事克制、冷静聪慧,最重要的是,具有鲜明的北欧特征。
把萨迦记录成文是在公元12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副本的制作则持续到了20世纪。曾经有过的萨迦比今天留存下来的要多,部分原因是并非所有萨迦都已记录成文,即使把萨迦写到羊皮纸上,也不能保证手抄本能够完好无损地度过数百年的时光。举例说明,公元1682年秋,一艘船从冰岛驶往丹麦时,在冰岛的东北海岸沉没,无人生还。这艘船上还装载着一夏天收集到的冰岛手抄本和图书,准备由国王的古董保管人运往哥本哈根。在冰岛收集到了什么,没有记录可查,收集物全部沉入大海深处。手抄本收藏大家奥德尼·马格努松(Árni Magnússon)想要确定船上装了什么,传回来的答复是:“一船羊皮纸破书。”
即使手抄本在航海途中保存下来,没有永久受潮,也远远谈不上万无一失。破损蒙尘的羊皮纸是上佳的引火物,奥德尼·马格努松在公元1728年10月的哥本哈根大火中吃了苦头后发现了这一点。哥本哈根失火后,奥德尼带领助手把注意力转向了图书馆。一次笨手笨脚的救火行动在慌乱无序的大街上展开,三四辆装满诺尔斯语手抄本和其他古籍的马车经过灼热的卵石路,吱吱嘎嘎地到达了安全地点。
模糊的边界
如同中世纪北欧人本身,萨迦也涉足辽远。总的来说,萨迦的天地既广阔,又层次丰富。它在遥远的北方深入北极的斯堪的纳维亚,向南延伸到拜占庭和圣地耶路撒冷,从东部罗斯的王国和江河,延伸到西部的格陵兰和北美洲外缘。萨迦也具有时间的纵深度,从混沌的、传说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古昔,一直绵延到公元13世纪冰岛的政治阴谋。这个萨迦天地混合着现实与幻想、准历史冒险与远远超出现实范畴的奇幻故事。主人公也许向北进发,头脑冷静地向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萨米人(sámi)征税,收取货品。同样,他也可能发现自己中了魔法,坠入情网;或者莫名其妙地到了巨怪和巨人族的王国。向西去往格陵兰的航程风雨交加,对航程的描述也许包含十足精确的航海信息:从一块陆地到下一块陆地要花多长时间,要选择哪个方向。到了格陵兰,新来者发现自己在东部定居点受到“红色埃里克”的欢迎,在荒郊野外遭遇神奇的巨怪姐妹的威胁。
另一类萨迦的主人公也许动身去往东边的异国,寻求政治避难或学习外语。在这些王国外面,广布着片片旷野荒原,一直通往人间乐土的地界,龙、鸟面人和食人巨魔在其间漫步徜徉。萨迦中有些人物向南去往中世纪基督教的中心,心之所向也许执着于去罗马和耶路撒冷虔诚朝圣,抑或参加血腥的东征。如果他们本性贪财,那么,可能性更大的目标也许是去拜占庭皇帝的精选私人保镖团瓦良格卫队(Varangian Guard)服役。如果他们走得足够远,也许会径自“掉”到地图以外,身边围绕着在中世纪地图和手抄本边角处嬉戏的精灵鬼怪。
尽管缤纷多元,萨迦却并没有沦为互不相干的意象胡乱堆砌的大杂烩。相反,萨迦呈现出一幅流动、片断式、多层次的世界图景。在萨迦的镜头下,世界的某些区域十分清晰,某些区域模糊而抽象,某些区域干脆一片空白。没有无所不包的世界视野,没有确凿无疑的心理地图,没有精准无误的文学地图集。世界各区不存在清晰划分的边界;各种文化也没有绝对的界限把它们隔开。本书虽然以指南针的四个主要方向安排结构,但是,北方自然而然渗入东方,东方渗入南方,南方渗入西方,西方渗入北方。如一部萨迦的作者所言:
“也许有人听到这些萨迦,不相信它们是据实编写,因为对各地的方位不明就里的人,也许会把东叫作西,把南叫作北。”可是,粗糙的字句、重叠冗余、灰色地带和前后矛盾,与精确测量的距离、详尽无疑的解释及对其他族类粗笔勾勒的漫画同等重要。这是人类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法。
(本文摘自埃莉诺·罗莎蒙德·巴勒克拉夫著《北方以北:维京人的航海与萨迦中的北欧历史》,梁卿译,低音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