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洛威尔:我自身便是座地狱,此处空无一人
只有臭鼬,在月光下
搜索着一口食物,
它们阔步行进在大街上:
白条纹,狂乱眼神中的鲜红火光
在三一教堂那白垩色、干燥的
圆柱尖塔下面。
我站在我们
后踏板顶部,吸入那浓烈的臭气——
一只母臭鼬带着一群幼崽在垃圾桶里大吃大喝。
它把楔形脑袋插入
一只酸乳酪,垂下鸵鸟般的尾巴,
毫无畏惧。
——节选自罗伯特·洛威尔《臭鼬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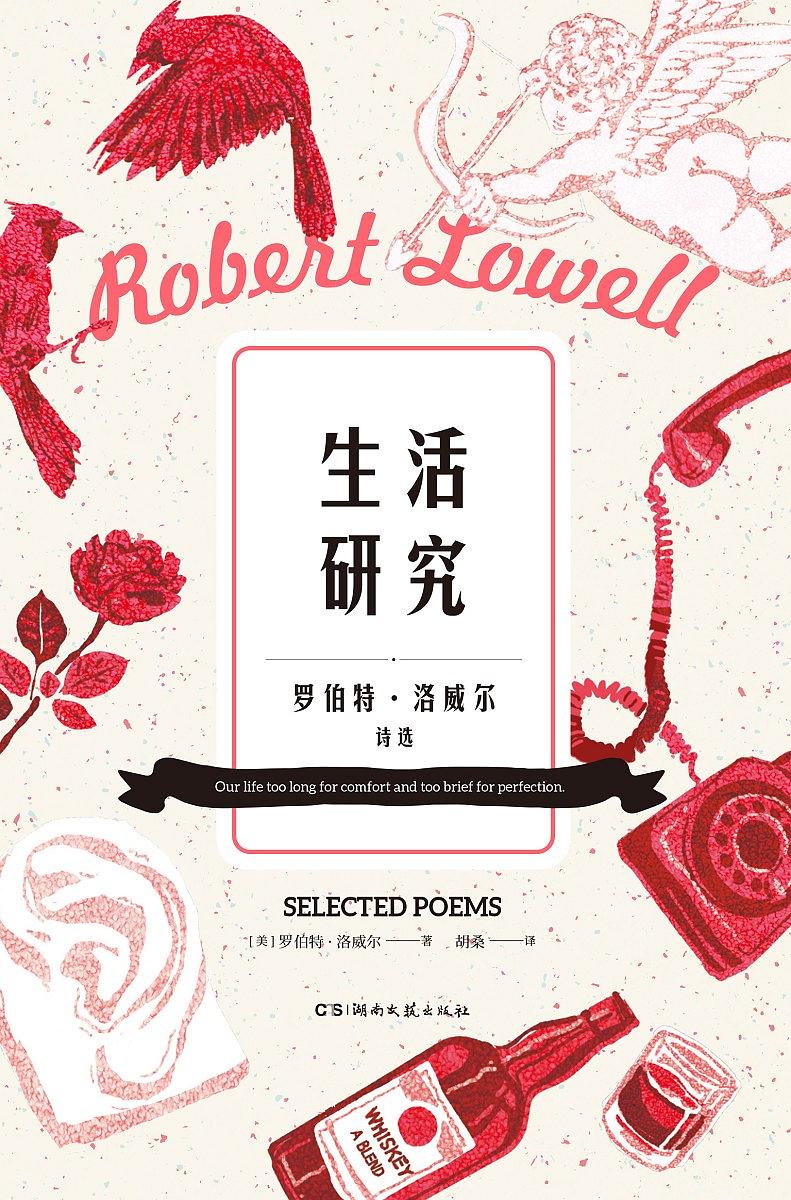
《生活研究》 (美)罗伯特·洛威尔 著 胡桑 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为什么只有臭鼬
这首《臭鼬时光》意义非凡,它是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 1917-1977)的代表作,也是自白派诗歌的里程碑作品。
原诗有八节,因篇幅关系,本文只引述了最后两节。这部分的写作,很有画面感。月光之下,一群臭鼬,在大街上,阔步行进,搜索食物,在垃圾桶里大吃大喝。发生在三一教堂的圆柱尖塔下面的这场狂欢盛宴,本质上是僭越,是反对宗教的,诗人歌咏的对象,是母性的爱与无畏,为了生存,母亲带领她的子女,向陌异的世界发起了挑战。
两段十二行,传达了激昂的情感,让人颤栗,让人不安。读整首诗,回顾前面六节,会有更深的体会。臭鼬是在最后出场的,之前的都是什么呢?从“鹦鹉螺岛上的隐士/女继承人在简朴的屋子里度过冬天依然存活下来”讲起,诗歌描述破败的、衰朽的人境。“这季节病了——我们失去了夏日的百万富翁”,古玩店装饰家贩卖着无用的商品,“他劳作,却身无分文,他不如去结婚”,“我的都铎福特车攀爬在山的颅巅”,望下去,“车身紧挨车身,仿佛坟场叠在城镇上面”,车中的收音机在怨诉着,而“我”觉得“我”的手仿佛卡在了喉咙……
纵使物质富有,孤独无边无际,城市被弃在身后。诗人叹息道:“我自身便是座地狱,此处空无一人”。他人即地狱。前面六节的主体是人类,最后两节是臭鼬。心灵的荒凉凄寂与精神的勃动活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臭鼬,唯有臭鼬,以生的斗志与健康的欲望,行进在空旷的大街上,成群结队,彼此信任,冲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
《臭鼬时光》是罗伯特·洛威尔的诗集《生活研究》的压轴之作。这部诗集写于1954-1959年。在这期间,洛威尔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1950年父亲去世,1954年母亲也离世了。重视亲情的洛威尔在1952年和1954年先后两次患上抑郁症。在1957年,洛威尔成为父亲,新的家庭与情感连接,抚慰了他的忧伤,也让他有了新的体悟。洛威尔开始回望家族的经历,反思为人父母的职责,审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边界。
洛威尔诗风的转变
浦睿文化的这部《生活研究》,不是洛威尔同名诗集的全集中译,而是从《生活研究》(1959)《威利老爷的城堡》(1946)到《日复一日》(1977)《最后的诗》(1977)等十部诗集的精选,主要是中晚期作品。洛威尔的早期与中晚期诗风有很大差异。
谢默斯·希尼说过:“如果有一个术语可以用来形容开始于火成而终止于沉积的过程,则这个术语就很适合形容罗伯特·洛威尔的诗歌。”从前的洛威尔是一头不驯服的公牛。他在1943年因拒服兵役而坐牢,这起事件让他被符号化,也让他的诗歌与政治结缘。作为带着抱负却被社会辜负的年轻人,洛威尔严厉批评他的国家,把喷火的愤怒诉诸于笔端。
《威利老爷的城堡》(1946)是洛威尔的早期诗集。选了六首。来读《圣婴》。它化用了《马太福音》里的故事。希律王为杀死婴童耶稣,屠杀了伯利恒城的婴孩。“希律王尖叫着,向正在空中呛咳的/耶稣那蜷曲的膝盖复仇。”诗歌象征意义明确,节奏短促有力,激情充沛。权威的《党派评论》评价:“他(洛威尔)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政治的、经济的和谋杀的世界——被残酷地坚持写下去,而我们一切新鲜而苍白的希望却消失了,希望的位置被盲目而血腥的天堂所代替了。”随着1945年战争的结束,压抑的情感寻找释放的渠道。诗人站在废墟之上,用诗歌呐喊,用诗歌控诉。
或者,极力反对的往往恰是因为热爱,所以肯定会失望。洛威尔渐渐转向更私密的内心探索。《生活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境下诞生的。
《臭鼬时光》有之前的风格遗痕,但已不是抗议的口吻,追索个体的存在意义。《丹巴顿》追溯家族起源,“我外祖父发现/他外孙大雾笼罩的孤独/比人类社会更甜蜜。”在这里,祖先曾经参与独立战争;在这里,祖先曾经非法自制红葡萄酒,“甜得就像装在蜡封/平底玻璃杯里的葡萄果冻”;在这里,家族的墓地埋下时代的遗骨。洛威尔写着《父亲的卧室》,写着《高烧时》躺在婴儿床上的小女儿,写着《男人与妻子》,写着《“谈及婚姻时的烦恼”》……这些诗歌有我们熟悉的家庭场景和生活细节,普通人的欢喜与烦恼,是一个人的生活自白。在诗风上,更加接近日常用语,更强调心理的真实表达,自由随意,开放不隐晦。
评论家罗伯特·霍尔伯格说,洛威尔取得了两项成功:《威利老爷的城堡》和《生活研究》。两本书的不同点,特别是风格的差异,意味着整体知识文化的情趣和情感的划时代的转变。1946年恪守格律,1959年宽松的格律、自由诗,甚至散文;1946年华丽的宗教狂热,1959年温雅世俗的自传。在从前,洛威尔以对有意义的历史性变化抱希望的启示录式空想家的身份创作,而《生活研究》的作者一扫往昔的信念:一首重要的诗,为谁而作?
自白,向着内心的追问
洛威尔的转型,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诗歌的功能。《生活研究》因此格外重要。在它的推动下,“自白派”蔚为潮流。
译者胡桑在译后记里,起笔就开列了一个长名单。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最为耀眼的诗人:洛威尔、毕肖普、普拉斯、金斯堡、默温……他们共同发动了对艾略特及由新批评派倡导的那种冷峻、晦涩、玄秘的学院风格的反叛。这一代的诗歌不断书写个人的经历,披露私人化的隐秘情感,掀动被压抑的心灵的绝望反击,他们毫不忌讳地谈论那些传统诗歌回避的主题,比如离婚、流产、药物、性、精神的疾病、自杀的冲动,等等。这些诗歌与当时美国的社会思潮相结合,反映了战后中产阶层的艺术观和生活观,彻底摧毁了高雅严肃文学规矩得体、正派严谨的准则,一意追求个性的解放。
洛威尔是“自白派”的开风气者,也是其中成就最大的诗人之一。在《生活研究》之后,直至1977年逝世,洛威尔一直继续他的“生活研究”。
洛威尔经历了三次婚姻,《在大洋附近》(为E.H.L而作)描摹“最后的激情/透过她的肉身震颤。英雄站立……”,甚至还出现了对经血的描写。《初恋》与《一九三〇年代》系列作品,回忆少年时代的激烈青春,“后来,我们知道了投射我们藏红花色/精子的更佳地点,领会了智慧所恐惧的,/胸部高耸”。有好几首诗是写给小哈丽特的,女儿是洛威尔的珍宝,在女儿身上,洛威尔重新发现了母亲,与亲情的温热。洛威尔长期为躁郁症所困扰,通过《症状》《在病房》《十分钟》等诗作,我们可以领略诗人的痛苦、恐惧与孤独。自白诗的视角是内向的、自我的,采取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学说的分析应用,很多自白派诗人都有精神疾病,或许,灵魂的损耗就是他们必须为诗歌付出的代价。
自白派的主题大多是个人生活,但并不等于说,这些诗歌就总是写琐细的日常。还有友情,还有阅读,还有思考,还有个体置身的社会与大世界。比如,《臭鼬时光》就是为伊丽莎白·毕肖普而作,洛威尔后来说,“重读她(毕肖普)的诗为我开启了一条道路,使我得以冲破我的旧模式的束缚”。洛威尔与毕肖普的友情延续了一生。自白派之所以成为一大流派,诗人之间的相互借鉴,是一大原因。洛威尔还有很多诗歌,写给他的同时代的“队友”。读《为联邦军阵亡将士而作》(1964),很显然是对越战的抵制。当洛威尔写下诗集《历史》(1973)时,一切历史都是他的当代史。这些公共性的诗歌,比起早期的作品更有同情心。
1977年8月31日,罗伯特·洛威尔离世。《夏潮》是最后的诗歌,写于他去世前三天。献给第三任妻子卡罗琳·布莱克伍德。在结句部分,洛威尔写道:“我想起我的儿子和女儿,/还有三个继女,/他们在遥不可及的暗礁上,/可怕的哗哗作响的波浪冲刷着暗礁……/逐渐侵蚀着我所站立的防波堤。/他们的父亲缺少慈爱的抚触/在疏松的围栏上颤抖。”在这时候,洛威尔似乎尚未获得心灵的平静,仍然被自疚感包围。愿他在天堂能逢亲人,他的祖先与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他爱的人们,愿他安息。


